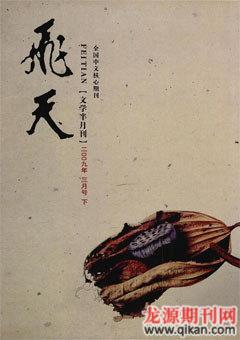二元對立中的文本
李兆芹 趙文慧
索緒爾是20世紀最著名、影響最為深遠的語言學家之一。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為現代語言學三大結構主義學派奠定了基礎。他的研究不僅對20世紀的語言學研究,而且對20世紀以來的文學理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特別是對結構主義文論影響尤為深刻。
語言學分析中的二元對立觀念源于索緒爾。他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組合關系與聚合關系以及能指與所指這些最基本的語言學范疇都表現為二元對立形態。由于二項對立在思維和認識中的重要作用,這種對立關系在文學和藝術創作中同樣被廣泛運用著。“文學敘事文本中最典型的類別是故事或小說,一個故事在表層上是若干句子的集合,但句子的集合卻并不都能構成故事。在作品中,作為運行過程的敘事和作為書寫的敘事都有其結構秩序”,并且,依照格雷馬斯的說法,“意義初級成分結構當被定義為至少兩項間的關系時,它只基于語言聚合軸特有的一種對立區法”。長期以來,二元對立形式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文本分析方法得到普遍應用。因此本文擬從組合關系與聚合關系的二元對立角度來分析俄國作家米·布爾加科夫的作品《大師與瑪格麗特》,以期能夠揭示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蘊。
一、橫向組合層面的《大師與瑪格麗特》
索緒爾認為,在語言狀態中,—切都是以關系為基礎的。這種關系表現為兩個向度語言的橫向組合關系和縱向聚合關系。橫向組合關系,是指構成句子的每一個語句符號按照順序先后展現所形成的相互間的聯系。語言的存在和表達方式總是時間性的。人們不可能在同一個瞬間完成多個符號的語言傳達。譬如“這是一個靜謐的夜晚”,我們只有在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后才最后明白它的涵義。這意味著,在一個旬段中,一個詞的意義,總是部分地由它在句子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別的詞構成的語法關系所決定的。
《大師與瑪格麗特》的橫向層面的布局“可以看作四條情節線索并行發展:當代莫斯科的現實生活,魔王沃蘭德的來訪,大師與瑪格麗特的愛情故事,古代耶路撒冷的事件。”這四條線索共同構成了小說的表層結構,讀者只有從頭讀到尾才能明白作者講述的是一個什么故事。
當代莫斯科的現實生活隨著魔王沃蘭德的來訪徐徐展開:不信神的作協主席的死亡,愚昧粗魯的詩人“流浪者”被關進瘋人院,雜耍劇院相關人員的莫名失蹤,等等。看似是演出了一場滑稽的悲喜劇,莫斯科市民的貪婪愚昧由此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示,莫斯科社會的陰暗面由此得到了揭露。
在這一層面上我們只了解到了故事,即只看到了故事是如何講述的,至于故事深層作者想要說些什么我們還得進一步分析,看看文章的聚合層面的安排能揭示什么。
二、聚合關系層面的《大師與瑪格麗特》
縱向聚合關系,它是“指特定句段中的詞與‘現在沒有出現的許多有某種共同點的詞,在聯想‘記憶力作用下構成的一種集合關系”。這是一種垂直的共時的關系。這—關系雖然沒有在現時話語中出現但它存在著并決定著現時話語中出現的詞的意義。
《大師與瑪格麗特》在縱向上的布局由兩個層面組成:“在超自然的層面上,主角有約書亞(耶穌),撒旦(魔鬼沃蘭德),撒旦的隨從(有時以小丑的身份出現),還有總督比拉多,這些都是神話或經書中的不朽存在;而在世俗的層面上,主角有大師和瑪格麗特,另有‘莫文協的詩人作家,有醫生、職員和市民,等等。”(米拉·金斯伯格)
作者在這個方向上的安排,在把故事中人物分類的同時,還收到了對比的效果。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共處在現實中時,他們看待事情的不同觀點也在他們的言行舉止間顯示了差別。本來是代表惡的魔鬼一方反而在替上帝顯示善,魔王沃蘭德派隨從去做的事情都是為了懲罰人的罪惡,在令人哭笑不得的行為中表露出的卻是對人的諷刺與嘲弄。而上帝在他所信賴的人民中看到的大部分卻是丑陋,他們沒有信仰、貪婪、嫉妒……在這種對比中作者的矛盾心情也顯露了出來:愛人還是恨人。現實是屬于人類的,它要由人類去建設,它的未來依賴的還是人類,但是現實中的人卻表現出種種丑態,讓人對未來失去信心。但是,上帝還在,心靈純潔的人如大師和瑪格麗特,他們依然對未來滿懷熱情。不過最后他們被上帝召喚去的結局值得我們深思,為什么要想讓他們幸福就得去另外那個世界?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看:在世俗層面生活的人也可以出現在超現實的層面上,獲得不同尋常的體驗,暗示了人對于深邃精神世界的探尋與渴望,對于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失去的另一種依賴:精神支柱。
三、橫組合和縱聚合的關系網絡
從語言的橫向組合和縱向聚合關系,我們可以看出,在索緒爾看來,語言符號的意義并不是它們本身的內容所規定的,而是在一個縱橫交織的關系網中,被語言的結構所規定的。在語言中,任何—個要素的意義都取決于它與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異與對立,用索緒爾的話說:“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因此索緒爾提出語言是一種關系網絡,必須從整體結構上來探討語言符號。
從文本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橫向組合關系和縱向聚合關系總是交錯在一起的,它們既是對立的,因為它們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上各自演繹自己;同時它們又是互補的、交錯的。橫向的情節線索總是在縱向的各色人物的行為中向前發展的,而不同人物又總是出現在不同的情節中。比如魔王沃蘭德,他在莫斯科演出了一場荒誕的鬧劇。劇中人戲劇性的死亡或消失都是出自他的命令,雜耍劇院的虛幻的一幕也是拜他所賜,單是這一情節就涵蓋了劇中所有人物。同樣大師與瑪格麗特他們出現在文本的各個情節中。這種網絡錯雜的結構還只是文本的表層結構,這種復雜性之下隱藏的是什么才是我們著重探討的東西。
在小說卷首,布爾加科夫引用了《浮士德》中的一段話:“你到底是何許人?”“我屬于那種力的一部分,它總想作惡,卻又總施善于人。”可以說是對沃蘭德性格的形象說明。他在莫斯科的出現引起的種種的荒誕現象,揭露了人們的貪婪、丑惡等行為。社會上不公正的現象,比如官僚階級的腐敗,官場上的形式主義作風,一切丑陋的社會內幕都被呈現出來。另一方面,他也做些美好的事,大師和瑪格麗特的結合就是在他的幫助下實現的。所以,魔王以惡的方式對待作惡的人,又以善的方式幫助人。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安排文本的心思是如何完美地體現在這兩種關系的復雜對立與交錯中,同時我們也理解了在這復雜表面下的文本的深層內涵:善與惡的糾結,善最終戰勝惡的美好愿望,作者本人對自己信仰的堅持。因此索緒爾的二元結構對立是闡釋和解讀這部集圣經故事、神秘幻想和莫斯科現實生活為一體的20世紀的俄羅斯具有魔幻魅力的現代主義巔峰之作的重要途徑之一。它為我們開啟了一個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