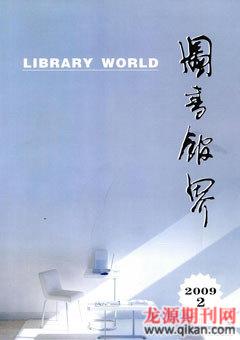新時期:實現城市街道圖書館的可持續發展
孫 冰
[摘要]街道圖書館是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薄弱環節,一直難以擺脫“建設一衰敗一再建設”的命運。新時期,北京、上海、蘇州等城市探索街道圖書館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其經驗值得學習借鑒。
[關鍵詞]街道圖書館;圖書館服務體系;總分館
[中圖分類號]G258.2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5—6041(2009)02—0013—03
街道圖書館是城市公共圖書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卻一直是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薄弱環節。作為公共圖書館服務向基層延伸的重要觸角,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普遍均等的公共圖書館服務是否能真正實現。在實現了縣縣有圖書館的目標后,我國將進入街道/鄉鎮以及社區/鄉村圖書館的建設階段。本文將圍繞城市街道圖書館展開敘述,分析街道圖書館的曲折發展歷程以及21世紀出現的新模式,總結經驗,希望能對我國的街道圖書館事業發展有所幫助。
1街道圖書館與社區圖書館的區別
在我國,公共圖書館按照行政級別可劃分為省級、市級、區縣級、街道/鄉鎮、社區/鄉村五個級別。其中縣級及以下的圖書館被稱之為基層圖書館。在一些文獻里,常常把街道圖書館和社區圖書館籠統地稱為社區圖書館。
筆者認為街道圖書館與社區圖書館不能混為一談,因為二者在建筑規模、服務對象、服務內容,建設主體上都存在巨大差別。街道圖書館的建設主體是街道辦事處,通常建立在街道文化站內,而社區圖書館則多由社區居委會籌建管理。社區圖書館在層級上應屬于街道圖書館的下一級。
雖然我國個別發達城市的社區圖書館已經開展得有聲有色,但就廣大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來說,與之相適應的基層圖書館發展重點應在街道一級。在街道圖書館健康發展的基礎上,再進一步考慮向下延伸至社區,最終構建一個城市完整的“市-城區-街道-社區”四級公共圖書館服務網絡。
2街道圖書館在城市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公共圖書館獨立或通過合作方式提供的圖書館服務的總和。[1]而街道圖書館是城市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發揮巨大作用。原因如下:
(1)從基礎設施架構的角度看,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是由一個個的圖書館實體構成的,以街道圖書館為代表的基層圖書館是整個服務體系不可或缺的末梢組織。
(2)近年來,“普遍均等”成為公共圖書館服務的目標。而要實現普遍均等,必然要求提高基層圖書館的覆蓋率。正如于良芝教授分析的“文化基礎設施的覆蓋是普遍均等服務的基礎。只有當文化基礎設施的覆蓋率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保障普遍均等服務和公眾的基本文化權益才會成為實實在在的目標。”[2]街道圖書館因其接近居民聚集區,方便居民就近利用,是提高圖書館覆蓋率的有效途徑。
(3)街道圖書館在城市圖書館服務體系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一個完善的體系應分為若干層次,圖書館服務體系亦然。作為“市-城區-街道-社區”四級公共圖書館服務網絡的重要節點,街道圖書館應該承擔輔導社區圖書館的職責。如果把整個城市圖書館服務體系比喻成一棵大樹的話,那么市館是樹干,城區館是枝干,街道館就是枝條,而社區館就是樹葉。如果沒有街道館,而是由城區館或市館直接負責廣大社區圖書館(室)的工作,會導致市館和城區館工作壓力超荷,不利于整個服務體系的健康發展。
3我國城市街道圖書館的發展歷程和現狀
3.1我國城市街道圖書館的發展歷程
我國的城市街道圖書館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其發展過程卻一直很坎坷,并沒有茁壯成長。從上海市街道圖書館的發展歷程可窺視出眾多城市街道圖書館的發展境況。
上海市早在1958年就出現了民辦的街道圖書館。大躍進時代,街道圖書館的數量激增。文革時期書封人散。上世紀80年代,街道文化事業得到恢復。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初,由于受全民經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沖擊,街道圖書館不斷被蠶食。[3]上世紀90年代末“精神文明建設”興起,為了迎接各種文化考核與評估,街道圖書館枯木逢春,又得到了注資與關注。[4]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國家的綜合國力不斷提升,文化事業也日益受到重視,在一系列文化政策的推動下,街道圖書館事業迎來了新的發展契機。2005年,上海首次將街道圖書館納入總分館體系,標志著發展觀念及發展模式的創新與改變。[5]
筆者通過實地調研發現,北京市西城區的街道圖書館也有著類似的曲折發展經歷。西城區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出現了街道圖書館。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同樣受到市場經濟浪潮的沖擊,街道文化事業開始走下坡路,大部分街道館處于維持狀態。但從2002年起,西城區開始以“街區共建”的模式發展街道圖書館,突破了“發展-衰敗-再發展”的宿命。
此外,筆者以文獻調研的方式了解到:南京、大連、常州、無錫等城市街道圖書館在上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也有著類似的經歷。
3.2我國城市街道圖書館的現狀
街道圖書館由于依附于街道辦事處的文化站,很容易受到各自形勢政策的影響。歷史上,“知識工程”“萬冊圖書室”“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等政府倡導的文化行動,都曾經給街道圖書館帶來短暫的發展生機。評估定級活動更是在短時期內刺激了街道館的發展。但這一系列的活動只是給街道圖書館的發展帶來了短時期的投入和虛假繁榮,綜觀各城市街道圖書館的生存現狀,它們普遍存在以下問題:
3.2.1經費得不到保障。經費問題一直是制約街道館發展的根本問題。街道館的經費來源雜且不確定,一般來源于街道辦事處的行政辦公費,或街道辦預算外創收留存資金,或是街道文化站以文養文的收入,這些來源都具有臨時勝和任意性。經費短缺又導致一系列的問題,包括館舍條件簡陋,圖書資料陳舊,人員工資待遇底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街道圖書館的服務能力。
3.2.2嚴重依賴“人治”而非“法制”。由于缺乏法規文件的規范和管理,街道圖書館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其所屬街道辦事處領導的重視程度。街道領導重視文化建設,街道館開展的就好;領導不重視,其地位便岌岌可危。街道圖書館的生殺大權完全掌握在領導者的手中,處于“人治”狀態。所以,很多人寫文章呼吁街道領導重視文化事業,其實都沒有脫離“人治”的思維模式。正因為“人治”,使街道館的發展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4探索城市街道圖書館的長效發展機制
如何使街道圖書館在今后的發展中,避免出現屢建屢衰的現象呢?這就提出了長效發展機制問題。最近幾年,北京、上海、蘇州等城市在街道圖書館發展中所探索出的新路,突破了傳統觀念,取得了令業界關注的成績。他們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
4.1法律法規的保障
街道圖書館要獲得持續穩定的經費,必須改變
依賴街道領導者的情況,從“人治”走向“法制”,依靠法律法規來保障基層圖書館的發展條件。
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圖書館專門法,但是不少地區已頒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地方性圖書館條例。例如《北京市圖書館條例》規定“本市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公共圖書館的經費列入本級財政年度預算,并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逐步增加投入”,并且規定街道圖書館的建筑標準“面積應當達到100平方米以上,閱覽座位應當達到30席以上”(第35條),其法規責任也規定明確,如果街道辦事處沒有按照規定建設發展街道圖書館或挪用經費,文化行政主管部門可以對負有直接責任的主管人員給予行政處分。在該條例的規范下,北京市各城區街道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均得到了保障。另外,在《浙江省公共圖書館管理辦法》和《上海市公共圖書館管理辦法》中,也都有條款涉及街道圖書館的經費來源、開放時間、藏書數量等要求。
從文獻調研來看,凡是建立了“圖書館條例”或“管理辦法”的地區,街道圖書館的發展水平都領先于沒有法規保障的地區。
4.2建設主體上移,提高財政支持力度
按照行政區劃、層層設館、分級管理的體制,街道圖書館的建設主體和管理主體是街道辦事處。但街道辦作為基層政府,財力有限,街道圖書館的經費就常常得不到保障。而公共圖書館作為公益性服務,不可能利用“以文養文”的錯誤理念來自籌資金,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找到持續的經費來源。
為了改變基層政府建設基層圖書館的弊端,有些城市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新的模式,把街道圖書館的建設主體上移到區級或市級政府,讓財政能力強的政府來支持街道圖書館的發展。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北京市“街區共建”街道圖書館的模式。2002年《北京市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基層文化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提出了區政府對基層文化建設的責任。隨后,北京市西城、東城、豐臺和崇文等多個城區就按《條例》的要求,由區政府支持街道圖書館的建設。
最早實施“街區共建”街道圖書館的是西城區。西城區政府下發《關于加強街道圖書館建設的實施意見》,規定街道圖書館不再僅由街道辦事處承擔,而是由該城區政府和街道辦事處共同建設,從而把街道館的建設主體部分上移到了城區政府。具體分配是:街道辦事處負責提供開辦街道圖書館所需的房屋場地、坐椅設備、日常經費和人員工資;區政府設立專款,每年提供30萬元的街道館購書費。圖書采編業務由西城區圖書館承擔。街道圖書館的購書經費得到保障,每月可以得到數百冊新增圖書。
深圳在建設“圖書館之城”的過程中,基層圖書館的初期設置經費來自城區政府。例如在福田區,街道圖書館就由城區政府委托給城區圖書館建設,城區財政為每一個新建的街道分館投入15萬的設置費,另外每年城區財政另撥10萬元作為運行經費。此外佛山市禪城區聯合圖書館的實施中,區街共同合作建設了瀾石街道圖書館和環市街道圖書館。
各地的探索和實踐表明,街道圖書館的建設主體上移是一種發展趨勢。
4.3納入總分館體系
除了借助城區級政府的財政支持外,街道館的可持續發展也離不開城區級或市級圖書館的業務支持。按照過去分級建館、獨立管理的體制,每個街道館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圖書采購、編目、借閱、讀者活動都需要負責,服務質量受到街道館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限制。
近些年,嘉興、蘇州、佛山、北京、上海等城市,都以開放的心態整合區域內的圖書館資源。街道館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的個體,而是以分館的身份加入到城市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中,不再進行專業要求較高的采編工作,僅進行讀者服務工作。這樣,中心館(市館或城區館)可以借助街道館的網點來延伸服務,街道館則可以借助中心館的資源和技術能力來提升能力。[6]
盡管目前我們國家出現的“總分館”體系還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總分館形式。但這些以分館形式運作的街道館已經開始彰顯公共圖書館的精神。實踐證明,街道館納入總分館體系,不僅有利于街道圖書館本身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是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的合理方式。
[參考文獻]
[1]于良芝,邱冠華,許曉霞.覆蓋全社會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模式、技術支持與方案[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3.
[2]于良芝.建立覆蓋全社會的公共圖書館服務體系[J].圖書與情報,2007(5):23-24.
[3]吟荒.上海市街道圖書館事業的調查與思考[J].圖書館雜志,1990(1):22-27.
[4]徐家齊,浦保清.上海市街道鄉鎮圖書館新貌[J].圖書館雜志,1999(6):29--30.
[5]王世偉.城市中心圖書館向社區基層延伸的理論思考與探索實踐[J]∥城市圖書館發展論叢.上海:上海科學院出版社。2006:13.
[6]李東來.城市圖書館集群化管理研究與實踐[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