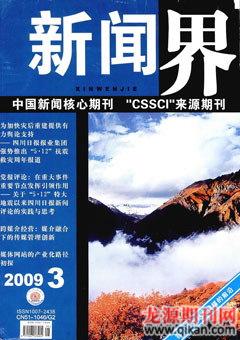從生態學視角解讀西方政治傳播的生態鏈
潘祥輝
摘要本文運用生態學觀點對考察西方政治傳播的生態鏈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生態學政治傳播生態鏈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識碼A
一、作為動態生態系統的政治傳播
我國傳播學者邵培仁教授認為,政治傳播是指“政治傳播者通過多通道、多媒體、多符號傳播政治信息,以推動政治過程、影響受傳者的態度與行為的一種對策。”這一定義突出了政治傳播的特性:傳播內容主要是政治信息,傳播的目的在于影響和推動政治過程,和其他傳播行為相比,政治傳播更加關注受傳者的態度和行為改變。
英國傳播學者麥克奈爾則將政治傳播簡潔地表述為“關于政治的有目的的傳播”。這一定義涵蓋了:
所有政客及政治行動者為求達到目的而進行的傳播活動。
所有非政治行動者對政治行動者作出的傳播活動,例如選民及報紙評論員。
所有在媒介中涉及以上政治行動者的新聞報道、評論及政治討論。
這一定義將政治行動者的政治傳播與非政治行動者的傳播及媒介產品都納入政治傳播的考察范圍。可以看出,政治傳播關注的其實是傳播學的“五w”在政治領域的運用,即政治傳播者、政治信息、政治傳播渠道、公眾以及政治傳播效果等等。它涉及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完全可以視作一個動態的生態系統。
生態系統(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圍或區域內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種類的動物、植物、微生物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群落內不同種群生物之間不斷進行著物質交換和能量流動,并處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響的動態平衡之中。這樣構成的動態平衡系統就是生態系統。從生態學的觀點來看,政治是一種生態,傳播也是一種生態。
政治生態可以理解為政治系統內部各要素及政治系統與自然、社會環境的關系。政治生態的特點有二:
首先,政治生態是一個系統。這個系統包括參與政治的主體、政治機構、政治規則、政治環境等諸多次級系統。按照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和鮑威爾說法,政治系統是指“構成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它不僅包括政治機構如立法機關、法院和行政部門,而且包括所有結構中與政治有關的方面,其中有親屬關系、社會等級集團等傳統結構,還有諸如動亂之類的社會非正規現象,以及政黨、利益集團和大眾傳播工具之類的非政府組織。”
其次,政治生態是一個“層級結構”與“循環過程”的統一。和生態系統中有生物個體、群體、群落一樣,政治生態系統也是一個有機聯系的層級系統。現代政治體系基本呈現三級化的結構模式:(1)個體公民;(2)作為“中介”的非政府組織和團體;(3)作為國家或公共權力代表的政府。在現代政治生活中,公民被組織在各種不同團體之中,通過不同的渠道形成政治輸入,而政治組織、社會團體以及大眾傳媒等非政府機構是公民進入政治體系的,形成政治輸入的中介,即所謂的“Gate Keeper”。政治生態系統主要在“公眾一守關人一政府”三個次級系統間形成關聯與互動。
傳播生態則指“社會信息傳播系統各構成要素之間、各構成要素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社會信息傳播系統與其外部環境之間關聯互動而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的結構狀態。”和政治生態類似,傳播生態的內部要素之間,傳播生態與外部環境之間存著復雜的互動與制約關系,這種關系是動態的、變化著的,每一個因子的改變都將引起整個系統的結構的改變。
政治生態是一個系統,傳播生態也是一個系統,兩個系統之間的交叉結合,相互作用。政治生態的形成可以影響包括媒介生態在內的一切社會系統。政治生態對傳播的制約不言而喻,不僅體現在宏觀的傳播體制上,也體現在傳播的內容、方式及效果等微觀方面,可以說,政治生態構成了傳播的最重要的生存環境。同樣,傳播生態對政治生態的影響極大。在政治日益媒介化的今天,大眾媒介在政治生態的形成和變異中起著越來越關鍵的作用。正如麥克奈爾所講的“縱觀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只要居問政治(Mediated Poltics)成為了民主機構的主要模式,那么傳媒地位的日漸重要就構成了一個普遍特征”此外,由于不同的媒介傳播特性的不同,對政治傳播的影響也不一樣。歷史上每一次新的傳播媒介的崛起都會對政治生態形成沖擊,影響政治生態的改觀。
二、政治傳播的生態鏈
麥克奈爾對政治傳播的要素進行了細分,對我們理解政治生態與傳播生態的關系有著直接的幫助。在麥克奈爾看來,政治傳播有三個主要要素分別是:政治組織、受眾和媒體,其關系如下圖所示:

如果將政治傳播的這些元素與互動納入到生態學的視野考察,我們可以發現三者間構成了一個生態鏈。生態學告訴我們,生態系統是由非生物環境、生產者、分解者和消費者四個基本成份構成的。我們若將生態系統的四個基本構成成分“非生物環境、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對應于政治傳播的話,我們能夠發現政治傳播的生態鏈:非生物環境相當于政治傳播的外部環境,而后三者相當于政治傳播的內部參與主體。政治組織(特別是政府和政治家)在政治傳播生態中所起的作用相當于生態系統中“生產者”的作用(生產信息),媒體則相當于生態系統中的“分解者”(取舍和解讀信息),而受眾者相當于“消費者”(對信息進行消費和使用)。
首先,政治組織及政治家相當于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生產者”。在麥克奈爾的傳播元素中,政治組織是主要的“政治行動者”,包括政府、政黨、公共組織、壓力集團以及恐怖組織等。政治組織是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最重要的信息生產者,有的組織如政黨有壟斷政治信息的天然優勢,有的組織如壓力集團和恐怖組織則相對處于信息生產中的弱勢,為了生產信息,它們往往通過游行、爆炸等非常規手段來控制信息的生產和傳播。政治家是政治行動者中的個人,在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政治家由于掌握了信息的生產權力,故在對政治傳播中處于主動地位;但另一方面他又要借助于媒介的傳播渠道來樹立形象,傳達政治主張以達到政治目的,故又要倚重于媒體。在政治傳播中,政治家傾向于趨利避害,積極傳播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信息,而全力阻止對自己不利信息的傳播。美國記者馬文-卡爾布宣稱:民主已經墮落到了“媒體一政治”時代。在這個時代。政治角色無一不會考慮新聞媒體對政治的作用。“任何一個在白宮、國會山、或者五角大樓作出重大或是微小的決定,都不能不把新聞的因素考慮進去。要想把任何一種觀點‘賣美國老百姓,首先需要媒體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傳。”當然,政治家處心積慮生產的信息媒體不一定照單全收,媒體對政治家的反制作用到底有大,取決于媒體在整個政治傳播系統中的獨立地位。
其次,可以將媒體看作是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分解者”。媒體是政治傳播生態中的第二個重要元素。如果說
政治家和政治組織在政治傳播生態中主要扮演“信息初級生產者”的角色,那么媒體的功能則在于對信息進行加工、分解,在此基礎上向公眾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說,媒體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動者”。“媒體以及從事媒體工作的人也應當被視為重要的政治行動者。這不僅僅因為他們把政治組織的信息傳遞給了公眾,還因為他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新聞生產方式以及對事件的解釋改變了信息本身。”正如生態系統中需要分解者一樣,沒有媒體信息分解者的作用,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也無法維持平衡。媒體的分解者角色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第一,政治家或政治組織等政治行動者必須通過媒體向目標受眾傳遞信息。不管是政治綱領、政策綜述,競選呼吁,還是壓力集團的活動或者恐怖主義行為,如果沒有經過媒體報道并且為受眾所接收,那么就沒有任何政治意義,更不要說產生有效的政治交流了;第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媒體不會不加選擇地報道政治家生產的信息,即便總統也不例外。一般來說,總統處于政治信息生態鏈的上端,但在民主社會,總統的信息同樣受制于媒體。有人研究過,總統的發言媒體是否報道,如何報道,取決于三個條件:一是總統的媒體地位。如果總統正處于任職早期而且能夠體現強大的媒體形象,新聞就更有可能對總統自己選擇的信息加以強調;二是場合越莊重或問題本身越重要,總統的信息越容易獲得關注。最后,可預見的中間分子及公眾的支持越多,總統的信息就越會得到凸顯;第三,媒體也不會以一種不偏不倚的方式簡單地報道政治領域中發生的一切,因為媒體對政治事件的敘述充滿了價值判斷、主觀臆斷與偏見。正如凱德(Kaid)所指出的,政治“事件”由三個范疇構成:其一是客觀存在的政治事實,真實發生的政治事件;其二是構建的事實,即媒體報道中的那個事實。其三是一個主觀的政治事實——政治行動者與公民認識到的政治事實。主觀政治事實在政治行動者和公民的腦海中的形成與媒體構建的事實息息相關。媒體在分解信息重新建構的過程中會受到媒介內部組織和媒介語法規則的影響,也會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在分解與重新建構的過程,可能會歪曲政治組織等政治行動者所制造的信息。托德·吉特林以上世紀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SDS(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后得出結論:獲得媒體的報道和讓媒體明白無誤地傳遞你對事件的定義不是一回事。新聞報道往往避重就輕,簡化從屬集團的活動,僅僅關注引人注目的方面,卻忽視了對問題的解釋與辯論。這也是政治傳播生態中媒體的信息分解者角色不容忽視的突出表現。
再次,可以將受眾視為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消費者”。在生態系統中,處于“消費者”地位的生物只能直接或間接地依賴于生產者所制造的有機物質,但消費者在物質循環和能量交換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對其他生物也有一定的調節功能。這與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公眾(或受眾)的地位相似。在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公眾是政治家傳達政治主張的對象,說服的對象,也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和消費者。在政治傳播中處于“終端”地位,施拉姆說大眾傳播事業的責任問題“乃是媒體、政府與大眾三種力量之間的微妙平衡關系。完成傳播方面所必須完成的主要責任在于媒體,基本義務則屬于公眾。”他強調的是公眾的“義務”地位。和媒體與政治家比起來,公眾的確似乎處于弱勢地位。正如班尼特所說,在政治傳播過程中,公眾面臨著一個兩難境地:“如果他們忽略,或者不再意制造新聞的官員和輿論領袖所說的話,那么他們就可能被孤立,而不能形成在民主國家中最為重要的公民資源——輿論。相反,如果人們克服了政治疑慮,成為公眾中的一部分,那么他們又必須調整自己的觀點,以保證與媒體的一致。”在班尼特的眼中,公眾似乎完全沒有辨別能力。政治傳播對受眾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至今仍存爭議,不管是強大效果論、適度效果論還是無效果論等,都能找到其證據。賴特·c·米爾斯(C·Wright·Mills)就否認受眾會被媒體操縱的看法。在研究了1948年杜魯門和杜威的競選后(杜威獲得大眾傳播媒體的廣泛支持但最終落選),米爾斯得出下面的結論:“關于美國公眾的生活,任何假定大眾傳媒能夠完全控制和操縱輿論的觀點都是不現實的。在公眾中有一些影響力在起作用,它們獨立于這些傳播媒體,能夠應時地反對這些媒體的意見。”因此,在承認受眾受到政治家說辭和媒體信息制約的前提下,我們也要承認公眾不會是一個被動的接受者,這已為大量的研究所證實。公眾會反過來影響和制約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的政治行動者如政黨和政治家。公眾可以通過手中的選票來決定他們的命運;公眾也可以不買或不看媒體報道的行動影響媒體的生存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傳播生態系統中,公眾(受眾)的素質起著決定性作用。一群受過良好教育、有著理性認知能力的公眾(受眾),對于政治傳播生態的持續建康發展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不僅因為其對政治的積極參與,也在于其對于政治的認知,對政治傳播的了解更為清晰、全面,更容易辯明是非。相反,一群烏合之眾更容易成為政治和傳媒操縱的對象。
總之,在“居間政治”或說政治媒介化成為事實的今天,政治傳播的過程錯綜復雜。傳播生態與政治生態互相滲透。互相影響。傳播主體與傳播環境,政治主體與政治環境互相交叉。交流與博弈不僅存于政治傳播的參與主體與外部環境之間,也存在于政治傳播的各參與主體之間。從傳播生態學的視角看政治傳播,其意義也許僅僅在于打開了另一扇觀察的窗口,有助于我們理解政治傳播的復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