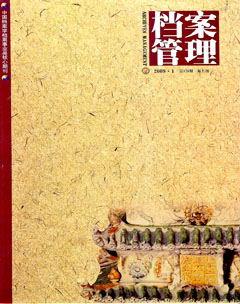蒲公英
YJCO212
故鄉的春天,是令人難忘的。原野上。青草還沒有露出綠意,這里,那里,蒲公英便露出了小小的芽尖,不幾天,就長出了幾片帶鋸齒形的葉片。故鄉的大地,捷足先登的蒲公英,確實是春天的第一個綠色使者,
三年災害雖已過去,極度貧困的陰影仍然籠罩著我的故鄉。鄉親們不會忘記。在那“苦春頭”的日子里,是蒲公英幫了人們的大忙。
有一年,我家糧食快沒了。寥寥無幾的“返銷糧”又沒有到來,幸虧我父親為生產隊做飯,每天偷偷摸摸地揣回幾個粗糙的高梁面窩窩頭,再熬一點稀得能照人的小米粥,這便是家中的早點了。晚餐,也許人們認為即使是吃好的,也在睡夢中自白地消耗掉了。所以,出土不久的蒲公英就唱主角了。
我家的晚餐常常是用蒲公英做的菜團。
母親把洗凈的蒲公英在菜板上剁碎,裝到盆里后,加上少許的玉米面和糠,再澆微量鹽水,攪拌均勻,攥成團狀,在玉米面盆里滾上幾圈,讓菜團四周沾上一層干玉米面,放鍋中一蒸,一頓晚飯就做好了。
有時碰巧家中存有一點土豆制作的淀粉,這可派上了大用場。把菜團在淀粉盆里滾幾下,蒸熟打開鍋一看,只見一個個半透明的菜團溜光锃亮,猶如精美的工藝品,不知內情的人真猜不透是什么高級食品呢。咬一口,卻是一團野菜。當時,吃著這“金玉其外”的野菜團,心里想,什么時候能夠吃上一頓哪怕是有一半兒玉米面和在里面的菜團也就心滿意足了!
那陣子,每天放學后,書包往墻上一掛,似乎第一件事就是去剜菜。故鄉的大地總是慷慨的,田頭,地角,不管肥沃與貧瘠,凡有小草的地方就有蒲公英的影子。
呼朋引伴,人多的時候,便劃分“勢力范圍”,你占一個地方,他占一個地方,有時因超越疆界而產生糾紛;當然,更多的時候是和睦相處。偶爾,也有因貪玩而剜得太少的怕回家挨大人叱罵,大家都去支援他一部分的義舉。
蒲公英以它金色的花朵,點綴著故鄉的春天。不久,金黃色的花朵魔術般地變成一團松散的絨球,呈銀白色。這意味著種子的成熟。微風吹來,這些成熟的種子各自打著別致的小傘,四處飛揚。世世代代。繁衍不絕。
這種誘人的情景,很能觸動文人畫士的靈感。遠方游子的情思。然而,在我的故鄉。卻沒有幾個人知道“蒲公英”為何物。不知從什么時候起。人們把這種野菜稱為“婆婆丁”。
蒲公英還是一味解熱鎮痛的良藥呢。當時。屯子里有一對老夫妻。男的姓閆,六十多歲,不知叫什么名字,大人孩子一律稱之為“老閆頭”。老夫妻本有一子,分家另過,也不怎么管兩位老人。這樣。老夫妻的生活很是窘迫,對其兒子的舉動,村人頗為側目。
有年春天,藥店收購蒲公英,老夫妻得到消息后,雙雙出動。村東,村西,南坡,北嶺,大肆忙了起來,把挖來的蒲公英裝到袋子里,由老頭背著,送到離家二十多里的藥店去出售。我在放午學的路上有好幾次恰好碰到老閆頭到藥店去。看到老人滿臉皺紋,滿頭白發,彎曲的背上又壓著一麻袋蒲公英,累得呼呼帶喘。孟子期盼的理想社會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這種斑白者負載行于路的情景,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禁不住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據說,那年春天,老夫妻的生活中出現了好久沒有的歡笑聲。
人的感情真是怪。走進社會后,榮辱升沉,人海蒼茫,嚴峻的現實畢竟不能使我們永葆一顆童心,然而,故鄉原野上開著金黃色小花的蒲公英,卻始終搖曳在我的記憶深處,
近些年,越走越遠,難得回幾次故鄉。即使回去,不是錯過季節,就是行色匆匆。與蒲公英竟未謀一面。今年三月,因參加一位朋友的婚禮,我們全家又回到離別已久的故鄉了。
到家第二天,晚飯前,不顧家人的勸阻,我帶上一把剜菜刀,挎著竹籃,領著20歲的女兒,來到村外的荒地上。這時,青青的野草剛剛覆蓋大地。我一手拿刀,一手提籃,作尋找狀,女兒跟在我身后,挺胸抬頭,恰似一位驕傲的公主。
奇怪,我們從地南頭走到地北頭,又從地北頭走到地南頭,竟未能找到一棵蒲公英。蒲公英呢?難道你真的消失在思鄉的夢里了?妻子見我們長時間沒有回去,竟尋路而來,見此情景,說:“你們連腰都哈不下,怎么能找到呢?”果然,彎下腰在草叢中細細尋找,不一會兒,就挖了半籃。
說來也巧,回來的前一天下午,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同學,現任鄉武裝部長。這時,他正為來此視察的一位省軍區政委安排午飯。原來這位政委非要吃農家飯不可,想喝苞米碴子粥,吃“婆婆丁”蘸大醬。無奈,跑了不少家還沒有著落,把我這位老同學急得團團轉。
怎么能找到呢?事過境遷,故鄉的蒲公英,你早已成了豬羊的飼料和雞鴨的夜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