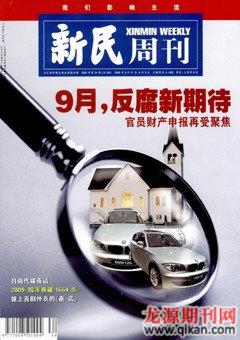依法治國才能化解檢察之尷尬
王 琳
一段時間以來,“被”字句風行網絡。舉凡“被自殺”、“被增長”、“被統計”、“被就業”等等,都曾引發輿論熱議。
從上述例證看來,“被××”的,均為弱勢一方。在強者占據輿論高地時,弱者只好以文字上的戲謔來進行另類的言論表達。從民意的宣泄來看,“被××”與“草泥馬”等如出一轍,均是作為“弱者的武器”而在網上“一詞風行”。在這些流行語的背后,實則有著可怕的社會認同。
強弱總是相對而言的。有的公權力相對于民眾是強者,但相對于更強的公權力又成了弱者。如此一來,公眾眼中的強者在這個“被時代”里,也難逃“被××”的命運。比如貴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近日也有了“被××”的最新例證。
據《檢察日報》8月21日報道,近日印發的《關于開展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的意見》中,最高人民檢察院被確定為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該《意見》表明,用2年左右的時間,集中開展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深挖工程質量問題和安全事故背后的腐敗問題,重點查辦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利用職權以權謀私甚至索賄受賄的大案要案。
細心的讀者可能看到了其中“被確定”這樣的字眼,一個“被”字,凸顯出當下檢察機關在行使法律監督權時的無盡尷尬。本來,在中國的現行憲政架構中,檢察權與行政權、審判權一并同列人大之下的三權之一。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行政機關一樣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并向人大報告工作。檢察機關依法行使檢察權,這是法治的應有之義,也是權力分立與制衡的邏輯所在。工程質量問題和安全事故背后的腐敗問題,只要涉嫌犯罪,就在檢察機關的法定管轄范圍之內。對犯罪的調查與追究,是一項主動的國家權力。檢察機關行司法反腐之職并不需要“被確定”。而問題恰恰是,如果沒有“被確定”,檢察機關還真無法加入到“工程建設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中去。
類似的“被確定”其實由來已久。在中國的反腐體制中,檢察機關僅僅被認為是“職能部門”之一。雖為法定的反腐機構,但檢察機關的重要性在實際的權力運行中并未凸顯出來。現行體制的官方表達叫做“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紀委組織協調,部門各負其責……”,將諸多黨政部門均囊括其中的這一體制,使得檢察機關在行使法律監督職能的過程中不得不面對其他權力的非法治化制約。于“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的潛規則之下,一種異化的權力實踐將檢察機關推到被邊緣化的尷尬位置上,檢察權事實上被“弱勢化”了。在不少時候,檢察機關不但要完成其他部門已經完成了案件調查之后的司法程序包裝,還要被迫接受更強勢的權力已經有了決定的案件處理意見。
可資證明檢察機關“被××”的另一例證是:近段時間以來沸沸揚揚的跨國公司賄賂門事件中,作為法定調查機關的檢察機關身影全無。倒是涉案的幾家企業從危機公關的角度不斷向外發布“辟謠”的信息。而常識告訴我們,這種涉案單位的“內部調查”事實上并無公信力可言。“賄賂門”仍然處于云遮霧隱之中。
到了8月21日,國資委有關負責人也就美國控制組件公司(CCI)向中國多家企業行賄一案作出回應,表示國資委對此事件高度重視,并已成立專門調查組就此事進行調查。與此同時,檢察機關對此仍在沉默之中。
很難相信擁有法定的反貪污賄賂職權的檢察機關,當沒有得到某些強勢部門的“被確定”時,就只能等待。而在司法之外運行著的紀檢調查、行政監察調查等等,事實上凌駕于法定偵查權之上。這種反法治化的反腐體制,正是前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其一本近作中所批評的。肖揚甚至建言應重組反貪部門,新的反貪機構由人大選舉產生,向人大報告工作,但不搞票決制。這樣的設想未嘗不是擺脫檢察機關“被××”的可行路徑之一。只是問題在于,在行使法定職權上并不獨立的執行部門并不鮮見,若為擺脫“被××”故而一一交由人大選舉產生,可設想一下未來的人大將直管多少個機構?至少國土、質監、藥監、環保等容易“被××”的部門都得尋求人大的蔭蔽。
另一個更讓人憂心的問題在于,人大權就足夠強大到可能幫助這些執法部門和司法機關免于“被××”的影響嗎?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否也有“被××”而又無能為力的時候?
從理論上說,只有樹立法律的至上權威,依法治國、依法治權,職能部門“被××”的尷尬才會得到化解。培植法律信仰、完善權力制衡,只能從公權力出發。先有權力為法所治,權利或弱勢的權力才能免于強勢權力強加過來的“被××”。(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知名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