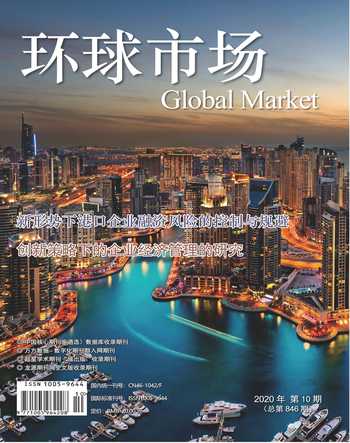化工設計中防爆電氣設備選型探討
張大嶺
摘要:一般化學爆炸(炸藥除外)及火災是由點火源、爆炸物特性和爆炸物與空氣的混合情況決定的,防爆就是從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由于電氣設備運行時表面會發熱,斷路器、接觸器、繼電器等斷開電流的設備動作時會產生電火花甚至電弧,故有可能發生電氣設備引起爆炸物的爆炸及火災事故。這就要求我們研究電氣設備引起爆炸及火災的機理,采取有效的預防措施及其提示注意事項,使其在特定的爆炸環境下正常運行,而不至于引起爆炸及火災事故。基于此,本篇文章對化工設計中防爆電氣設備選型探討,以供相關從業人員參考。
關鍵詞:化工企業;防爆電氣;設備選型;生產安全
隨著我國科技的快速發展,化工企業已經成為當今社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化工企業在運用設備進行生產的過程中會經過很多的工序,對其的操作要求和管理要求也較高,如果出現操作不當,很容易引起化學設備火災,滅火救援不及時或者措施不得當,出現爆炸,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甚至人員傷亡。因此,充分做好化學設備火災爆炸事故滅火救援對策十分重要。
一、加強化工生產安全的意義分析
通常來說,化工生產往往會使用大量易燃、易爆、有毒害性、有強腐蝕性的原料。如果要保障化工生產的正常運行,必須加強安全生產管理。若化工生產安全管理落實不到位,則會增大發生安全事故的概率。一旦發生安全事故,不僅會給化工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經濟損失,還會對公眾財產安全構成威脅。無論對于任何性質、任何規模的企業而言,保障生產安全都是第一要義。尤其是化工企業,必須加強安全生產管理。
二、爆炸形成條件和原理
易燃易爆物質狀態轉變速度很快,能量釋放過程中后會有高速的化學反應,爆炸形成的沖擊波會對物品造成嚴重的損壞。爆炸形成需要存在易燃物質,已經與空氣進地混合,而且存在著火源,這三個條件必須同時存在。在正常工作條件下,故障形成的火花、熱效應無法點燃介質混合物,該種電氣線路被叫作本質安全型電路,是一種重要的電氣防爆設備。而電氣設備在運行過程中,由于開路、觸點接觸等形成的電火花、熱效應,該種類型的電氣設備可以將火花能量控制在很低的范圍,無法將附近的易燃物質引燃,這需要控制好電路工作電壓和電流,對電氣元件參數進行限制,并配置可以快速切除故障的電路,可以達到本質安全性能。
三、化工設計中防爆電氣設備選型探討
(一)根據爆炸性環境危險區域選型
根據《爆炸性氣體環境第14部分:危險場所分類》(GB3836.14-2014)規定,設備防爆型式等于或者嚴于爆炸性環境危險區域的要求。0區(20區)危險性最大,要求最嚴格,1區(21區)、2區(22區)依次減弱。實際工程中能用于0區(20區)的防爆電氣設備當然也可以用于1區(21區)、2區(22區)的爆炸環境,只是經濟性差,但是反過來,只能用于2區(22區)的防爆電氣設備絕對不可以用于。區(20區)、1區(21區)的爆炸環境,因為性能上不滿足要求。
(二)化工設計中設備防爆的防護要點
短路保護。通常采用的短路保護措施是加裝熔斷器;這樣一旦系統電路發生短路故障,熔體就會迅速升溫而造成熔斷,從而使整個電路被切斷,以免對設備造成威脅。
(三)爆炸危險環境劃分的根據
為了準確地劃分爆炸物質的危險性,需要先深入了解易燃易爆介質的特點,還應該掌握生產設備的作用,工程技術人員需要將介質和電氣設備的安全性關聯起來,結合規范要求進行操作,從而可以使危險區域得到準確的劃分,這就要求參照相應的設計規范要求,并考慮到可以產生的后果。需要在保證化工企業安全生產的前提下,防止將一些生產區域爆炸危險的區域進行不合理的提升,這樣會使得防爆性能提高而增加投資。易爆區域的劃分需要結合爆炸源特點,對爆炸環境進行評估,再分析該區域的通風條件等影響因素,最后,合理確定該區域的等級。
(四)化工設計中防爆電氣設備管理具體措施
1.科學選擇防爆電路系統
防爆電路系統的選擇對于化工企業平臺設備防爆同樣至關重要。但是不同的設備的本質安全電路也各不相同。所以,在選擇設備的時候,必須要針對其安全防爆電路系統展開慎重篩選。有些設備的電路系統,能夠直接用于。類危險區域,從而使整個平臺的防爆性能得到強化;而有的則完全不能適用于企業。所以,必須要慎重選擇防爆電路系統。但需要指出的是,對防爆電路系統的選擇也應當兼顧其經濟性和安全性,這樣才能實現效益的綜合最優化。
2.防爆安全設備應用環境
化工電氣設備防爆安全技術應用中,可以將其具體應用環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是易燃易爆氣體環境,在化工生產中此類型環境較多,且安全隱患較大,是引發爆炸事故的重要原因;第二是可燃性粉塵環境,在化工生產中,可燃性粉塵也會產生安全威脅,需強化電氣防爆,保證化工生產正常進行;第三是化工成品運輸環境、存儲環境,生產出的成品也具有易燃易爆特性,在其運輸、存儲的過程中操作不當會引發爆炸,因此在此環境中需廣泛應用安全技術來達到防爆目的。
3.加強防火防爆培訓
防火防爆一直是化工企業乃至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一旦化工生產過程中發生火災、爆炸等安全事故,不僅會給化工企業造成無法挽回的經濟損失,還會對公眾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威脅。為此,化工企業必須加強安全事故預防管理工作。
四、結束語
電氣設備防爆不僅涉及電氣學科,還涉及化學、消防等多門學科,規程多,涉及的知識面廣應嚴把設備質量關,選用符合國家規范要求的設備,認真檢查防爆合格資質證明,同時做好定期檢查維護工作,確保防爆電氣設備處于良好的工作狀態。
參考文獻:
[1]王鑫.化工防爆電氣設備的合理選擇及運行維護方案分析[J].山西化工,2018,38(04):151-153.
[2]元亞明,周簪榮,沈建云,韓棟.化工企業爆炸危險場所電氣防爆安全檢測技術的探討[J].廣州化工,2019,47(08):178-180.
[3]杜超超.化工企業正確運用防爆電氣設備的方法與維護[J].石化技術,2018,25(06):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