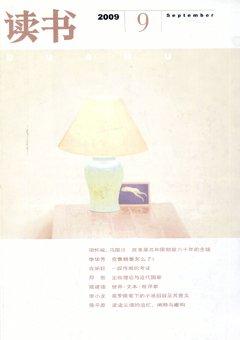改革是共和國財政六十年的主線(上)
項懷誠 馬國川
從山東大學到財政部
馬國川(以下簡稱“馬”):建國六十年來,一共是十任財政部長,您是第八任部長。
項懷誠(以下簡稱“項”):前三任都已經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擔任了三年的財政部長,一九五二年因為“新稅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評,然后由鄧小平同志兼任財政部長。當時鄧小平剛從西南軍政委員會調到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財政部長,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馬:李先念先后當了二十一年,是時間最長的財政部長。
項: 這三位都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任財政部長,所以他們都不在財政部辦公。鄧小平同志的辦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辦公室是在國務院。第四任部長是張勁夫,第五任是吳波。吳波從一九五二年起就一直是財政部副部長,后來他長期擔任常務副部長,主持財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們這茬兒人都是在勁夫、吳波、丙乾同志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
馬:您是山東大學畢業的?
項:我祖籍江蘇,后來跟著父母到上海讀書,一直到高中畢業。當時全國統考,一九五六年我考進了山東大學,學的是中文。我們那一屆擴招,就像現在的擴招一樣,不過那時是把在職的干部吸收進來,叫做調干生。調干生年齡都偏大,我們那一班里年齡最大的三十五歲,我算最小的,十七歲。
馬:在大學里,您想畢業以后做什么?
項:當時的學生,畢業以后沒有自我設計的問題,都是組織分配工作。我一九六○年大學畢業,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來“山大”挑人,我被選中了。
馬:您是學中文的,為什么會進計算機研究所呢?
項:原因是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有一個“俄漢機器翻譯研究組”,是當時非常先進的一個前沿性項目,對人員的要求是第一要懂一點外語,第二要懂一點數學,第三要懂得中文,還有就是要年輕的。
馬:您正好符合這些條件?
項:我想是吧,沒有人跟我說過。我報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學去學俄語,一邊進修外語,一邊開始研究工作。因為當時的技術水平不具備,不可能在短期內突破。一九六二年國家進行整頓,這個項目就下馬了。我們這一批研究人員里,一部分本來就是學數學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數學系畢業的),所以就留在計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語言的,就把他們送回到語言研究所去了。本來,計算所對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適,根據我的條件,組織部門認為我到大學里去教書可能比較合適,所以就找了很多學校,包括云南大學、黑龍江大學、內蒙古大學等等,叫我去教什么英語、俄語。因為它們看了我的簡歷,誤認為我是學外語的,我說,要我教漢語,可能還湊湊合合,俄語、英語我是教不了的。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愛人正懷孕,所以我不愿意離開北京。我就跟他們說,我在北京找一個工作就行了。
馬:不服從組織行嗎?
項:那一年在廣州召開的科技工作會議和戲劇創作會議上,陳毅受周恩來的囑托,向會議代表宣布要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當時知識分子的心情還是蠻舒暢的,組織部門對知識分子的分配也比較慎重,認為我的要求通情達理。恰好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樓開了個會,叫做“西樓會議”。會議要求加強稅收監管,決定在財政部稅務總局設立一個機構,加強對國有企業的財政監管。
馬:財政部招人,機會來了。
項:對,組織部門找我談話,問我愿意不愿意去?我當時沒有其他的要求,留在北京就好。一九六三年初我就到財政部工作了。從那時起,一直到二○○三年調離財政部,我在財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
在財政部成長起來
馬:從學中文到去計算所搞研究,然后又到財政部,這個彎轉得很大。
項:計算所搞一段時間,不可避免地要和數字打交道,這樣增長了很多知識。我在財政部稅務總局新設的“監繳利潤處”做辦事員,這個處負責監督國有企業利潤的繳納。
馬:假如當時把您分到云南或其他邊遠地區,中國可能就少了一位財政部長。
項:我進了北京,進了中央機關,在我這個年齡段的人里面,不是萬里挑一,而是幾千萬里挑一。“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財政部許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財政部“五七干校”勞動,我是一九六九年四月份去的,待了三年。
馬:主要做什么?
項:種棉花、種水稻,我干了一年農活,第二年就開始教書。財政部干部認為當地學校的教學質量不夠好,就為自己的子弟辦了一個中學和一個小學,把我調去當老師,所以叫我“老九”。我教的是中學,語文、歷史都教過。我們的教學質量確實比當地要好,因為老師都是正規大學的畢業生,有的還是留蘇的副博士。學生后來也都非常有成就。我當了兩年老師,一九七二年四月份又把我調回來,去預算司,當時預算司司長點了名要我。“文革”中,李先念還是財政部長,可是基本上“靠邊站”了,雖然沒有被打倒也管不了多少事兒。當時財政部實行軍管,殷承楨同志到財政部做軍管會主任。財政部名義上還是李先念領導的。殷承楨這個人非常好,是一個老紅軍。他對我們都特別好。當時他出差,點名要我跟著去,他們把我叫做“拐棍”,因為部隊的干部不懂財政業務,把我當他們的“拐棍”使。
馬:從資料看,一直到“文革”結束前一年,部隊才撤離財政部。
項:當時周恩來總理還在世,他說給你們財政部派一個精明能干的強將,派的是誰呢?就是張勁夫。張勁夫同志做了四年多財政部長,一九七九年到國務院當國務委員。
馬:一九七八年召開了“三中全會”,國家開始走上正軌了。
項:我一九六○年就開始參加工作,直到一九七九年我四十歲,正是而立之年,我才真正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才華。“三中全會”以后胡耀邦提出來干部要“四化”:年輕化,知識化,革命化,專業化。我很幸運,趕上了“三中全會”后好的政治環境。我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搞紡織的高級工程師,母親是一個醫生。像我們這樣的家庭,在“三中全會”以前最多當一個教師。但是趕上了好時候,好政策。張勁夫當部長的時候,我還沒入黨,張勁夫就要我參加部里務虛小組。張勁夫是非常開放的一個人,有真知灼見。
馬:張勁夫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人?
項:思想解放,非常開放。在財政部我屬于有爭議的人物。大家公認我這個人很能干,所有的領導都喜歡。但是我一九六二年以前就申請入黨,直到一九八四年才批準。因為,在“左”的思潮看來,我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我在財政部里一直表現很好。一九八○年開始提干部了,第一批沒有我,我也沒有感覺怎么樣,年輕嘛。
張勁夫之后,吳波同志做了一年部長,因為年齡大了,主動讓賢,由王丙乾接任財政部長。解放前,吳波是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王丙乾是華北財政部審計處副科長。解放后,在華北人民政府財政部的基礎上建立了新中國財政部,吳波擔任了中央財政部辦公廳主任,王丙乾是財政部主計處科長。所以,吳波和王丙乾是財政部內部成長起來的部長,為人非常親切,也很隨和,他們在財政部都有很高的威望。財政部的人對前三任部長都非常尊重,但是感情上不是那么親近。
馬:有點敬而遠之的味道。
項:有點遠吧,他們畢竟是國家領導人,地位更高。我在財政部是小字輩,是一個從小就在這里長大的干部,上面領導是看著你長大的,有什么缺點、有什么優點他們心里都明白。我在預算司十年,到一九八二年組建綜合計劃司。我就調到綜合計劃司當副處長,第二年入黨,第三年提副司長,過了兩年就提為副部長。
馬:說句玩笑話:您這是坐直升飛機上去的。
項:對,人家說我要么不動,要動就亂動,開玩笑嘛。反過來講,我自己很注意。我在財政部當副部長的時候,分管司局的領導很多,都是老同志,工作上有問題要商量時我從來都是到他們辦公室去,這樣關系不就處理好了嗎?所以一個人的成長和他的環境是分不開的。
馬:您趕上了歷史機遇。一個是大時代變了,改革成為時代主題,再一個是您碰上了一群好領導。當然這和您個人的努力也是分不開的。
項:如果沒有勁夫、吳波、丙乾等老部長們的培養,我不可能成長起來。我這一輩子,好領導、好政策都趕上了。
改革是共和國財政六十年的主線
馬: 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財政已經經過了多次的調整和改革。
項:很多,有很多反復。解放初期是一個暫時階段,財政部缺錢,財政收入主要是公糧,一切為了前線。到一九五三年以后,我們國家的工作重點第一次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財政處在建設階段。就是毛主席說的兩句話“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一直到改革開放,財政基本上都是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我們經常要計算每年的財政支出里面有多少錢、多少比例是用于建設的。但是那時體制不好,工業產值增加很多但效益不好,GDP雖然增長很多,產品存量并不多,人民生活改善不多。中國經濟走上了一條消耗大、成本高、效益差的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財政體制的變化偏多,財政體制本身缺乏穩定。到什么程度呢?平均三年就要變一次財政體制。從實踐來看最短的財政體制只使用了一年。最長的財政體制也不過五六年。平均三年。這個體制使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制度安排不穩定,處在經常的變化之中。所以,當時的問題不是干部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是體制的問題。基本上是在分權和集權之間進行變化。用現在比較時髦的話講,是中央和地方那種博弈關系。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講《論十大關系》,十大關系里一大關系就是講中央和地方的關系。
馬:就是說,前三十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線就是尋找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一個合理的權力界限?
項:對,合理的分權界限,集中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制度保證?我們摸索了三十年,每一個不同的時期都有它自己的特點,最后也沒有找到一個最好的辦法,但是做了很多有益的嘗試。所以,不能說改革只是后三十年的事。一九七九年我們寫過一本書就叫《中國財政體制的改革》。先是在一家財經雜志上連載,署名的是三個人,后來結集出版。
大略地說,解放以后,我們事實上是無可奈何學習蘇聯。和美國談不攏,還發生了朝鮮戰爭,中國只能“一邊倒”,是被迫的。蘇聯派來了很多顧問,當時各部委都有蘇聯的顧問,財政部也有。蘇聯專家幫助中國建立蘇聯模式。其實,中國內部也在探索,陳云就對蘇聯的東西做了很多修改,不是完全照搬蘇聯的這一套。中國共產黨有很多做法就是和蘇聯不一樣,包括后來有一些證明是不對的做法,不就想走一條中國式的道路嗎?財政改革前三十年有過很多探索,包括分灶吃飯、包干制、總額分成,包括我們現在進行的分稅制在前三十年都搞過。
馬: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為什么當初搞這些東西沒有成功?
項:為什么呢?就是條件不具備。但是不能否認,改革是六十年財政政策的一個主線,六十年里財政始終是處在改革中間。前三十年已經做了很多探索,很多實踐。但是條件不成熟、不具備,因為稅制本身就不科學,沒辦法分稅。前三十年的改革絕對不能抹殺,不能說中國財政改革就是后三十年的事。事實上,前三十年的改革為后三十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礎。前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財政體制改革,為后三十年的改革進行了具有深遠意義的探索,為后三十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礎。從大脈絡上講,六十年的改革實際上是財政由高度集中向分級分權轉變的過程,是財政管理逐漸科學化、規范化的過程。
財政包干
馬:盡管有各種改革,但是到改革開放之初財政體制仍然不穩定。
項:前三十年走來走去,走到了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了嘛。都吃不飽肚子了,財政上已經非常脆弱了,赤字率很高了,很危險。一九八○年發生了“吳趙大戰”,就是吳波和趙紫陽之間的爭論,趙紫陽主張包干制,吳波主張分灶制。當時趙紫陽還沒有到北京工作,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當然吳波從來不承認“吳趙大戰”,他說,我只不過是作為一個下級講了我應該講的意見,趙紫陽是上級,我跟他沒有“戰爭”。我覺得吳老這個態度是對的。后來中央會議決定財政包干,財政部的分灶吃飯否定了。
馬:在分稅制實行之前,主要實行的財政體制是包干制。
項:盡管在一段時間里面有變化,但是就其性質來講,主要是實行包干的體制。有大包干,也有小包干,還有分稅包干的,也有增長包干的。總而言之,不脫“包干”二字。那么,什么叫做包干體制,怎么產生的?包干體制是改革開放以后,為了解決激勵機制不足,在沒有完善的法制條件下產生的一種過渡的辦法。最早是從安徽的鳳陽小崗村開始的農村大包干,“交夠了國家的,留夠了集體的,最后都是你自己的”。后來就把這種包干的制度引進到企業里面,在企業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包干制度。很多人覺得包干的辦法很好,也就引進到財政制度里面。當時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也有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怎么樣使地方政府盡可能地放心,實行包干制度是可以部分解決這個問題的。在體制多變的情況下,包干體制能夠起到調動積極性的作用。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表現在當時的財政收入上,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不是太快,中央財政增長的速度相對來說更慢一些。那個時候一年財政收入能夠增加一二百億就不錯了。
馬: 實現包干制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出現了逐年下降的趨勢。
項: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一個重要的目標。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實行減稅讓利,在這個前提下面,把一部分財政收入有意識地讓給企業,增加企業的活力。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為9.5%,可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現逐年下降,一九七九年財政收入在GDP的比重28.4%,一九八○年就下降到25.7%,到一九九三年比重已經下降到12.6%。在這段時間里面一共下降了15.8%,大體上每年要下降一個百分點還要多。另一方面,在整個財政分配中,中央財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導地位,中央財政不大能夠起監控地方政府和地方的收入。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也是呈現一個下降的趨勢。一九八四年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是41.5%,到了一九九三年下降到22%。是倒二八。所以中央財政的發言權就相對比較小。老百姓有一句話,就是喊雞還要撒把米呢,你手里的錢都沒有幾個,你讓人家聽你的很難。錢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政治上的權威如果沒有經濟的基礎也是不行的。
當時國門已經打開,我接觸了很多人,也接觸到臺灣地區的專家,包括臺灣的原“財政部長”陸潤康。他在大陸有投資,他卸任后到北京來,想拜會財政部長。當時我是副部長,我們聊得很好。他說,“臺灣的財政是‘弱干強枝,中央比較弱,地方比較強,整個臺灣財政收入的90%是靠臺灣省,我這個‘部長見了臺灣省的‘財政廳長要討好他的”。他說,“弱干強枝”在臺灣是不行的,在大陸更是不行的。
馬:這是肺腑之言。
項:肺腑之言,這對我的思想是有影響的,認識到集中一定的財力是有必要的。我還到南斯拉夫去考察,南斯拉夫當時有個副部長叫奧格奧夫斯基,是個經濟學家,他跟我說,南斯拉夫財政集中占國民收入比例太低了,11%,他擔心國家要出事了。果然,我回來了以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出事了。
馬:這應該是一九八七年的事。
項:是一九八七年。奧格奧夫斯基有眼光,他的話提醒了我,這個比例關系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下降到11%政府的職能要想維持都很難。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這個比例一年一年下降,下降到11%左右。
馬:當時財政部也到了很窘迫的地步了。
項:中國的情況與南斯拉夫不同。我們除了預算內收入以外,還有一部分預算外收入,一部分政府性收費。不管怎么說,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例太低,財政部很窘迫啊。有人把中央財政叫做“懸崖邊上的中央財政”,一碰就掉下去,如臨深淵。由于中央財政收入嚴重不足,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甚至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并且借而不還的事。幾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錢:糧食收購財政虧損補貼資金不到位;重點建設資金不到位,很多重點建設卡著脖子,如鐵路、港口、民航等。當時連某些中央機關都已經到了不借錢,工資發不出去的境地。我的前任劉仲黎部長跟我開玩笑講,我現在背心都快給扒掉了。他三次找朱基副總理,希望他批條子向銀行借錢,朱基不允許。包干的體制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全國財政、稅務工作會議召開。朱基副總理來到會場,對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員說:“在現行體制下,中央財政十分困難,現在不改革,中央財政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如果這種情況發展下去) 到不了二○○○年(中央財政)就會垮臺!”
親歷分稅制改革
馬:包干體制已經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改革的方向就是分稅制。
項:分稅制也不是我們發明的,是很早就有的,世界各國普遍實行。到一九九三年我們搞分稅制的時候,世界上大體有三種不同的分稅制類型。第一種是以美國、加拿大為代表的聯邦式分稅制。第二種是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集權式分稅制。第三種是以日本和意大利為代表的混合式分稅制。當時我們推行的分稅制,相對地說比較接近集權式的分稅制,主要是財權相對集中。
馬:分稅制改革是怎么推行的呢?
項:一九九三年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率走高。當時中央派了十三個部長到了二十六省市調查研究。部長們回來以后寫成了一個文件,當時寫了十三條,十三個部長一人寫一條,拿到國務院討論,朱基當時是主管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總理,他開玩笑說十三條建議不吉利,加幾條,后來加了三條,形成了十六條,這就是一九九三年的中共中央六號文件。這個文件非常重要,為經濟體制改革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基礎,對于分稅制的展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一九九三年下半年,我們幾乎全部精力都撲到了分稅制改革,做了很多準備工作,其中許多是非常緊急的。因為上上下下并不熟悉分稅制。財政部部長劉仲藜在北京龍泉賓館主持召開了一次體制改革座談會,我當時是常務副部長,在會上有個發言,第一次比較全面地介紹了分稅制。差不多同時,時任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書記的金鑫同志再次向中央匯報了工商稅制改革的方案,并經中央同意。在分稅制改革方面,龍泉賓館會議對統一思想非常有益,隨后工商稅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就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一九九三年下半年,無論財政部還是稅務總局兩個辦公樓晚上經常燈火通明。那時已普遍使用計算機,大大提高了效率。那年我還開了很多座談會,包括納稅人的、地方政府的、專家學者的、海外人士的。就工商稅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聽取各方面意見,這次可能是歷史上歷次改革中聽取意見最充分的一次了。
馬: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要求進行財稅體制改革,共有三項內容:一是把現行地方財政包干制改為分稅制,建立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體系。二是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推行以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制度。三是改進和規范復式預算制度。
項:這個決定意味著分稅制改革正式開始了。如果說,改革開放以前的三十年分權和集權不斷進行博弈,到一九九三年進行分稅制改革的時候,我們已經避開分權和集權的說法,因為掉進去以后說不清楚,說我們要集權,地方一聽就不干了。我們就說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個話要最高層的領導人講,當時是江澤民同志,他說,要適當地集權,因為中央財政太困難。聽說,鄧小平和陳云兩位老人家也贊成適當集權,增加中央財政的財力。江澤民總書記先后多次分片主持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的書記、省長座談會,宣講政策,聽取意見,消除誤會。記得一九九三年九月,江澤民同志在廣東的珠島賓館召開中南和西南兩大區十個省的書記、省長座談會。原先財政部沒有隨行任務,會上有位省長對分稅制提出一些意見,因為涉及許多具體政策,曾慶紅同志臨時電話通知我參加會議。我接了電話就直奔機場,當晚趕到廣州。
馬:分稅制改革主要是朱基。
項: 對,他當時是常務副總理,親自帶隊,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帶領相關部門的同志,先后走了十三個省,面對面地算賬,深入細致地做思想工作。每次去都是專機,一般是五六十人,最多的一次八十多人。基同志說過,到地方去征求意見,核心問題是財政,所以他對財政部特別寬容,在嚴格控制隨行人員的前提下,卻對財政部網開一面,愿去幾位就去幾位。先后隨基同志到各省市征求意見的同志,有劉仲藜、劉克崮、姜永華、王立峰、許宏才等。除了廣東、海南,其他地方我都去了。每次隨行都不輕松,經常加班加點,有的時候通宵達旦,車輪大戰。事后基同志曾經半開玩笑地說過,那段日子是東奔西走,南征北戰,苦口婆心,有時忍氣吞聲,有時軟硬兼施。總算談下來了,我自己則掉了五斤肉。
馬:在你的回憶文章里,實事求是地記載了你們與朱基之間的爭論。
項:主要是對以一九九三年為基數有疑義。朱基同志就分稅制改革調研去的第一站是海南,第二站是廣東。財政部部長劉仲藜同志隨行。這是實施分稅制改革調查研究、交換意見中最重要的一次,因為以一九九三年的財政收入為稅收返還基數,就是廣東省匯報工作時提出的。后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決定以一九九三年為稅收返還基期年,這在當時是個非常大的政策。事實上當時我和仲藜同志都不同意以當年為基數,坦白講,對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當時我思想上并沒有理解,坦率地說是有點保留意見的。當然,財政部對于執行黨中央的決定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財政部門比較務實,從技術操作層面考慮問題多一些。說白了,就是擔心地方的數字弄虛作假,擔心錢在一九九三年都收光了,都成了地方政府的基數了,以后年年要給它。擔心今年收入上去了,明年又下來了無以為繼怎么辦?實際上,宣布以一九九三年為基數的當年后幾個月確實出現了一些異常情況,把死賬欠款都收起來的,大量向銀行貸款交稅的,甚至連倒閉的企業都把以前的稅補齊了,凡此種種,造成了一九九三年后四個月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據一九九三年地方財政收入月報,這一年地方財政收入全年增長966.63億元,增長率為40.2%,其中九至十二月地方財政收入增長756.95億元,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了51.8%、62.5%、86.1%、121.3%。這是從來沒有過的,確實也是反常的。對于這種現象的出現,當時的朱基副總理也非常重視,那年四季度,他曾布置多次檢查,還做出了凡違規操作不合理的基數可以扣除等政策規定。
馬: 以一九九三年為稅收返還基期年,各地當年財政收入基數猛漲上去之后,對一九九四年的財政收入有沒有影響呢?
項:這是我最擔心的,因為我是分管預算的副部長。一九九四年一月份的時候,我是憂心忡忡,寢不安席。到了一九九四年二月八日,一月份的財政收支報表出來了,一月份收入二百七十七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一百零六億元,增長62%,這是從來沒有過的速度!我高興得不得了,一塊石頭落地了。按照財政部的慣例,農歷大年初二、初三部黨組歷來是要開會的,那年的春節是二月十日,我向仲藜同志提議,一月份情況太好了,今年春節就不要開會了吧,仲藜同志欣然同意。在不經意中是我把財政部的優良傳統給破壞了。這其實是表明當時的一種心情。財政收入數據顯示,一九九四年每個月的財政收入都比上年同期增加,全年財政收入增長了八百六十九億元,比上年增加20%,是以前歷史上少有的。自一九九四年實施財政改革以來,到二○○七年已經十四年了,財政工作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財政收入由一九九三年的四千三百四十九億元,增加到二○○七年的五萬一千三百億元,十四年平均年增三千三百五十四億元,平均年增長19.3%。這一切充分說明了一九九四年的分稅制改革功不可沒。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改革,它奠定了中國特色財政改革的基礎。
馬:現在回頭看當年你們與朱基之間的爭論……
項:現在我對于以一九九三年為基數的政策已經心悅誠服,這個政策說明,在推進重大財稅改革時,必須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強有力支持。這是必要的妥協,這個代價必須付出,這一讓步爭取了民心,統一了思想,保證了分稅制改革的順利推行。因為這場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如果進行不下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一句空話,它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奠基的,對中國來說,它是經濟發展、長治久安的基礎。朱基說過一句話:“對財稅體制取得的成功,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馬:在分稅制改革中朱基總理一定給你很多影響。
項:我們黨內歷來有一個傳統就是對個人在工作中的作用不過分地強調,朱基同志肯定是一個偉大的人物,是一個偉大的改革者。他的領導、能力對我教育很深,我也能有這個機會追隨他的左右,一起來完成財政稅收的改革我覺得是非常光榮的,也是非常榮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