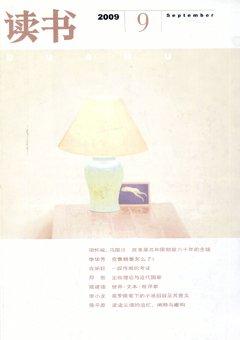克魯格曼怎么了?
李華芳
經濟學界對于克魯格曼獲得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并不意外,甚至有人打趣說,克魯格曼應該拿兩個諾貝爾獎:一個經濟學獎,一個文學獎。這大概是因其在《紐約時報》開設專欄帶來的巨大影響力;而就文筆而言,克魯格曼也被《幸福》雜志認為是自凱恩斯以來文筆最好的經濟學家。
籠罩在克魯格曼身上的一個以訛傳訛的傳言是,他準確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事實上,一九九四年,克魯格曼在《外交》(Foreign Affairs)雜志上發表了《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亞洲增長不是奇跡,來自當時芝加哥大學教授艾爾文·楊的一篇廣為流傳的論文《數字的暴力:正視東亞增長經驗的統計現實》(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中的觀點。但楊教授的這篇論文直到一九九五年才發表在《政治經濟學》(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學術雜志的長審稿和發表周期,無形之中影響了楊教授思想的傳播,讓克魯格曼領了先。難怪人們把這一成就記在了克魯格曼身上。
楊教授,克魯格曼,或者還有劉遵義等人都不過是指出,東亞模式并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好,東亞模式有問題,高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而且大量的FDI會出現問題。這一觀念與“亞洲四小龍”以及亞洲價值觀的經濟學者非常不同,當時可以說屬非主流。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大家才發現原來克魯格曼說過亞洲模式有問題,但這也斷然稱不上是預測。一九九九年,克魯格曼寫了《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才正式對亞洲金融危機進行了總結。書中有這樣一段話:“不久前的諸多權威認為提倡基于優越的亞洲體制和獨特的亞洲價值之上的亞洲奇跡,現在同樣有很多權威(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一批權威)堅持認為亞洲金融危機是失敗的亞洲體制的必然結果。但是,如果亞洲體制真有彌天大錯的話,過去它怎么會成功呢,今天又怎么會突然崩潰呢?所以,我們應該以開放的態度來分析問題,不要只是簡單將過去對亞洲的崇拜顛倒過來。”但,這番警告顯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克魯格曼那種“實用主義”的思想態度,也被忽視了。
“實用主義”的思想態度,也是凱恩斯一貫倡導的,這一態度一是著眼于應用;二是較注重短期,因為“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
克魯格曼目睹了共和黨上臺之后,尤其是小布什實行的種種公共政策與羅斯福新政南轅北轍背道而馳,左翼凱恩斯主義者克魯格曼自然痛心疾首,撫今追昔,生出感慨。他的《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這本書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寫的。
克魯格曼認為羅斯福新政貢獻巨大,為其后美國經濟的“長鍍金年代”奠定了基礎。關注福利,提高教育、醫療、環境和一系列削減不平等的手段,使得貧困減少,美國經濟迎來增長。克魯格曼和另一位左派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一樣肯定了工會的作用,盡管角度不一樣。加爾布雷思是從抗衡力量的角度切入,認為工會與大型企業之間如果缺少必要的制衡,就會產生相應的不公平,而工會的強大有助于制衡大型企業。而當工會強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企業之間也會形成聯盟來對抗工會。這種“競爭”有助于提高經濟的效率。
克魯格曼則從工人工資入手進行考察,他發現工會強大之后,工人的平均工資提高了,這對工人而言是個好事。在克魯格曼統計的長鍍金年代里,工會力量的強盛和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沖突。不過克魯格曼也許心太急了一點,將工會膨脹當成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
客觀地講,不能說工會和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性。問題是,克魯格曼沒有區分開:對公平而言,工會力量增長作為抗衡力量有助于增進公平的觀點,是加爾布雷思論證的;對效率而言,工會強大是不是促進了經濟增長,是未知之數。盡管在克魯格曼關心的時間段內,工會和經濟增長兩者都有正的增長,但是在工會持續增長的七十年代初,美國經濟開始衰退。克魯格曼卻沒有提到這一點。
工會的例子只是一面鏡子,克魯格曼在標榜作為自由派的良心時,實際上主要的訴求是平等而非效率原則,并且只是短期內的平等,長期來看并不一定。對于工會的研究表明,長期看,行業工會往往會成為一個壟斷性組織,對于企業和非工會工人產生擠壓效應。尤其是非行業工會的工人工資往往會低于工會成員,并且非行業工會工人常常因為行業工會規定不得雇傭非工會人員而遭受損失。因此,對工會一味說好的態度,或者推而廣之,對一切短期內看似公平的公共政策“叫好”的態度,有短期實用主義的味道,從效率的觀點或者從長期來看,都未必是站得住腳的。
《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的中譯本,譯者劉波將“Liberal”翻譯成了“自由主義者”,引起不少誤解。實際上較為確切的譯法應該是“自由派”。而自由主義者對應的是“Liberalist”,至于“Libertarian”是自由至上主義者。三種人各不相同,“自由主義者”與“自由派”之間的區別就算中間沒有橫亙喜馬拉雅山脈,也至少隔了一條黃浦江。相比于傾向“平等”公共政策的“自由派”而言,自由主義者無疑更加看重效率的問題,自由至上主義者就更不必說了。就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及其側重而言,克魯格曼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反自由主義者。
《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并不是克魯格曼拿手的題材,而是克魯格曼對美國政治的一個分析。他認為共和黨之所以在美國歷史上獲得了較長的執政期,種族因素在其中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白人精英階層盡管人數不多,但是憑借鼓吹的自由市場經濟獲得了巨額財富,因而可以拿出更多的競選經費來支持共和黨上臺,繼續推行保守派的政策,使得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這與羅斯福新政背道而馳。
克魯格曼對羅斯福新政及其影響念念不忘,認為羅斯福新政使社會福利得以保障,不平等程度降低。而一九四八年杜魯門上臺,克魯格曼更視其為共和黨被迫承認羅斯福新政難以動搖的地位。克魯格曼認為“二戰”以后美國的中產階級社會,是由羅斯福新政造就的,尤其是戰時工資管制和對工會的扶持,使工人的待遇有了較大的提升。同時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使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局面維持了近三十年之久。但令克魯格曼痛心疾首的是,小布什上臺之后卻打算拆除羅斯福新政的最后一塊招牌,那就是社會保障制度。這使得克魯格曼在《紐約時報》開設政論專欄,開始了長達數年對小布什的口誅筆伐,幾乎每一項共和黨執政時期出臺的政策都遭到了黑嘴克魯格曼無情的嘲諷。
因為在小布什執政期間,貧富不均的狀況急劇惡化,這一切盡管有自由市場的因素,但主要是一小撮白人精英耍起了政治陰謀,這種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深深植根于美國文化之中。克魯格曼對新保守主義運動的批判如此強烈,保守主義運動說到底是要損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從根本上講它是反民主的。又是種族歧視,又是反民主。這樣的指控在克魯格曼看來還遠遠不夠,從伊拉克重建的一敗涂地到應對卡特里娜颶風時的手足無措,共和黨簡直一無是處,是當今美國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而小布什難辭其咎。
在這些近乎詛咒的言辭背后,可以審視一下克魯格曼的態度,他的態度還是一以貫之的,并沒有多大的變化,依舊是注重短期內的平等,為了達成這一“實用主義”的目標,克魯格曼甚至沒有太多理性的經濟學分析,而更加注重情感性的表達。這恐怕也是在他榮獲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后,很多報紙諷刺“專欄作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所在。
當然媒體記者們可以再為克魯格曼歡呼雀躍一次,因為他準確預測了二○○八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是,會有一位民主黨總統上臺,以及由民主黨人牢牢控制的國會。克魯格曼寫下這些的時候,還是二○○七年。不過奧巴馬的上臺,也對克魯格曼之前的種族歧視說產生了沖擊。如果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在之前存在的話,那么這些年移民的演化已經使得選民中白人減少,而其他有色人種大大增加了。所以克魯格曼對共和黨之前勝選依賴于“種族歧視”的解釋,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從克魯格曼對美國大選的分析說明,關注短期公平的實用主義態度,是很難解釋長期趨勢的。前者可能更加偏向政策應用,而后者較為關注理論解釋。但問題在于克魯格曼在學術理論的貢獻上是成就斐然的,所以令人困惑。
促成克魯格曼在學術上嶄露頭角的是他關于《壟斷競爭貿易模型》的論文,這得益于屠能、受教于多恩布什的論文,奠定了“新貿易理論”的基礎。梁捷在一篇介紹克魯格曼學術思想的文章中提到:國際貿易理論發軔于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經過上個世紀赫克歇爾和俄林的工作之后,整個理論體系已經比較完善。不過許多人發現理論與現實之間存在背離,而且兩者距離越來越遠,形成很多不解之謎。克魯格曼的基本想法就是要挑戰李嘉圖傳統。他認為即使在不存在比較優勢的情況下,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是產生貿易的原因。隨著生產力提高,產業內貿易使得專業化與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這進而導致更低的價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樣化。這一思想通過一九七九年的《收益遞增、壟斷競爭與國際貿易》和次年的《規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格局》等幾篇論文而初見規模。其后,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和格羅斯曼又一起合作,完善了這一理論,故而被稱為“新貿易理論的三劍客”。
三劍客的“新貿易理論”針對的還是克魯格曼一開始提出的問題,即便沒有比較優勢,自由貿易是否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但國際分工卻由很多偶然因素決定,歷史地理文化等因素會影響分工,某些邊際報酬遞增的行業會引發集聚而形成路徑依賴。這一思想奠定了克魯格曼后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術基礎。
傳統的經濟學研究并不注重歷史學者和地理學者關于歷史地理因素對經濟活動造成影響的研究,因此新經濟地理學這樣的學科被忽視也就理所當然了。受波特關于“國家競爭理論”的啟發,克魯格曼開始研究“新經濟地理學”,成為這個學科的創始人。新經濟地理學的核心模型是“核心—周邊模型”,意思是兩個原本外部條件相同的區域,如何在報酬遞增、人口流動與運輸成本交互作用的情況下,逐漸分化形成完全不同的生產結構。一九九一年,克魯格曼在《政治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論文《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對新經濟地理理論進行了初步探討,建立了基本的核心—周邊模型。克魯格曼抽象地假設世界經濟中僅存在兩個區域和兩個部門,即報酬不變的農業部門和報酬遞增的制造業部門。在一定水平的運輸成本下,如果一個區域的制造業份額越大,相對價格就越低,廠商能夠支付的工資越高, 越能吸引更多的制造業工人,農轉工也會越來越多。這時候會形成兩個現象,首先是制造業成為核心,而農業部門分散在周邊。而對于制造業內部而言,原本平均分布的結構也會變成一個“核心—周邊”結構。不僅在一個地區有核心—周邊的結構,世界范圍內以生產水平來看,也會有核心—周邊國家的區分,從而形成不同國家的專業化分工。
在新經濟地理學中,理論假設存在一個世界,其中某個區域或者國家因為偶然的技術進步在制造業率先建立起一種自我強化的優勢,這一優勢允許它支付比其他國家更高的工資(事實上,這就是美國)。隨著時間的發展,世界對制成品的需求上升。這將使得制造業區域的生產水平上升,制造業在該區域大規模地集聚,并使得該區域的工資上升。這一過程不斷地循環往復,進一步發展,不同區域或者國家之間工資差異將越來越大,最終不可持續。制造業廠商情愿轉移生產去追逐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于是他們會設法遷入次一級的區域,在那里他們可以享受相對較低的人力資本和相對較好的規模效應,從而變得有利可圖。這樣,第二個區域又開始了建立制造業自我強化優勢、提升區域工資的輪回,與上一個輪回一樣,最終變得不可持續,從而引發第三個區域的制造業成長。只要還有工資和生產水平較低的區域存在,這種產業的轉移過程就可能持續下去,最終階梯狀地拉動落后地區的經濟增長和產業集聚。
這種梯度轉移要得以實現,只有交易成本足夠小,低到一定程度,產業的地理集聚才是可能和可持續的。此時資源得以比較自由地流動,最終由產業結構和市場水平決定地域或者國家內部的地理集聚和分工。運輸費用或者交易費用的變化對于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是非線性和非單調的。貿易成本的下降使得世界經濟一體化程度穩定地增加,反之亦然。這也是克魯格曼支持自由貿易的重要理由,因為自由貿易而不是通過關稅等進行阻礙,有助于降低國際貿易的交易費用,促成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有效配置。
但這似乎與克魯格曼一貫關心的平等問題相悖,從全球的角度來審視,甚至有悖于克魯格曼一貫的堅守,因為國際貿易有可能造成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拉大,尤其是在產業梯度轉移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要承受更多的勞工和環境成本等。
也許這不過是因為克魯格曼在討論政治和對待學術的時候,采用不同的方式與態度。在經濟上偏右、政治上左傾的人也比比皆是。也許不應該苛責克魯格曼的態度,權且將這一種政治表達當成參與競爭的一種“意見”,自由派保守派都各自拿出絕招,面向選民進行陳述,接受民主選舉制度所設定的程序,并享受其結果。而這也正是二○○八年的美國大選帶來的啟示。
在理論上,克魯格曼與弗里德曼意見不同,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也是各有道理,甚至長期來看左右搖擺。而把克魯格曼評價弗里德曼的話放在他自己身上也一樣合適:“不論持何種政見,他都會贏得諾貝爾獎。”允許觀點的自由競爭,才是自由主義者的良知所在。
(《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美]克魯格曼著,劉波譯,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