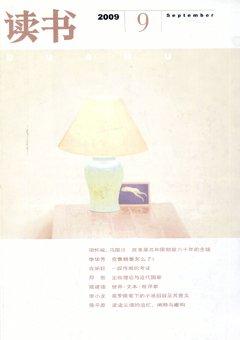不一樣的俾斯麥
李伯杰
人們似乎早已習慣了把奧托·馮·俾斯麥看做一個政治強人,甚至是戰爭狂人。在各種書籍、報刊等媒體中,俾斯麥大多被定格在“鐵血宰相”。只要一提到俾斯麥,就不會不想到“鐵與血”,想到普法戰爭,想到“糖面包加鞭子”。俾斯麥最為人熟知的畫像也許總是頭戴尖頂頭盔的那一幅,畫像上的“鐵血宰相”面色沉凝、嚴肅、堅毅;除了“保守”、“反動”之外,他給人的印象或許只剩下了鐵腕、好戰、精明強干、工于權術等等。
毫無疑問,“鐵血宰相”的頭銜之于俾斯麥,可謂實至名歸。無論對內、對外,俾斯麥都是一個政治強人。對外,自俾斯麥一八六二年出任首相后,不到十年間,普魯士先后對丹麥、奧地利和法國一連打了三場戰爭,最終建立了第二帝國,完成了“自上而下的革命”。對內,俾斯麥一向用鐵腕來鎮壓反對勢力。他曾與天主教教會展開過所謂“文化斗爭”;他曾頒布了“社會主義者法”,鎮壓工人運動。在與民主派的斗爭趨于白熱化之時,連國王威廉一世都產生了動搖與恐懼。威廉一世對俾斯麥說:“這一切將會怎樣結束,我完全精確地預料到了。有朝一日,在歌劇院廣場上,在我的窗戶下面,有人先把您的頭砍下來,稍后就輪到我了。”(奧托·馮·俾斯麥:《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東方出版社二○○七年版,189頁)但是俾斯麥面對嚴峻的局勢毫無懼色,視死如歸,他不以為然地說道:“是呀,我們都得死,可是我們遲早得死,難道我們不能死得更莊嚴些嗎?……是在斷頭臺上還是在戰場上,為上帝恩賜的權利而英勇地獻身,不同樣是光榮的嗎?”(同上)俾斯麥的強悍與“大義凜然”,由此可見一斑。但是,“鐵血宰相”并非一個“單向度的人”,除了強悍、剛毅之外,俾斯麥也還有別的面孔;除了人們所熟悉的“鐵血宰相”之外,還有一個不一樣的俾斯麥。
首先,俾斯麥并不是一個戰爭狂人。所謂“鐵血宰相”的綽號,來自他在一八六二年九月三十日普魯士議會預算委員會上的一篇演說,他情緒激動地慷慨陳詞,認為統一問題絕不可能通過和平手段實現:“普魯士期待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其強力。……時代的重大問題是不可能通過演說、多數派的決議來解決的——這是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的重大失誤——而是只有通過鐵與血。”但是“鐵與血”這個著名的比喻并非由俾斯麥首創,而是來自自由派人士馬克斯·申肯多夫于一八一三年在反對拿破侖的戰爭中創作的一首詩。俾斯麥甚至不是一個軍國主義者,戰爭對他來說,只是一種達到目的的工具。他認為該打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進行戰爭,并且把戰爭堅決打到底;而他認為戰爭弊大于利的時候,他堅決不打。所以俾斯麥實際上是近代德國歷史上少有的懂得節制的政治家,在這一點上除了阿登納之外,鮮有政治家能出其右。普法戰爭爆發后,正當普軍節節勝利時,俾斯麥在一八七○年十一月寫給其夫人約翰娜的信中,表露出了擔憂和恐慌:“他們(指總參謀部——作者注)為勝利而欣喜若狂,而我卻很害怕;這種狂妄的自視過高,會讓我們自己受到懲罰。”(見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über die Detuschen,München,List Verlag,2001,S.243)同年十一月初,他在一次宴會席間對同僚說:“我現在極度恐懼。局勢到底怎樣,這些人是預料不到的。我們是在一根避雷針的頂尖上搞平衡;我們一旦喪失了我辛辛苦苦創造出來的均勢,我們就將完蛋。”(同上)一八八八年威廉二世登基后,老宰相同新皇帝之間產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和沖突,導致俾斯麥被解職。沖突之一就在于,新皇帝認為德國已經強大,必須開足馬力,去奪取“陽光下的地盤”;而俾斯麥則認為,處于歐洲中央的德國,必須盡可能地維持和平,通過一系列的外交手段,把各個列強編織進一張網中,使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對德國開戰。而且他在二十年的政治、外交生涯中,與各列強簽訂了無數公開的和不公開的條約,用條約織就了這樣一張大網,確保了德國及歐洲的和平。
其次,不太為人所知的是,俾斯麥除了俠骨之外亦不乏柔情,尤其對于森林情有獨鐘。正是因為對于樹木癡情無限,他才自封為一個“樹癡”。他被解職后,歸隱山林的過氣英雄自然是怨天尤人,他對于政治對手卡普里維的一些做法尚可容忍,但對此公下令砍伐首相官邸周圍的百年老樹一事則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自傳《思考與回憶》中,他道出了心中的忿忿之情:“我不能否認,從得知我的繼任人讓人砍光在他的住宅,即以前我的住宅的庭院前面的那些古樹之后,我對他的人品的信任忍受了一次打擊。……我寧可諒解馮·卡普里維先生的一些政治上的意見分歧,但不能饒恕他毀壞這些古樹的惡劣行為,他濫用自己對國家地產的權力來對待這些古樹而使田園荒蕪。”(《思考與回憶》,572頁)。
然而最為人所不知的,大概當數俾斯麥的幽默感。“鐵血宰相”實際上是一個詼諧幽默的人,幾乎無時不在說笑調侃。文化史家弗里戴爾在其《近代歐洲文化史》講到,俾斯麥的警句式的語言非常睿智,時刻都戴著一種略帶反嘲的語氣,就像腓特烈大帝一樣,展現出了典型的法國作派:“他是個性情中人,也喜愛幽默,與他的幽默相一致的是,在這個世界上的當權者中,他是最不尚虛榮的人之一。需要補充的是,俾斯麥同樣不是一個嚴肅的人。”(同上)弗里戴爾還敘述了這樣一個情節,更為典型地展現了俾斯麥的幽默感:普法戰爭一觸即發之際,國王威廉一世一八七○年六月十五日從療養地埃姆斯急忙趕回柏林,俾斯麥、羅恩和毛奇驅車至勃蘭登堡門前去迎接。從這里返回王宮的路上,俾斯麥向國王陳述了他對歐洲當下局勢的綜合分析。同行的普魯士王儲在其日記里記載道:俾斯麥的報告“極為清晰、充滿高貴的莊嚴,完全沒有他平時一貫所喜愛的玩笑話”(Egon Friedell: 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 C.H. Beck, München 1996, S.1236)。“鐵血宰相”卻無時不在說笑,同我們關于俾斯麥的形象似乎不匹配,但這就是俾斯麥。
本文絕非想要為俾斯麥辯白,更無為他翻案之企圖。關于俾斯麥的評價,德國人至今仍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民族主義者及愛國者尊奉他為德意志統一的締造者,他的塑像仍隨處可見;而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則譴責他終結了德國的民主希望,把德國引進了一條不歸路。這里想要指出的只是,“鐵血宰相”是一個復雜的、因而也有趣的歷史人物,并非永遠板著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