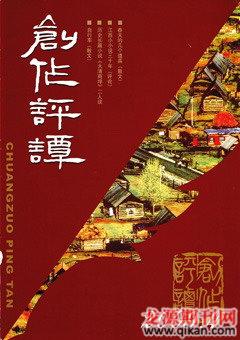另一種開始
董 雪
中國文學自古就不缺乏對鄉土生活的抒寫,至近現代小說產生后更是出現了一大批鄉土小說作家。但是這種所謂的鄉村敘事往往會陷入兩個極端:一是把鄉村描繪成“精神家園”,是人的心靈在無所皈依之后的叛逃與出路,農民則是這個“精神家園”中的“隱士”或者“英雄”。比如以沈從文為代表的京派文學,就是把鄉村作為一種自足的理想世界來歌頌詠嘆。與此相反的是將農村描繪成苦難的源泉,農民的落后愚昧成為知識分子啟蒙的對象。這最早以魯迅為典型代表,其后繼者則不勝數。新時期以來,對鄉土的書寫出現了一種新的突破。由于“土地”“鄉村”“農民”這樣一些詞匯先天地“與國家、民族、歷史這些‘永恒的載體聯結在一起,并因此給人以‘歸宿感”,因此當作家站在新的時代高度上回望歷史時,很容易選擇以土地、鄉村為載體進行一種“史詩性”的建構。無論是《白鹿原》所揭示的“一個民族的秘史”,還是《秦腔》所講述的清風街的故事,歸根結底都是由一片土地、幾個家族來折射整個民族國家的社會歷史變遷。這些作品無疑是沉厚的、深刻的、發人深省的,但同時也會給人一種迷惑,難道今天我們寫土地、寫鄉村、寫農民就一定得是悲戚沉痛的?能不能有另一種審美的存在?鄉村可不可以是輕松快樂的?或者更進一步,將民族、國家、歷史這樣的宏大思考、沉重命題寓于輕松的鄉村敘事之中?展鋒的新作《終結于2005》或許可以作為對這些疑問的一個回答。
小說圍繞永欣村城市化的過程、以末代村支書老淮山為核心人物,講述了一個村莊六百年尤其是近一百年來的改革風云和歷史變遷,展現了珠江三角洲以及繁衍在這片土地上的農人的獨特命運和遭際。農民與土地,這樣的題材并不新奇,在我們慣常的想象中,農民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他們要以繁重的勞作來換取并不優厚的物質生活,和城里人相比無論是物質財富還是精神生活都十分貧乏并因此矮人一等。我們也見過了很多“底層寫作”“打工文學”所刻畫的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形象。但是我們卻忘了農民中也有例外,比如聞名遐邇的華西村、南山村,村民的收入水平、生活質量令很多城市居民都難以望其項背,但我們的文學卻從來沒有描寫過這樣一些“農民”,他們的生活方式、精神狀態我們一無所知。《終結于2005》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它所描繪的永欣村位于珠江三角洲地區,在改革開放之前就率先做出了“招商引資”的創舉,村民無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年就可有八九萬元的分紅。這種生活方式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對“農民”的想象,更超出了我們對所謂“鄉土敘事”的書寫,甚至超出了我們對“農民”這個詞的定義。而這其實恰恰正是作者想要進行辯駁的:“農民就不能有錢?農民有錢了就一定還要去種地?農民企業家怎么說?是不是也要種地?我知道你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有錢,農民是不應該這么有錢的!”作者通過小說給出了一個新的關于“農民”的界定,農民不應該只指那些在田間地頭勞作的農人,更本質的是與土地唇齒相依的感情、是與土地打斷骨頭連著筋的深情厚意。基于此,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在村里很多人逃港“做一日當一年”時,曾祖父卻不為所動,執意守著自己的幾畝薄田;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當大伯將承包下去的土地集中起來以公司的方式來經營時,面對前所未有的高額利潤,曾祖父卻“眼里閃出了淚花,哆嗦著雙手,打擺子一樣牙齒磕碰得說不出話來”;我們也就能理解為什么大伯要帶領全村人和鎮委書記斗智斗勇,不惜一切代價要保住村里每一分早已不用來種養的土地;更可以理解為什么村里人那么在意自己“名不符實”的“農民”身份,叫嚷“我不是農民誰是農民”。
基于農民與土地這種唇齒相依的關系,作者對農村城市化作出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永欣村的土地早已不用來種植農作物,而是用來蓋廠房出租給工廠,永欣村的盈利方式也不再依靠農業生產,而是靠買賣土地。這種經濟模式已經不屬于農耕文明的范疇而是地地道道的工業文明的產物,因而最后永欣村雖然負隅頑抗但終究還是被“城市化”了的結局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但作者要引領我們思考的卻是必然的就一定是正確的嗎?從作者對老淮山在城市化之前悄悄將自己的戶口轉去仙嶺村,讓自己成為永欣村最后一位農民這一情節的設計中可以看出,至少作者于這一點是有所保留的。城市化就一定能給村民帶來更美好的生活嗎?老淮山去早些年已經城市化了的珠海農村參觀后發出的感慨是“要是農村城市化就是化成眼前這模樣,天哪,那真是天大的災難!”“他的意思是說,農村城市化結果把過去的農民,全都變成了有錢的閑人廢人!說溫柔點,就是喪失了過去生活情趣的人,活到半中間咔噠一聲攔腰剪去了一截的人。”作者借老淮山之口表達了這樣的憂思: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農民延續了上千年的生活方式將無以維系;喪失了與土地的關聯,農民也就喪失了對生活的主動權;靠宗族血緣為紐帶的村人,在城市化之后將喪失唯一的凝聚力,本來就是“一盤散沙”的農民將更加無所依傍。
除了深刻的主題思想,值得關注的還有小說的表現方式。小說講述了一個村落六百年的歷史,且不論宋元時的南遷、康熙時的遷界復界,只說一百年來,從曾祖父的父親開始的關于土地的失而復得、得而復失,就能譜出一曲催人淚下的悲歌。然而這樣一個關乎歷史、國家、家族的故事,作者并沒有采取正劇的寫法,而是采用了詼諧幽默的喜劇形式,在小說中我們讀不到沉重壓抑的描繪,而是處處充滿令人忍俊不禁的細節,除了隨處可見的隱喻的性描寫,即使是對苦難的書寫,作者也采取了喜劇化的手法。比如:人民公社化時家里的飯菜沒什么油水,二伯只得趁給公社送菜、替廚師刷碗之機把盤子舔一遍,回到家再一次次的品咂留在唇齒間的滋味,這本來是個很凄慘的故事,但作者卻將它寫的充滿喜劇色彩:“在暮色降臨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他坐在屋場上,端著飯碗,嘴里念念有詞地吃出了別樣的滋味,最后在用舌頭將飯碗舔干凈時,就會從美好的想象中回到現實,抱怨油放的太少,根本舔不出味道。這當然讓家里人感到討厭,吃著碗里的,想著別處的,那還像話!如果是漂亮的姑娘,尚可自得,好歹也算是本事。于是,群起而誅之,用白眼珠而視之,用唾沫而唾之,用打鼻孔里發出的冷冷的哼而哼之。最不能容忍的是,他會趁家里人都睡了,跑去廚房,偷偷地將油倒出一點兒到菜盤里,加入一點兒醬油,用手指在里面攪動,隨后像貓洗臉那樣將盤子舔個干凈,并且發出嘖嘖的聲音。是大伯起夜,發現異常的響動才窺破的。引來最直接的后果是實施家庭緊急戒嚴,每當那兩位長輩做飯時,總要罵上一句挨千刀的,因為要先用鑰匙去開啟碗櫥,從里面取出油瓶之類的物品,方可燒火做飯,太麻煩了!”這樣的幽默還體現在作者對當下很多社會現象不露聲色的針砭諷刺上,比如針對城里人瞧不起農民沒文化,作者就讓身為農民的大伯用“文化”制約了那些“有文化的人”:“大伯把那些破爛不堪的老屋,叫做民居文化;把祠堂的擴建,叫做祠堂文化;把看上去不成體統的,尚不健全的健身中心,叫做農村全民健身文化;把在土地上鬧出的矛盾,叫做農耕文化;把村民都陶醉于粵劇的旋律之中,叫做粵曲文化;把九龍柱和九鳳壁,乃至八字頭上一口塘,叫做性文化;甚至領了人去裝修古雅的茶餐廳和茶吧吃飯,不說吃飯,只說吃文化……與外人張口閉口就是文化,反讓一些人在他面前不敢胡亂說話,害怕鬧出沒文化的笑話。”
正是用這種詼諧幽默的語言、以一家人吃喝嫁娶的日常生活,串起了發生在這片土地上的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土地承包、農村城市化等一系列變革以及由此引發的悲喜劇。讓歷史一改平面靜止的刻板面貌,變成平常人家的潑煩日子,由此讓我們感覺到歷史不是與我們無關的史書記載,而就是我們曾經和正在經歷著的生活。雖然永欣村最后沒能逃脫城市化的命運,一個有著六百年歷史的村落終結于2005年,但土地和農民的命運并沒有因此而結束,所謂的“終結”其實是另一個“開始”:城市化之后農民的命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境遇,如何在“終結”之后進行新的建構以及怎樣建構,是比“終結”更難、意義也更重大的問題。因此小說結束了,但我們的思考卻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