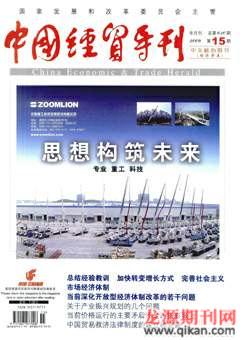改革農村宅基地制度的理由與思路
趙樹楓
2008年中共中央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推進農村改革與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嚴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農戶宅基地的用益物權。”這個決定第一次指明了農村宅基地改革的方向和目標,十分切合我國農村特別是大城市郊區的實際。當前迫切需要的是形成具體的政策法規,盡快加以落實。
一、農村宅基地制度的變遷與評價
(一)宅基地制度的演變
第一階段:我國農村的宅基地與房產制度一直是“房地合一”,均屬農民私有,一直延續到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初期。
1956年農村實現了高級農業合作化,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變成合作社集體所有。當年以全國人大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仍然規定農民房屋的宅基地“不必入社”,同時提出“社員新修房屋需要的地基,……由合作社統籌解決。”
第二階段: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條”),第一次宣布宅基地“歸生產隊所有”,“不準出租和買賣”;同時規定“社員的房屋,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有買賣或者租賃房屋的權利”。
宅基地由農民私有變成集體所有是一個重大變革,農民沒有精神準備。當時一些地方曾經發生砍樹、賣房等混亂現象。為此中共中央于1963年3月20日專門發通知,要求各地對宅基地問題做一些補充規定,宣布了四條政策:(1)社員的宅基地,包括有建筑物和沒有建筑物的,都歸生產隊集體所有,一律不準出租和買賣。但仍舊歸各戶長期使用,長期不變。生產隊應保護社員的使用權,不能想收就收,想調劑就調劑。(2)宅基地上的附著物,如房屋、樹木、廠棚、豬圈、廁所等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有買賣房屋或者租賃房屋的權利。房屋出賣以后,宅基地的使用權即隨之轉移給新房主,但宅基地的所有權仍歸生產隊所有。(3)社員需建新房又沒有宅基地時,由本戶申請,經社員大會討論同意,由生產隊統一規劃,幫助解決。……社員新建住宅占地無論是否耕地,一律不收地價。(4)社員不能借口修建房屋,隨便擴大院墻,擴大宅基地,來侵占集體耕地,已經擴大侵占的必須退出。這就形成了現行宅基地制度“一宅兩制、房地分離;無償取得,長期使用”的基本框架。
第三階段: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率先改革,農民迅速解決了溫飽,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建房高潮。但是,包干到戶以后有些地方基層組織瓦解,出現了亂占濫用耕地、在承包地上蓋房等問題。于是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從1981年起不斷發文件、頒法律,強化宅基地的管理制度。內容包括:宅基地面積要有限額;一戶只能有一處宅基地;申請宅基地要具備條件,符合規劃,履行審批手續;出租出賣房屋的不能再申請宅基地;等等。這些規定,對于治亂是必要的,起到了規范管理、保護耕地的作用。
在此階段,法律法規允許某些非農業人口無償或有償使用農村宅基地建房。如1988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一條仍規定:城鎮非農業戶口的居民經過批準可以使用集體土地建住宅,但需參照國家建設征地標準“支付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
第四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經濟大發展,城鄉人口加速流動,某些非農業人口使用農村宅基地反而由允許變成了“禁止”,農宅流轉政策出現了逆向調整。
1998年8月29日《土地管理法》修訂時刪除了上述第四十一條的規定。1999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土地轉讓管理嚴禁炒賣土地的通知》(國辦發[1999]39號)則宣布:“農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準城市居民占用農民集體土地建宅,有關部門不得為違法建造和購買的住宅發放土地證和房產證。”2004年10月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提出:“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同年11月國土資源部《關于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見》 提出“兩個嚴禁”:嚴禁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嚴禁為城鎮居民在農村購買和違法建造的住宅發放土地使用證。200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再次申明“三個不得”:“農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給本村村民,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宅基地、農民住宅或‘小產權房。”
(二)農村宅基地制度的基本評價
第一,總的看,農村宅基地制度及其配套政策,在計劃體制下和社會轉型期,使農民獲得了大體公平的住宅用地保障,實現了農民居者有其屋;形成嚴格的申請審批程序,制止了農地的亂占濫用;使管理大體有序有效,維護了農村穩定。這是應該肯定的。
同時必須指出,這個制度自身存在矛盾和漏洞,又同市場化、工業化、城鄉一體化的現實發展不相適應,政策調整明顯滯后,導致一批老問題和新矛盾的不斷積累。
第二,現行制度本身的主要特征是:一宅兩制,房地分離;無償取得,長期使用。宅基地屬集體所有,不能出租買賣,但可無償使用,長期不變;房屋屬個人私有,可以出租買賣。這種制度一方面助長農民“不要白不要”心理,多占、侵占宅基地的問題難以制止;閑置宅基地也難以收回;造成資源浪費,加大管理難度。另一方面,以宅基地“集體所有”為由限制農房在本集體成員以外的流轉,使農戶多年積累的房屋財產不能順利變現,使農民遭受種種損失。
第三,現行宅基地制度的另一特征是:政府管制,不準流通;強調福利,漠視產權。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城鄉人口的流動和遷徙不可避免,城鄉住宅的商品化也就變得不可阻擋。城市居民住房也是“一房兩制”,但已經商品化,可以自由上市流通,其房基地使用權可以隨房屋買賣轉移給新房主。農村宅基地卻以“福利保障”為由禁止流轉,其房屋也不準進入市場。城鄉住宅再次出現新的二元制。2007年3月通過的《物權法》雖然把宅基地列入用益物權,但只賦予農戶占有和使用兩項權利,把一般用益物權具有的收益權抹掉了。在《物權法釋義》中只強調“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基于集體成員的身份而享有的福利保障”,不承認其財產權利。這不僅顯失公平,而且對推進城鄉一體化,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入,改善城鄉居住環境,節約土地資源,都是不利的。
二、宅基地制度在北京郊區遭遇的現實挑戰
2004年以來,我們對北京郊區宅基地使用狀況進行過兩次系統的實地調查。總的情況是: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點占地有小幅擴大,宅基地管理有序有效,農戶宅基地面積平均4.22分,人均住房面積40平米,農民居住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生態化的發展,使用宅基地的人群發生重大變化,宅基地的功能顯著改變,矛盾和糾紛大量出現,許多政策規定難以執行,對現行宅基地制度形成了嚴重挑戰。
(一)宅基地使用人群的變化
第一,城市化和農村非農化,使農民大量減少,人口和勞動力轉移、流動加快,改變了本市農民自身的居住狀況。本市農業戶籍人口高峰值為1990年的392萬人,2006年已降至292萬。這些變動帶來的結果是:農宅閑置率增加(據我們調查,密云縣牤牛河一條溝9個村農房閑置率達17.2%);農宅與戶籍地分離、農宅與房主居住地分離,在農村已不是個別現象。
第二,外來人口大量進入農村居住。有調查數據顯示,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動人口從1997年的146.3萬增長到2006年的383.4萬,9年間增加了237萬。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的流動人口從1997年的16.4%上升到2005年的33.9%。就是說1/3以上的流動人口“不流動”了,已經成為事實上的“新移民”。其中,農民工多數在郊區居住,務工經商戶許多也以農村為生產場地。北漂族也基本住在農村。結果,本市農民的減少并沒有使村莊常住人口減少,反而不斷增加。近郊區村莊的外來人口已超過本地人。京郊農村成為農民和居民、本地人和外地人共同居住和利用的社區。
農村常住人口結構多元化及總量的變化,是對傳統觀念的顛覆。其一,農村宅基地不再為本村農民專用,“農村宅基地使用人”應予以新的概念;其二,城市化不意味著鄉村的消失,在一定的時期,還表現鄉村人口的增長。因此,按鄉村人口將大量減少為指導思想編制的農村土地利用規劃,應該予以調整修正。
第三,城市的現代化發展,使改善生態環境的要求日益迫切,都市農業特別是休閑觀光農業迅速普及,使農業、農村更加廣泛地為城市居民所利用。民俗接待戶大量涌現。2006年到農村農戶旅游休閑的市民達到2193萬人次。
第四,城市的發展擴大,又將農村吞沒,讓農民離開他世代居住繁衍的宅院,成為拆遷安置的對象。處理不好,農民喪失這塊屬于他們的最后財產,將會變成“失地失業失房”的城市貧民。
(二)農宅功能的改變
宅基地利用人群的變動引起農村宅院功能的變化,在保留居住功能的同時,生產資料的功能、環境功能和財產性功能突出出來。
主要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房屋出租。近郊和平原最突出,成為農民財產性收入的主要來源。
二是住宅出賣。上世紀80—90年代城鎮居民和外來人口在農村買房或申請宅基地建房逐漸增多。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通知禁止城市居民購買農民住房,農宅買賣變成私下交易,“以租代買”,依然禁而不止。調查顯示,北京農戶賣房的比例在4%以上,就是說,購買農宅的至少有幾萬戶,幾十萬人。
三是經營“農家樂”,發展觀光休閑農業。利用宅院進行民俗接待或經營商業、服務業、手工業,成為許多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
四是在拆遷時獲取高額補償。市政府2003年124號令確認了農宅拆遷補償包括宅基地區位補償價和房屋重置成新價兩項,等于承認了宅基地使用權是農民的財產權利,有權獲得土地的級差收益。
上述種種農宅功能的改變,使農民對于宅基地十分珍惜,“家家算賬,寸土必爭”。
(三)宅基地政策法規調整滯后,積累的矛盾和糾紛增多
1、法規與現實背離,使法規難以執行
法律規定,一戶一宅,實際上農村存在“一戶多宅”,并在發展。據農業普查數據,2006年末,擁有兩處住宅的11.81萬戶,占8.22%;擁有三處以上住宅的0.78萬戶,占0.55%。一戶多宅的成因,一是接受繼承和贈予而必然發生;二是購買農宅或建新不拆舊、為子女預先建造而沒有使用;三是搬遷、遷徙以后在新駐地建了住宅,原駐地宅院依然保留,等等。盡管有關法規一再重申堅持“一戶一宅”制,明確“一戶多宅”不合法,而在確權時即使不確定其使用權,也難以依法收回。
法律規定,農戶宅基地面積不得超過省、市、自治區規定的面積限額。北京市規定,近郊和人多地少地區,戶均2.5分,遠郊3分,1982年以前的按4分地從寬認定。據抽樣調查,宅基地實際面積超過4分地的占現有宅院的39.37% 。而形成原因復雜,大部分是合作化以前的祖產老院(當時并沒有什么“面積標準”),或者屬于社隊批準同意造成的,屬于私自占用的極少。死扣法規確定的“面積標準”,事實上難以執行。
北京市政府1989年39號令規定,村民全家遷出或轉為非農戶后另有住房的,原宅基地由集體經濟組織收回。有的縣曾做出限其在一年內將房屋拆除,把宅基地歸還集體的硬性規定。實際辦不到。只好不了了之。
上述政策問題,都成為準備開展的宅基地確權發證工作的難題。
2、限制農宅買賣的政策,引起的糾紛和官司增加
例如,通州區宋莊鎮,從1994年起至今聚集了1500多名藝術家,包括來自海外和港臺的近百人。買農宅定居的有200多戶。宋莊畫家村成了國際知名品牌,市委市政府確定宋莊為“文化創意產業聚集區”,并納入通州新城建設規劃。于是農宅價格大漲。拆遷補償時僅宅基地區位補償價一戶就可得二三十萬,少數原來兩三萬元賣了農宅的戶后悔了。有13戶賣房者以“買賣農房違反國家政策,屬無效合同”為由到法院提起訴訟。2007年7月區法院判決被告畫家李玉珠敗訴。李玉珠上訴,一中院判決維持原判,但指出原告在此非法交易中負有更大責任,被告可以另行起訴,要求賠償。李玉珠提出賠償48萬元的訴訟請求,至今仍在調解中。宋莊畫家村房產訴訟,為國內外所矚目。現在已經看到負面效果累累:農民和畫家以及鎮村集體都受到了傷害,沒有一個贏家。當地315名藝術家聯名上書最高法院和市區領導,緊急呼吁就維護農民私房處分權和誠實守信規則出臺相關政策。
雙方本無任何爭議,就是因為面臨拆遷可能得到高額補償的誘惑,賣房人毀約翻案,而法院以“新規”判“舊案”,竟然予以支持,宣布原合同作廢。而引起的合同糾紛案件,近年來呈明顯上升趨勢。
由此可見,現行限制農宅流轉的政策,與市場化、城鄉一體化的現實嚴重背離,引發的矛盾沖突十分尖銳,再不改革創新,調整政策,已經難以為繼。
三、改革創新農村宅基地制度的基本思路
農村宅基地改革有兩種大思路,一是房地統一都歸農民所有;二是宅基地所有權仍屬集體,但將使用權作為完整的用益物權給農民。我們主張后者。初步設想是:
(一)在繼續實行宅基地集體所有的同時,賦予集體成員比較完整的用益物權,使宅基地使用權真正成為農民的一種財產權利
(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繼續實行“一戶一宅”,有面積限額,體現公平,合理保障農民住房用地;同時實行有償使用制度,允許合法的宅基地使用權隨房產買賣流轉。宅基地有償使用的政策,要體現本集體成員與非成員的差別,面積限額以內和以外的差別,新老宅基地的差別,內部價與市場價的差別,對非本集體成員使用宅基地不僅要收取更高費用,而且要規定使用期限,用經濟手段促進土地的節約集約利用。
(三)尊重所有者的權益,實現所有權與使用權的有機統一
在宅基地使用權流轉實現的收入,由集體與農戶分成;建立宅基地公共基金,用于村莊公共設施建設和對純農戶的宅基地有償使用補貼。依照《物權法》第59條和第60條的有關規定,堅持宅基地“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宅基地使用、流轉等重大事項“依據法定程序經本集體成員決定”,并由“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代表集體行使所有權”。明晰本集體成員身份,健全集體經濟組織及其運行規則,保證宅基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權利的正確行使。
(四)面向未來,區別對待,使改革的設計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續性
要研究農村居民點的演變趨勢和宅基地消亡的條件與途徑,實行分類指導。現在可以看出,北京郊區農村居民點的發展趨向在城鎮化地區,鄉村化地區和生態涵養地區各有不同,產業結構、人口構成、居住方式會有明顯差別,因而在宅基地利用的政策上需要區別對待。
(五)承認差別,鼓勵試驗,允許創新
建議中央政府支持北京開展農村宅基地政策調整和制度改革試驗,以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探索制度創新之路,為法律的修改提供實踐依據。
(作者系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