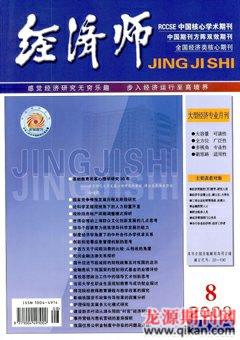無可奈何花落去
摘 要:“洪山調”是在覃懷大地流傳了2500余年的一種古老曲種,它起源于春秋末期,戰國時期得到迅速發展,兩漢時期形成規模,唐宋時期達到鼎盛。明、清時期更為盛烈,民國末期一度處于低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迅速得到恢復光大,并達到顛峰。“洪山調”的唱腔音樂系民間歌樂、小調糅合而成,屬板式變化體結構,七聲音階宮調式,音域寬闊,有頂板和閃板兩種不同風格的藝術流派。從清乾隆年間的藝人馬文彪算起,到目前止“洪山調”藝人計有10代,張清軒和馬九信有較為翔實的資料記載。“洪山調”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是在時代和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下,伴隨著民眾價值取向和審美理念的變化而逐漸顯露端倪的,進一步研究和保護“洪山調”最好的方法是遵循事物發展的自然規律,尊重文化藝術的推陳出新和取而代之。
關鍵詞:“洪山調” 板腔 藝人 衰落 規律
中圖分類號:J6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09)08-239-03
“洪山調”是廣泛流傳于河南省焦作市溫縣一帶的民間說唱曲藝,距今已有2500多年歷史。它曾經唱遍了覃懷大地,上至達官顯貴下至村野農夫,皆家喻戶曉、喜愛有加,莫不以在閑暇之余聽上一場“洪山調”表演唱為享受。但隨著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民眾的人生觀、價值觀、審美理念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洪山調”逐漸淡出了民眾精神文化生活的視野,步入了瀕亡的邊緣,日趨衰微。目前只有溫縣的馬九信一人還能表演完整的“洪山調”曲目。當地政府和一些有識之士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想止住“洪山調”發展的頹勢,于2006年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提出申請保護,2007年6月,“洪山調”藝人馬九信被授予“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榮譽稱號;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吳佳文女士親自到溫縣當地采訪馬九信先生,并撰寫題為《遠去的絕響沉郁蒼涼——訪“洪山調”藝人馬九信》一文(《四川戲劇》2008年第2期),以期引起更廣泛的關注;當地文化部門組織力量將群眾耳熟能詳的全國道德模范謝延信大孝至愛的光榮事跡編寫成唱詞,希望為“洪山調”注入新鮮血液。但“隨著現代娛樂方式的不斷出現,音樂的載體和存活空間同以前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有的音樂形式都不同程度受到沖擊,尤其是傳統音樂所面臨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1}就藝術形式本身而言,“洪山調”單調的表演形式和方言濃郁的唱腔以及有些低俗的唱詞,被當前萬花筒般精彩的文化娛樂活動沖擊得七零八落,它確確實實面臨著的藝術的冬季,已然走向了它生命周期的末端。但正如村上春樹所言:“死,不是生的對立面,而是作為生的一部分永遠存在。”所以本文認為,與其不遺余力、不惜一切代價的挽留和搶救,還不如遵循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遵循“洪山調”作為一種藝術生命的“生、老、病、死”,即使它最終消失在民眾的精神世界里,也不會磨滅它曾經燦爛輝煌的印跡,它將會作為一種藝術生命的存在永遠地留在歲月深處。遵循“洪山調”這種民間藝術的發展規律恰恰是一種尊重性的保護。
一、朔本求源
據1973年考古發現,河南焦作市西馮封村(原屬博愛縣)南宋、金墓中有彈三弦的說唱俑(實物現存河南省博物院)。三弦形制為大鼓低音三弦,俑人為坐姿,呈自彈自唱狀。三弦的唱腔屬于板腔體,腔調樸實清新,自然流暢,自由活潑,且音域寬闊,幅度較大,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這一實證為同樣以三弦為主要伴奏樂器、同樣屬于板腔體,而且曾經廣泛流行于河南省焦作市溫縣一帶的“洪山調”找到了確切存在的歷史依據。
“洪山調”是我國曲壇上最古老的曲種之一,也是一種獨特而稀有的優秀民間文化遺產。相傳“洪山調”起源于春秋末期,為晉國重臣苗賁皇所創,西漢、東漢時期盛行于民間,唐、宋時期達到了頂峰,明、清及民國時期更加繁榮昌盛,至今2500年的歷史。但因年代久遠,以及“洪山調”從藝群體的特殊性(均為盲人),清朝康熙以前的藝人皆已失考。歷史上,曾有““洪山調”獨霸覃懷(河南焦作溫縣一帶)天下”之說。據口碑資料傳,清乾隆年間的著名藝師柴明勛的徒弟達100多人,最著名的有48個,素有“半百高徒”之稱。從清乾隆年間的藝人馬文彪算起,到目前為止“洪山調”藝人計有10代。
近年來,隨著趙鐵印、范貴書、鄭松貴、申玉麟、石廣慶等幾十位末代老藝人相繼謝世,這門曾經唱遍懷慶大地的珍貴民間曲藝中的許多曲目,來不及被整理和挖掘,就隨他們飄然而去,永遠地埋藏于地下了。截至目前,唯有于2007年6月,被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授予“中國民間文化杰出傳承人”榮譽稱號的盲人藝人馬九信還能表演完整的“洪山調”曲目,但是也已經后繼無人,進入青黃不接的的凄惶季節。
二、板式唱腔
“洪山調”板式齊全多樣,曲調高亢,婉轉細膩、優美流暢,音樂表現力豐富,藝術感染力較強。它的唱腔音樂系民間歌樂、小調糅合而成,屬板式變化體結構,七聲音階宮調式,音域寬闊。“洪山調”的演出形式為坐唱,演唱時,演員自操三弦,以腿板擊節,一人自彈自打自唱,亦稱“腿板書”。在演唱風格上,“洪山調”有頂板和閃板兩種不同風格的藝術流派,頂板派是傳統的板上起腔唱法,即強拍起音,節奏平穩有力,舒展流暢,蕩氣回腸;閃板派唱法上閃板奪字用的多,即弱拍起音,具有風趣幽默、輕快活潑的風格特點。主要樂器大三弦在伴奏中,除運用按、揉、打、拍、單音、雙音等傳統技法外,還常有從高音到低音的大滑音演奏,并能模擬說話、鳥叫、鑼鼓、槍炮等自然聲響,烘托演唱氣氛,藝術效果頗佳。“洪山調”的唱腔音樂屬板式變化體,主要板式有:慢板、二八板、快二八板、滾板、流水板、大漢腔、小漢腔、昆腔、陽腔、快板、頂板。“洪山調”的曲目以中、長篇為主,另外還有些書帽、小段。詞格以七字句和十字句為主,演唱中以唱為主,偶有念白,念白為本地方言,人物語言形象生動。“洪山調”樸實無華,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是典型的、深受人民群眾喜愛的民間說唱曲藝。
三、藝人傳承
筆者查閱了《溫縣志》和其它一些相關文獻,沒有發現對“洪山調”藝人翔實的文字資料記載,由此可見,這種在盲人中間廣為流傳的曲種,也確實因為盲人的“盲文”,而耽于文字資料的保存。我們只能在百姓的記憶中尋找他們的信息和曾經唱遍覃懷大地的印跡,在群眾口碑好、印象深的“洪山調”藝人,以張清軒和馬九信為主。
張清軒(1912.4.15—1974.11.10),“洪山調”藝術大師。在河南曲藝成熟和繁榮的20世紀30年代,張清軒于1935年創立了閃板派唱法,將“洪山調”分為頂板和閃板兩大藝術流派。他借鑒、吸收了河南梆子、京劇、懷梆、大鼓書等唱腔和白口的精華部分,融進“洪山調”的唱腔,并且多用閃板唱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唱腔風格,引領了當時“洪山調”的潮頭,一時之間習之者甚眾。他還創立了三弦的“五指輪”奏法,促使“洪山調”藝術發展到了巔峰時期。1957年,張清軒以《五彩云》書目,參加了河南省第一屆曲藝、皮影會演,并且榮獲了優秀演員獎(引自何處)。張清軒“三不照”(眼盲、腰彎、腿瘸)的藝名更是婦孺皆知,其將“洪山調”唱遍方圓數百里,聲名遠揚。日寇侵華期間,身殘志堅的張清軒組織藝人冒死在百姓中演唱痛斥日寇和漢奸滔天罪行的書目,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革命斗志,打擊了敵人的囂張氣焰。他還培養了一批以胡虎臣為代表、技藝高超的盲人徒弟,對““洪山調””的發揚和傳承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馬九信(1948年10月—),河南溫縣祥云鎮張寺村人,出身于革命烈士家庭,自幼因患眼疾導致雙目失明。1963年,15歲的馬九信拜“洪山調”著名藝人胡虎臣為師,以師徒相承、口口相傳的方式專習“洪山調”藝術,比較全面地繼承和掌握了“洪山調”彈、唱、念、打、演的技藝,同年加入溫縣曲藝隊,隨師行藝八年。主要演唱曲目有《紅巖》、《雷鋒參軍》等中、長篇書目和《小姑不賢》、《小兩口抬水》、《小大姐算卦》等短篇傳統節目。1972年以來,經常在農閑時節為鄉親們演唱。1991年,溫縣文化館干部深入民間,完成了《中國曲藝音樂集成》(溫縣卷)的編寫工作,將馬九信演唱的《小兩口抬水》、《小姑不賢》等節目唱段編入其中,先后入選省、市資料卷和國家卷,且出版發行。2005年10月,在河南省第二屆民間藝術節上馬九信演唱的《小大姐算卦》榮獲銀獎。
四、衰落追因
2500多年來,曾經深深地根植于民眾的沃土的“洪山調”,為陶冶情操、凈化心靈、美化生活、家庭和睦、鄰里團結、移風易俗、社會安定等起到過潛移默化地巨大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文化藝術發展的與時俱進和人民群眾日趨多樣化的娛樂生活,廣大群眾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極大豐富。民眾對于精神享受的可選擇性、復雜性和多樣性的接納與認可,沖淡了“洪山調”在人民精神世界里的濃墨重彩,民眾的審美理念較之以前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歷史深處走來的“洪山調”正以無比孤獨的步態趔趄著漸行漸遠。而一種藝術形式的存在,不外乎遵循著這樣的三角形的立體結構關系:演員—作家—觀眾,尤其是作家,更占據著主要和支配地位的作用。從這種模式的嬗變過程中,我們可以窺見,“洪山調”由盛而衰的齲齒早已潛藏在它曾經唇紅齒白蔥籠歲月里。
首先,從演員的角度分析。“洪山調”曾有過“技藝不傳明眼人”的規定,就演員本身來說,目不能視,自然學習和練習起來會比正常人付出多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努力,意志不堅定者也不見得就能學會。而且,表演者對一部分曲詞也是不知其意,比如在有些唱段開始之前,往往會有一句念白:“大明月亮黑洞洞、樹梢不動刮大風”,問及馬九信先生其為何意、為什么要用這樣的開場白,則曰不知,老師就是這樣教的,他只需要死記硬背就行。這就在曲詞和曲調精確性上產生了一定的誤差,在帶徒傳習的過程中,必然會造成無法避免的謬傳,以誤傳誤,成為傳承脈絡中的硬傷。在筆者看來,定下這樣一條規矩的創始者,恐怕除了是因為眼盲之人目盲耳聰、心下清靜,可以心無旁騖地專習此項技藝之外,更主要、也更良苦的用心是想借此保住殘疾人來之不易的飯碗,其情固然可憫。但也恰恰是因為這種狹隘的“小行業”意識所帶來的局限性,使得“洪山調”在盛行時雖從業者甚眾,卻也只能作為目盲者果腹飽食的一時之用,終不能開出舉世矚目的藝術之花。在當時,貧困且殘疾的“洪山調”藝人多數沒有文化知識,不能賦予“洪山調”創新性的發展和更強有力的生命支援,更有甚者,為了迎合觀眾市場的需求,一些曲目的唱詞中還有許多媚俗低級的成分。同時,由于眼明者不得其技,因此便不能或無法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文字資料和演唱曲譜。在社會飛速進步、經濟高度發展的當代,瞽者已無生活之虞,且就業和謀生的方式更為寬泛,自然不需要再走村串戶、搭臺賣唱,從業者大幅度的減少,使得“洪山調”逐漸乏人問津,甚至淪落至當下的難以為繼。作為“洪山調”藝術的演繹主體,藝人們自動放棄無疑是釜底抽薪之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原本就命懸一線的“洪山調”,再生能力也被攔腰折斷。
其次,從作家這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來說,歷史上大凡曾經輝煌燦爛、盛極一時的藝術形式都有過一批偉大的、彪炳史冊的作家群體,他們創作出的作品皆成傳世之作,比如關漢卿的《竇娥冤》、王實甫的《西廂記》等作品,完美著元雜劇的金聲玉振、舞臺獨步;湯顯祖的《臨川四夢》成就了昆曲的浪漫瑰麗、極致婉約;孔尚任的《桃花扇》傳奇著明清戲劇舞臺的轟轟烈烈、悲歡離合。可以說,沒有這些強有力的創作群體的卓越貢獻,戲劇藝術舞臺上就不可能產生這么多影響深刻的優秀作品。作為一種古老而稀有的珍貴曲藝品種,“洪山調”缺乏的正是這些內容與形式俱佳的上乘之作,它甚至根本沒有固定的創作群體,更不用說擁有一批頂尖的創作高手了。不隱諱地說,“洪山調”的作家就是藝人們口中的“祖師爺”,他們在有限的能力范圍內,創作了一部分既適于在鄉間陌頭、寒村貧舍表演又方便盲人傳唱的曲目和篇目,然后再傳授給同樣以此為謀生手段的徒子徒孫,其中不乏“公子遇難,小姐養漢”的庸俗小調,甚至談不上內容健康和積極向上,更不用說能賦予唱詞深刻的內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蘊了。鑒于文學素養的低下,很難創作出具有典型意義的經世之作,“洪山調”藝人們只能自甘于草根文藝的宿命,沒有創新的曲目,就兀自傳唱著那些老段子、老節目,日復一日在廣大的農村粉墨登場。所以,構成這種藝術形式最重要的支柱——作家的缺失,即成了“洪山調”發展過程中的致命傷,這種作為藝術存在的中堅力量的缺失,使得“洪山調”缺乏新鮮血液和養分的供給,直接導致“洪山調”的藝術魅力的日漸蒼白。這些少量的由藝人代代相傳的作品,也僅僅依靠盲人們小心翼翼的口念心記,哪里能辟出一片藝術的開闊天地?這就注定了“洪山調”的生命力將會是有限而脆弱的。盡管建國后,一些文藝工作者也曾創作了一部分新的、被賦予時代意義的篇目唱詞,但這些唱詞要完全貼合“洪山調”的演唱曲調,并被盲人藝人們完全掌握也是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洪山調”藝人以傳統的盲人“扣子譜”來記錄學習的內容,顯然我們的詞作者們無法做到依韻填詞來供藝人們記唱。由于經濟利益的驅使,文化素養不高的藝人們也不愿意再付出置之死地的努力,來發揚這門“不用來謀生的玩意兒”了。同時,演出市場的萎靡也逐漸泯滅了他們創作的激情,終未再見新篇,這不能不說是“洪山調”莫大的悲哀。
最后,從觀眾的角度來分析,應該說觀眾是這個世界上最多情也最薄情的角色。當一種文藝形式符合他們的審美情趣,給他們的精神和感官帶來愉悅和刺激時,則動輒“一人唱,千百人恭聽”,上至達官貴人,下至村野百姓無一例外地趨之若鶩、狂熱追捧、如癡如醉。在馬九信先生的記憶中,一把大三弦、一副腿板、一把椅子、一張桌子就是演出的全部陣容,即使是這么簡單的演出形式,接連唱幾天幾宿的表演是很正常的。其時,臺前圍滿了觀眾,坐著的、站著的、甚至連周圍的屋頂上、樹杈上也坐上了許多觀看“洪山調”“說書”的人,老年人、青年人包括小孩子都聽得搖頭晃腦、有滋有味,時常因為觀眾太多而不得不將凳子放在方桌上演唱,為的是讓更多的人聽到和看到他的表演。更熱鬧的是,春節期間各村與村之間互換演出,舞臺上表演的有曲劇、豫劇等多種劇種,只要“洪山調”上演,舞臺下一片叫好聲,馬上成為晚會的高潮部分。甚至就連馬先生和他的愛人也是因為“洪山調”的牽線搭橋,而成就的美好姻緣,我們的觀眾不可為不多情。但是隨著物質生活的豐富,當各種各樣良莠不齊的文化娛樂活動鋪天蓋地地涌向農村的廣闊天地后,年輕人的審美情趣發生了改變,大量的快餐文化刺激著他們的藝術味蕾,狼吞虎咽之后來不及細細品味就有新的花樣接踵而至,如此眼花繚亂的應接不暇,讓他們不知道“洪山調”為何物,更不知道這曾經紅火的民間文藝曲種,愉悅過多少民眾的茶余飯后、節日農閑。隨著老藝人的相繼去世和當前表演者的“老齡化”,“洪山調”成了一種讓人調笑的“稀罕物、老古董”。大多數年輕人,甚至一些中老年人寧愿看一些毫無趣味的熱歌艷舞,求得一時的感官刺激、眼熱心跳,也不愿意聽那“瞎子三弦的嘣嘣嘣”,不被需要的無奈,讓“洪山調”狼狽不堪,使得“洪山調”不得不黯然神傷,向隅而泣。當初人山人海的演出現場已然絕跡,稀稀拉拉而又左顧右瞻的觀眾逐漸冷卻了“洪山調”藝人的心,怎能不讓人心寒的薄情觀眾?“洪山調”這朵曾經如花般嬌艷絢爛的藝術奇葩,無可奈何地步入了藝術的寒冬。但是,時代是在發展中進步的,“我們看到,每一代人的情感都有自己的獨特風格,這一時代的風格是震顫的、羞怯的或眩暈的,另一時代的風格或許就成了粗獷的,再過一個時代它或許變成了像俯視人類的上帝一樣無動于衷。所有這些風格都不是故意做出來的,而是由許多社會原因決定的。”{2}因此,我們可以指責觀眾如敝屣般地拋棄的行為,卻不能阻擋歷史一往直前的堅定步伐。
五、歸去來兮
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從來沒有哪一種藝術形式的繁榮和興盛可以無限制地延續下去,即便是有過黃金時代的昆曲藝術和國粹京劇。作為一種沉積的文化遺產,它具有永久的價值;但作為一種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戲劇現象,它已進入疲憊的歲月。{1}出身高貴的昆曲和京劇尚且如此,我們在民間摸爬滾打的“洪山調”,此時也像極了一位步入暮年的老者,一輩子的滄桑是沉淀在胸中丘壑縱橫的豐厚,而坐在晚霞中悵惘唏噓的,也許正是行將就木的蒼涼,可誰又能阻擋歷史前進的步伐?桑德諾瓦先生認為,尊重民間文化藝術本身的發展規律(即自然產生、發展、變異、消亡)本身也是一種保護。{3}負責任地講,一種文藝類型的興衰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不是一時一事就可以挽留的,一次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工作也不可能包治百病,一次中國民間文藝杰出傳承人的評選也不能立刻掀起民間文藝的學習熱潮。我們應該遵循事物的發展規律,不能留而強留之,必然會使其更加尷尬。
如今,一些文藝工作者開始留意,并且為挽救“洪山調”做著自己的努力,有將它融入到其他藝術形式再現的,比如梨花大鼓和河洛大鼓,在表演中都吸納了“洪山調”的曲調,在發展其自身藝術生命的同時也帶動了“洪山調”的發展;還有的大型文藝演出開始用時尚的形式,邀請它的參與,比如中央電視臺2007年6月9日的《鄉村大世界》欄目,華麗的舞臺和時尚的配樂以及熱情的觀眾,讓“洪山調”重溫了盛大而喧闐的演出場面;有的以論文的方式訴諸筆端,希望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幫助,洛陽師范學院的楊冬梅教授,在國家核心期刊發表了關于“洪山調”探討性的論文,{4}必然會引起一些有志于民間曲藝藝術傳承工作者的興趣和研究。筆者不敢妄言“洪山調”的明天會如何,但在藝術的洪流中,“洪山調”確確實實正在無可挽回地衰落著,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言“這是不必惋嘆的歷史必然”,它曾經有過的輝煌無法阻止它的衰落,而它的衰落也無法否定它的輝煌。{5}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會有新的、不同的文藝形式鵲起,將前一種沒落的藝術形式取而代之,這是歷史新陳代謝的必然,是文藝推陳出新的進步。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社會終究要遵循歷史發展的規律前進、發展,而人類偉大的精神創造——藝術,盡管它不可避免地遭遇著種種曲折,然而它終究要發展下去。”{6}“洪山調”也許將會以一種歷史存在留在我們記憶深處,也許會以一種嶄新的面貌被歷史和觀眾重新選擇,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將向它頑強生存的2500余年風雨歲月致敬。盡管它無可奈何地花將落去,但我們更期望著,它能夠有朝一日“似曾相識燕歸來”。
秋天是人們印象中收獲的季節,農民們在一季辛勤地勞作之后,無一例外地品嘗著收獲的喜悅和倉廩飽實的快樂。然而秋天同樣也是蕭索的,古有云:秋者,殺也。筆者正是懷著這樣復雜的心情,探尋著“洪山調”這種古老而樸素的民間曲藝在歲月的長河里由盛及衰的生命歷程,希望能為這種存續了2500多年古老藝術的搶救、傳承和研究工作,盡上自己的綿薄之力。
注釋:
{1}{3}桑德諾瓦.“有所為”亦“有所不為”.中國音樂,2008(2)
{2}蘇珊,朗格.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4}楊冬梅.“洪山調”初探.中國音樂,2008(3)
{5}余秋雨.舞臺哲學.中國盲文出版社,2008
{6}于潤洋.音樂史論新稿.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
(作者簡介:邱雅洲,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河南開封 475001)
(責編: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