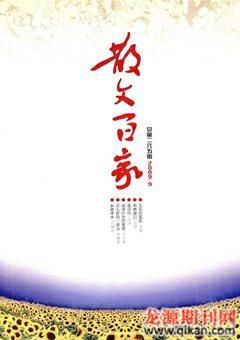品咂時光的重量
方小英
時光站成了此岸和彼岸:生長和死亡,敞開和關閉,貧窮和富足,擦肩而過和驀然回首,還有看得見和看不見的痕跡。從懵懂無知的稚子學童跨進鬢毛微衰的中年,時光宛如手中無法阻止的流沙,清晰地滑過,又清楚地烙在生命里。這個過程如此漫長,又如此短暫。在一步一步的回首之中,已悄然沉淀成細沙,積累成懷念的樣子。
樹
沿時間的河流逆向而上,我總在一個地方停留與觀望——老屋后的古樹,仿佛森林覆蓋著我的心靈和往昔。我試圖從那些樹上找到光陰的痕跡,這些古樹年代久遠,也不知是哪個朝代的鳥兒銜了種子,先在村莊出現之前就落地生根,參天蔽日把大半個村莊攏在枝椏下。小時候,每到夏天,榧樹落花,全掉在屋瓦上,夏天雨水多,堵住瓦路,經常半夜被淋濕。一家人起來找出家里所有可以接漏的家什。
不知道老樹現在是否還開花,它的內心早已空成大洞,像大海一樣容納村莊所有的變化,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時間,就像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動聲色地見證著村莊的風來云去,目睹著農人稀稀稠稠的日子。
樹群下納涼的喧鬧,還有捕蜻蜓,捉蟬,斗蟋蟀,秋風過后一地的榛果……年少時的戲趣已淡成美好回憶的一幕幕。老樹給貧寒的鄉村日子帶來很多快樂,年少純粹的快樂,并不關心自己明天要干什么,和二妮,水生他們,光著腳走在石板路上,聽蟬聲嘹亮地唱響一個個夏天。在樹的注視下我攀上了時光的高度,經歷一次次疼痛的蛻變,終于有一天我以決絕的背影離開了村莊。
如今村子已越來越空,像千年的榧樹一樣內中空洞。人們像蛾子般投奔城里的熱鬧去了,老房子兀自關著,幾個老人守著老房子獨自老著。
我知道我的來路,和樹一樣來自腳下的土地。那些樹如同我慈祥寬宏的祖輩,欣喜著兒孫們天南地北的遠行,而獨自品呷著寂寞。
路
延伸出去的房子大都建在路兩旁。路的這邊,是山;另一邊,還是山。但路,不再是那路。曾經的路是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從大山腹地開辟出來的,碎石鋪就。這頭連著外面的世界,那頭是更深處的山。小時候看起來無比寬敞和悠遠,通向一個我不知所向的遠方。
十二歲那年,堂哥用叮當作響的自行車馱我上路,使我見識了城市,一個迥異于我所在世界的世界,那些讓我目瞪口呆的事物都存放在路的盡頭。回來時,我感覺頭頂的天突然窄得無法原諒。從那時起,我就萌發了離開了它的念頭。
離開的過程艱苦而漫長,經歷了挖野菜,打柴,采藥材……那些植物的清苦至今還在回腸蕩氣。曾為了想吃雞蛋,故意把自己弄病了,母親采了草藥熬湯打進一個雞蛋竟成了我奢侈的夢想。采過黨參、半夏、魚腥草、柴胡,它們是我們心中的“銀行”,稚嫩的字跡布滿了我們的汗味。那時的冬天是真正的冬天,雪一下就是兩三天,冰天雪地,把鄉村變成鳥也飛不進來的黑白世界。高二寒假那年,路被雪阻斷,上學迫近,父親挑了我的書擔,鞋子綁上草繩,我們在泥濘的雪地里走了六七個小時才到學校。
在無數次的丈量中,我熟知這條路的每一個坡度和彎道,以及它們所蘊蓄著的隱情的歲月。從它上面走過的人和事無數,它像一座渡橋,承載了夢寐以求的期待。從這條路上出發的人們,他們回來。他們驚奇地發現這條路已被修飾得近乎完美,華麗如同走向一個風景名勝。車輪與路面彈奏著近鄉情怯的淺吟低唱,每一聲都在我心里喚醒我的存在。存在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凝視傾聽著,讓一條路穿過我的肌膚,穿過我的血管。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這是比利時詩人維爾哈倫關于道路的預言。
草
父親常常說,草民的命就是草。我從小就覺得自己就是一株草。從大地深處鉆出來,求得一抔生存的泥土,草莽中生存,野氣而孤傲地生長著。陽光將影子照亮,舉著詩經的句子,落在春天的衣襟上,如同無數關于憂傷、關于命運的小秘密。父母對我的養育可以用“含辛茹苦”來概括,這苦,就是草的清味,體現的不僅僅是植物本身的屬性,也是那個年代一種大背景。
越是物質匱乏的環境,生命力越發頑強和堅韌。那些生長在菜園的黃瓜,荒坡上的野草莓,還有懸鉤子上的金櫻子,都曾經填過我們饑餓的胃。把玉米秸稈當甘蔗,嘴邊橫吹,吹成簫的模樣,是苦澀里的那抹酸甜。我們那消化力極強的胃腸啊,堪比食草的牛和羊,甚至,在冬日里還赤足穿行在草叢刺窠中,感受枯萎和柔軟。當環境不具備嬌慣,人的生命的另一端必須長出倔強或者忍耐,就像野草在貧瘠的沙地上,雖然長得艱難,卻不愿放棄。白天割草,晚上睡在稻草上,夢可以長在柔軟的白云上。
李白高唱“我輩豈是蓬蒿人”大笑著出門,我離開村莊時沒有仰天大笑,但是我肯定也用了另一種慶幸的姿勢——我以為我擺脫了一株草的命運。
在城里扎根下來,我逐漸褪掉了鄉音,蛻去了泥土味,和城里的人一樣在健身房里流汗,在美容院里和皺紋作斗爭。豐衣足食,沒有特別為錢發愁的日子。吃不求解飽的點心,偶爾彈箏撥弦,聽雨聞香,調弄一些風雅的閑情逸致。物質一點一滴地填滿生活的空缺,那些被時光剝去外衣的苦難也蝶化成珍珠的光芒。
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質地沒變,依然是一株草!
如果以甘和苦作為幸福的分界線的話,草顯然是個悲劇角色,但是誰能肯定永遠只有一種味道呢,當一株草隨雨而生,有楔子一樣扎根的力量;因風而起,有羽毛一樣飛天的勇氣,與四季循環共處,同萬物和諧相伴,到最后也要以一朵花的姿態映在藍天碧水里。“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我終將是幸運的,遇著最滋潤的雨和最和煦的風,踩著苦澀,一步一腳地向幸福邁進。
米
鄉村躲在大山的皺折處,太陽晚出早歸,只能種單季稻,米就更賦予了寶貴的意味。每當新谷出米時,村莊的上空飄落著米飯的清香,村民的臉上蕩漾著喜色,連孩子斷奶也選擇這個時節。可是能吃上純粹的白米飯并不多,只是象征性的,多數時候,米飯一半紅薯一半,黏軟的米飯被活生生拆散。紅薯吃得我的胃直犯酸。我恨死紅薯了,那時我端一碗飯,坐到門檻上吃,把紅薯挑出來,喂雞。奶奶看見了用筷子打我,邊打邊罵,說,有紅薯吃還不知足,荒年時,叫你吃樹皮啃樹根。
先人對米的描述是那樣的唯美,“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可是記憶中稻田深處泥漿里父親佝僂的背影,母親開裂的手指,米包裹著的黑無邊無際,它從下種到抽穗到收割到碾米,向上生長的路,蜿蜒崎嶇,一步一個腳印,一粒一粒地繁衍,一季一季地生長,一餐一餐地喂養,供給我們生命的血漿。
韓美林有一篇文章,說他餓極了的時候,聽到別人講到一個“米”字就會滿嘴口水,渾身顫栗,起雞皮疙瘩。
看到這段字,我眼睛里有了淚花,吃飯是件高興快樂的事,但倘若面對米飯,流的不是口涎而是眼淚,便是滿含悲情的飲食了。
那時考大學,只要能成為非農業戶口,每月有國家供應糧,學什么都是其次的。高考的獨木橋,仿佛就是通往桃花源的必經之路:“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
我和米一樣行走,馬不停蹄地往前趕,終于走到我想要去的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傳說中叫作幸福。
現在,米不再是餐桌上的主角,成了可有可無的陪襯,甚至有些減肥的女人,常年不吃飯,只吃水果,好像跟米飯有仇,米成了她通往幸福的障礙。假如米有人一樣的心臟,它是欣喜還是悲傷?
糧食是大自然的恩賜,米是大地母親潔白的乳汁,要永遠抱有尊敬之心。或許,一粒從大地長出的米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被人們傷感地懷舊,因為曾經帶給我們無奈的酸楚,但是不要為它沉重,不魂牽夢縈,它愿意淡出生活的重心,與世人平靜相處,偶爾被感恩之心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