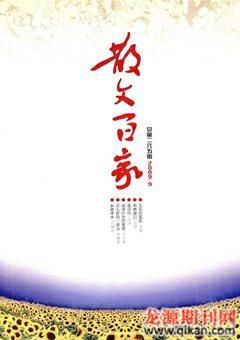漈下村苔痕
程耀愷
出門旅行,最大的樂趣,莫過于有奇遇。一如古人所言:見前所未見,聞前所未聞,最暢雅懷。四月上旬,與散文家許俊文、漫畫家呂士民結伴南行。當一行人在福建作家禾源的接引下,沿著美麗、富饒、強悍而又柔順的閩江河谷,驅車急馳之時,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前方有一片神奇的苔痕,正準備把驚艷獻給我們。
前方屏南,是地處閩東的一個山區縣。屏南有兩寶:白水洋,漈下村,據說是屏南人的驕傲。路上,禾源一副秘而不宣的架勢,只是說,到時候你們盡情把玩就是了。那幾天南方正是“蓬蓬流水,采采遠春”的好時光,世界整個兒浸泡在“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的情緒中。果然,白水洋只消望一眼,朋友們便同聲驚為天人,而漈下村半日下來,就像與睡美人,有了一場艷遇。
漈下是甘棠鎮的一個自然村,飛鳳山、馬鞍山、鳥崗山、文筆峰四圍環護,一條小溪,從高處流下,縱穿南北,溪水不舍晝夜,兩岸參差人家。千百年來,村中男女春種秋收,老實得像樹,村外田園風飄雨灑,平靜得如水。
下車伊始,鱗次櫛比的古民居,猶如巨大的磁石,一下子就將人們的興趣吸引了過去,我雖不能例外,卻在不知不覺中為無處不在的青苔所傾倒。
苔蘚,以撩撥人心的翠綠,以與世無爭的低調,在中國人的審美意識里,形成別具一格的幽況。“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花不可無蝶,石不可無苔”,“高士流連,花木添清疏之致;幽人剝啄(指叩門聲),莓苔生淡冶之光”……但凡一個“苔”字,最平淡的文字,頃刻便有了詩情;再尋常的景物,瞬息便有了畫意。今人難以想象的是,在古代文人那里,種植青苔,甚至成了一種審美追求。典型人物,當推明代的屠隆(有人說他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此公官拜禮部主事,后遭人構陷丟官歸隱,董橋說他“家境雖然貧寒,居然念念不忘經營書齋情調,種蘭養鱗之外,洗硯池邊更沃以飯瀋,引出綠褥似的青苔。”
人為的青苔,或可賞心悅目,格局終歸有限。漈下村的青苔,如果說是大自然的手筆,不如說是山川與歷史野合的私生子,嬌生慣養固然談不上,遮風避雨亦不可求,它們像一群日曬夜露的野孩子。因為野,所以生機無限,因為野,少限制,無拘束,所以并不寂寞。眼前的漈下村,除了大姑娘的臉蛋,小媳婦的乳房,即使是屋舍的墻體,庭院的廊柱,巷陌的石徑,溪流的護坡,先人的墓道,乃至榕樹的根須,水碓的輪頁,亭臺的美人靠,溪上的獨木橋,總之,凡磚木土石,不避陰陽,不挑上下,青苔默默無聞地經營著,當仁不讓地守護著。若是站在文筆峰遠眺,青苔宛若漈下村的綠色衣衫,但身臨村中伸手觸摸,你馬上就覺得,青苔其實是漈下村的皮膚。皮膚是不可替換的,你無法把它與村子剝離開來。
青苔之于漈下村,既是獨特的自然景觀,也是獨具的人文景觀。我們在村里漫步,與村民聊天,到農家做客,逐漸體會到,漈下村靈氣、風致、姿色、氣味的聚集與釋放,都是通過青苔來完成的。如果不是青苔,所謂“朝天馬首”“眠地牛蹄”“石龜拱北”“彩鳳朝陽”等三十六景,定然黯然失色。如果不是青苔,所謂“地瓜真甜,玉米真香,山風真爽”的贊譽,就是一句空話。如果不是青苔,所謂千年古村落、明清古建筑的價值,或許大打折扣。漈下村的青苔,讓漈下村變得古樸而鮮艷,讓漈下村的人,過上簡單而真實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