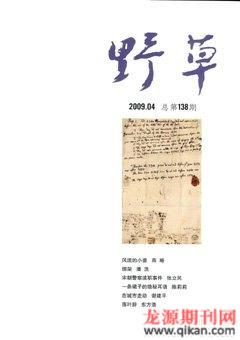綁架
潘 洗
十幾天后我們才知道,團長那天中午為什么吞吞吐吐只說了幾句就匆忙掛斷了電話。我們從刑警隊那里獲知,團長的兒子王遙被綁架了,我打進電話時幾個警察正在他家里了解案情,并警惕地關注著綁匪的動向。
可當時我們哪能想到這些,我們還以為這小子老毛病又犯了。平日里說的比唱的還好聽,又是秧歌又是戲的,可一到關鍵時刻就掉鏈子,團長沒少干這樣的埋汰事兒。用老田的話說,想讓團長出血請客,還不如從自個兒大腿上割塊肉來得痛快些。老田的說法固然有些夸張,但團長的錢包捂得比較緊,這的確是我們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關于這一點,如果你讀過我以前寫過的那篇叫《煎熬》的小說,肯定會對他有個大概的印象,那便是對團長發跡之初的真實寫照。也有哥們說不至于吧,此一時彼一時,團長現在又不缺錢,哪還能那么摳擻?再說了,這可是大家都定好了的事兒,怎么能說改就改呢。
大家都定好了的事情,是指我們每個人都要在自己過生日那天,請其他幾個哥們,帶著媳婦兒,好好出去撮一頓。飯局一般都設在晚上,男男女女加在一起差不多有20個人,得擺兩桌的樣子。酒足飯飽之后,讓女人們回家督促孩子寫作業去,我們這些大老爺們繼續在外邊撒野。也就是去找家歌廳練練嗓子,自然,少不得要找小姐陪著喝酒、唱歌。這已成了程式化的習慣打法,兩年時間下來,弟兄們依然情緒高漲,一點都沒覺得枯燥乏味。說白了,還不是沖著那些年輕、乖巧的小丫蛋們去的,這可能才是我們心里癢癢的最想做的事情,大家對此也都心照不宣。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哥們之間的感情日見其深,必須承認,歌廳里那些小丫蛋兒們功不可沒。
如果還用老眼光看人,那也實在有些冤枉團長。我們這10個人中就數團長的生日最小,是在農歷十月初九。剛開始那年團長就安排得相當到位,飯后不僅唱歌,還增加了一頓燒烤,算是個比較完美的收尾。這不,他又拍著胸脯許愿,如果時間趕趟兒,就再去桑個拿,一定要讓弟兄們舒舒服服、干干凈凈回家。雖說團長名下的那個鎂砂礦效益一般,主要是因為他有個腰纏萬貫的姐夫,他不過是掛在他姐夫的斗子上掙點小錢而已,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他也算是我們這些哥們堆里的富豪了,我們也樂得趁機痛宰他一刀。
那一年的冬天來得早,玉城剛剛進入11月份,天兒就冷得嘎嘎的,是那種陰沉沉的干冷。那天臨近中午時,老段打電話給我,先把冰冷的老天爺咒罵了一通,然后問我晚上的安排有沒有變化。我說是團長請客,又不是我請,你直接打電話給他唄。老段說靠,誰不知道你軍長面子大,團長基本上只聽你一個人的。我心中竊喜,嘴里卻還謙虛地說哪里哪里。
老段說得不錯。我這人辦事講究個丁是丁卯是卯,所以一旦張羅點什么事兒,大家還真都給面子。以前哥幾個聚會時經常文齊武不齊的,團長總借口忙,磨蹭著不來。對付團長我有招兒。我說讓你來是帶著嘴來喝酒的,又不是讓你帶錢包來買單的,你磨嘰啥呀?一番敲打,團長有些不好意思了,忙屁顛屁顛地趕過來,出現在飯局上。這次輪到團長做東,他請的是大家,我把大家的事情攬過來倒也不是裝相,而是因為我反復掂量過跟團長的這份交情。我想,我在團長面前說話好使,可能與我當年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借給他5000塊錢有直接關系。團長經常掛在嘴邊的就是“這年頭”如何如何,但是,“軍長講究,他老人家在關鍵時刻拉了我一把”,云云。顯然團長沒有看到我那篇《煎熬》,如果他知道我在小說里面抱怨他不按時還錢,那他一定會像吝惜腰包里的錢一樣吝惜對我的溢美之詞了。
我之所以記得那天是13日,是因為每個月的14日是我們單位發工資的日子,多年來雷打不動,一般不會提前,更不會推遲。這個月總公司提前把工資撥款下來,我這個主管會計就自作主張提前把工資發了。總得把工作上的事情做個妥善安排,才能放心大膽地出去吃喝玩樂,免得第二天起來暈頭漲腦的,容易出錯。事后,我們都知道了,這不僅僅是單位職工喜笑顏開地提前領取薪水的一天,這一天,還發生了一起震驚玉城的綁架勒索案。2002年11月13日,農歷十月初九,團長過生日,這天,他的兒子王遙被綁架了。
然而在當天及后來的10多天里,我們對此卻一無所知。這說明警方在辦案初期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到位。那天午后一上班,我就撥了個電話給團長,問他晚上的具體安排,要是沒什么變化,我可就通知下去了。只聽團長壓低了聲音說,我現在有點急事,晚上的活動取消了,以后再跟哥幾個解釋,找個時間再補請。說完就匆匆把電話掛了。事后想起來,團長的聲音有些低沉、沙啞,還透著一股焦躁、不安和驚慌。但我壓根就沒往別處深想。我在辦公室給團長打電話時,二濤子和老田兩個大閑人就坐在我對面。我一愣神的工夫,他們倆忙問怎么了怎么了?我感覺有些訕訕的,就像團長當面撅了我似的,勉強對他倆擠出一點笑容:得,大餐吃不著嘍,團長說他有急事,今晚的會餐取消了。
我們三個開始分頭打電話給其他哥們,相當耐心而又極其遺憾地通報了這個壞消息。頓時引來罵聲一片。言語之間,我們三個都有意無意地將這把火引向團長。誰叫他言而無信呢?本來答應得好好的,說推就推了,這叫什么事兒呢!再說了,即使安排有變化,也得提前吱一聲吧?大家都是交往了10多年的哥們,誰不了解誰,說句不雅的話,連每個人那個部位長了多少根毛都清清楚楚,怎么還能干這種損出胰子的事情來,也太不講究了吧……我猜團長那天一定會感到耳根發熱,那肯定是哥幾個在背后叨咕他呢。實際上他也的確已經心急如焚,但不是因為我們,而是因為他的兒子。
接下來的幾天,哥幾個只要聚到一塊兒,準會議論這事兒。我們也都在猜測,團長爽約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說老實話,我們也不怎么相信這小子是臨陣脫逃。我們也想到了好幾種可能,比如他跟人結怨啦(聽說海城的黑道勢力已介入了玉城的老玉礦與鎂礦),比如家中突遭重大變故啦,比如遇到了重大商機啦,等等,但都一一被排除。最后我們將原因鎖定為兩點:一、團長跟他媳婦兒小鄒同床異夢已多年,這小子是不是在鬧離婚呀?二、最近這幾個月,團長跟一個叫雪眉的小丫蛋兒打得火熱,兩人已經好得如膠似漆,據說雪眉已經珠胎暗結,又給他懷了個小團長。經過進一步的梳理,我們得出了一個初步的結論:十有八九,團長是因為跟雪眉的事情被他媳婦兒察覺了,兩口子正鬧得不亦樂乎,家丑不可外揚嘛,所以團長才瞞著大家。毒舌老田更是描繪了一幅活靈活現的圖景:團長正跟雪眉在床上熱火朝天地忙活著,被跟蹤而至的媳婦兒逮個正著,于是,一場離婚大戰的好戲拉開了帷幕……
我對這種猜測一直半信半疑。雖說現在這社會離個婚就跟撒泡尿一樣容易,可不離婚,也沒影響團長在外邊找丫蛋兒呀。不光在玉城,無論在什么地方,一個男人,特別是兜里有倆小錢的男人,身邊領個丫蛋兒出來晃,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家里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玩一玩,別過火,這有啥大驚小怪的。既然什么都不耽誤,干嘛要離婚呢?傻子才離婚呢。團長話多,除了閉口不談自己兜里的錢,他那些陳年爛谷子的破事兒,隨時都會從嘴里蹦出來,就連睡個丫蛋兒也要在哥幾個面前顯擺顯擺,要是真離婚,也沒必要這么藏著掖著。我們至少還能假惺惺地過去勸勸,沒準還能給兩口子找個臺階下。至于聽不聽,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老張鬧離婚時我們弟兄們倒是組團上門勸阻了,好話都說了好幾火車皮,到頭來還不是照樣離了!離了還不是照樣住在一起!
團長那邊好幾天都沒動靜,我們也不好再打電話催他。不就一頓飯的事嗎?不吃這頓飯,還能把牙饞掉咋的,再怎么說,也不能為這么大一點小事兒把哥們感情弄夾生了。團長這人就這樣,沒辦法。沒準哪天這小子良心發現了,再補請一頓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關于團長請客禿嚕了這事兒也就這么輕輕撂下了,直到大約一周后,雪眉打電話找到了我。
哥幾個自然都還應該記得雪眉,她就是小張過生日那天會餐后,在滾石歌廳唱歌時,陪團長的那個小姐。清秀,骨感,蜂腰,豐乳,豪飲,這些便是這個20多歲的海城女孩留給我的印象。當然,這個印象是后來跟雪眉熟悉了之后才逐漸形成的,她給我們的第一印象卻極其惡劣。大夏天,別的小姐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就她穿一個小T恤,似乎也沒化妝,嘟著嘴,一聲不吭,只在一邊抽煙,還把自己嗆得直咳嗽。老田喝大了,罵罵咧咧湊過去,老妹呀,講點職業道德好不好?哥們花錢是來買你笑的,可不是看你給我兄弟使臉子的。雪眉冷冷看了老田一眼,猛吸一口煙,又狠狠吐出去,什么都沒說。老田大怒,抓起個啤酒瓶,你信不信我一瓶子把你腦袋給開了?媽個B的,還不給我快滾!雪眉竟然呼地一下站起來,噔噔噔,把門一甩,揚長而去。老田手一揚,酒瓶子追著雪眉飛到了包房的門口,摔得粉碎。大家一下子都站起來,大著嗓門問怎么回事。吵鬧聲驚動了領班,他急忙過來賠不是,說這個丫蛋兒才來,跟對象鬧別扭了,心情不好,又不懂規矩,哥幾個別和她一般見識,我再給這位哥換個溫柔點的。我們都是這兒的常客,有幾個哥們他們也惹不起,再說又是他們理虧,所以那領班只好一個勁兒地好言安慰。要是換了別人,進來兩個膀大腰圓的保安就給你架出去了,再賞你兩個耳光,臨走,別把賬單忘了。那天晚上我們借著酒勁兒都不依不饒的,最后不歡而散,但做東的小張可省下好多銀子,包房費、酒水全免了,那幫小姐看到要打起來了,也都作鳥獸散,哪里還敢要小費呢。先前請客的幾個哥們心中不平衡,到底讓小張又請了一次桑拿才算完事。
誰能想到,團長后來竟然會跟雪眉勾搭上了呢。等大家知道團長的“妹兒”就是滾石歌廳那個脾氣暴躁的小姐時,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這個丫蛋兒有些面熟。我努力想回憶起那天晚上有沒有什么苗頭,卻發現亂糟糟的根本沒什么印象,光顧著吵吵鬧鬧喝酒了,只恍惚記得她是個板著臉坐在那兒抽煙的瘦瘦的小丫蛋,直到她甩門而去,我都沒有仔細看看她的樣子。我們都很同情團長。團長也太沒眼光了,再怎么也不能剜到筐里都是菜呀,只要有錢,高挑的、漂亮的、豐滿的還不隨便挑,我們就納了悶了,肥肉、瘦肉、五花肉什么都有,團長干嘛把一堆排骨當寶貝呢?可這世界上有些事情偏偏就這么邪門,他倆到底粘糊到一塊去了。好聽的,管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粗魯點的,可就是“王八看綠豆——對上眼了”。起初,我們出去唱歌時,團長總是抄起電話打給雪眉,雪眉也是隨叫隨到,哪怕正在陪客人喝酒,她也會立刻撇了客人,有時連小費都不要了,儼然成了團長的專業陪侍。老實說,我們這幫人在出去玩的時候,找個感覺不錯的、相對固定的小姐陪并不奇怪。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發現,雪眉已頻繁地在團長身邊晃來晃去,我有好幾次在街上巧遇雪眉膩膩歪歪坐在團長那輛破普桑的副駕駛座位上,這才明白,他倆的關系已經相當不一般了。我馬上打電話拷問團長,團長嘿嘿嘿只是笑。我能想象得到,電話那端的團長此刻露出了幾顆大白牙,轉過身去,幸福地望著身邊的雪眉,雪眉嗔道:哥你干嘛呀?這么色迷迷地瞅我?小心開車……
后來我逐漸發現,雪眉這丫蛋兒其實還是挺順眼的。很瘦,腰細得簡直就像一根鉛筆,胸部也很小巧,就因為附著在骨感的胸脯上,倒顯得頗為豐滿。可能團長就稀罕這種骨感的丫蛋兒吧,我就不喜歡,怕硌手。除了這薄俏的身材,雪眉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能喝酒,不僅陪團長喝,也跟大家伙喝,整個五六瓶啥事兒沒有。雪眉對老田一直耿耿于懷,老田遇上她算是倒血霉了,差不多每次都被灌得晃晃蕩蕩直翻白眼,卻又礙于團長的面子,不好發作,最后老田都開始躲著雪眉了,實在躲不掉就揣幾個藥丸來逃避喝酒。我們也常常在邊上煽風點火,看老田與雪眉拼酒,這已成為我們哥幾個的一大樂事。出來混的小姐,誰還沒有兩把刷子?臉蛋兒、嗓子是資本,酒量好也是一種資本。不過在我看來,更重要的可能應該是某種感覺。總的來說,找小姐、見網友,就跟找情人差不多,關鍵是找對感覺。在我印象中,海城人心思縝密、聰明絕頂,來自海城的小姐也都是有心機、善于算計的,但我直覺雪眉不這樣。她也就是個咋咋呼呼、直來直去、沒啥心眼的小丫蛋兒,清爽而不忸怩,還沒有混跡歡場所歷練出來的那種甜言蜜語、笑意盈盈、取悅于人的本事。在這個充斥著虛凰假鳳、虛情假意的年代,某些簡單而本真的東西尤為難得,反而會讓人刮目相看。
不知道團長是炫耀呢還是真的相信我,他經常露出他那幾顆大白牙,嘿嘿笑著,跟我磨嘰他跟雪眉那點事兒。團長說,軍長你不知道呀,跟身材薄俏的丫蛋兒上床真過癮,一用力好像要穿透了似的,那感覺,嘿嘿嘿。團長說,雪眉這丫蛋兒挺可憐,跟對象黃了,一氣之下就出來當小姐了。團長說,雪眉不是貪財愛錢那種勢利眼,這年頭像她這樣的小姐可不多了。團長說,這丫蛋兒心眼挺好的,我給了她點錢,她都寄回家給她媽了,還挺孝順呢。團長說,媽拉個巴子的,一不小心有了,還是哥們火力猛呀。團長又說,軍長你快給我拿個主意吧,雪眉這死丫頭非要生下來,怎么弄?
簡直是大洋河朝西邊流了,團長這陣子好像突然間悠閑起來,他不僅經常出沒于我的辦公室,還經常請我出去坐坐,并且搶著買單。他自然會帶著雪眉,我知道自己就是一只锃亮的大燈泡,有時把自己也烤得迷迷糊糊的。就在團長過生日的幾天前,團長把我約到一家茶樓,很嚴肅地向我討主意,他愁眉苦臉的樣子很好笑。其實也難怪他發愁。雪眉因為身體的緣故,不宜做流產,按照大夫的說法,這個如果再打掉,將來就沒法再懷孕了。一個執意要打掉,一個執意要生下來,事情就僵住了。眼瞅著都3個月了,幸好已入冬,雪眉穿著件蓬蓬松松的羽絨服,才把已經顯懷的肚腹遮蓋起來。我知道這主意可不好出,但我還是答應團長試試。雪眉接到電話一會兒就來到茶樓,她看上去好像更加消瘦了。我轉彎抹角地幫她分析利弊,可說了半天也沒有說到點子上。雪眉說,潘哥,你別說了,你是個好人,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她朝團長冷冷地挖了一眼,說,我就是想把這個孩子生下來,我自己養還不行嗎?誰都不用勸我,誰說都不好使!等團長追著氣鼓鼓拂袖而去的雪眉走了之后,我自己想想,靠,我這是何苦呢。
雪眉知道我的手機號碼倒沒什么,但給我打電話卻讓我有些意外。這么說吧,雪眉本來是某只鍋里的,現在被團長盛到了碗里,那別人就不好染指了,至少我們哥們已經把她當成了團長的女人。雪眉屬于團長,一般情形下,她只能打電話給團長,這就是游戲規則。可雪眉卻沒有這么多顧忌,她在電話里很著急,問了一大堆問題:王哥他怎么啦?是不是出什么事兒了?他怎么不接我的電話?我都好幾天沒看見他了。他也不是那種不講究的人呀,難道就因為我肚子里的孩子,他就把自己藏起來了嗎?
聽得出雪眉火氣很大,好像我就是團長似的。我耐心聽她說完,告訴她我們這哥幾個也都不知道他現在在忙什么,但他肯定是在忙什么大事,等他忙過勁兒了,一定會聯系你,放心吧。
等他忙完了,孩子也生下來了!電話那端的雪眉冷冷一笑,讓我心中一凜,一種陰森森的冷氣從我的膝蓋骨那里突突突冒了出來。
是啊,團長這小子到底在干雞巴啥呢?整得神神秘秘的!
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困擾我多長時間,幾天后我們就被一一叫到刑警隊訊問。我們從警察那兒得到了確切消息:團長的兒子被綁架了。
此前警察已經秘密排查了一輪,一無所獲,便又擴大了偵察范圍。團長的親戚、朋友、鄰居、生意伙伴等等,一個都不放過,像篩砂子一樣又過了一遍。這第二輪就把我們這幫哥們給罩里頭了。警察問我們的問題大體都一樣,比如:你跟王崇平時關系怎樣?最近有沒有什么金錢往來?知不知道他最近得罪了什么人?等等。還吩咐我們:為了盡快破案,希望暫時保密,如果想起什么線索,及時向警方反映。我想,警察辦案肯定也是靠某種直覺的,他們打眼一看就知道我們這些人不會作案,所以沒幾分鐘就完事了。倒是老張在那兒被盤問了半個多小時,因為之前有一天晚上他借著酒勁兒在電話里向團長興師問罪,車轱轆話說了好幾分鐘,電話號碼被警方監控,解釋了老半天才被放回來。刑警隊就在我單位斜對面,好多哥們完事了就聚到我辦公室,大家伙都嘲笑老張:小樣兒,讓你得瑟,喝多少假酒呀,半夜三更騷擾人家,差點被當作綁匪抓起來,活該!開過玩笑后轉念一想,團長的兒子還生死未卜呢,大家的心忽倏一下又懸了起來。
鑒于案情毫無進展,并且消息已經走漏出去,在案發之后半個月光景,也就是我們被刑警隊找去問話之后第三天,警方決定將這個案子由秘密調查改為公開偵查。于是,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像雪片一樣飛滿了整座玉城,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幾乎所有的玉城人都知道,有個8歲小男孩被綁架了。開始是為這個孩子的命運擔心,緊接著為自己的孩子擔心,許多家長都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生怕自己的孩子一不小心也被綁了。
雪眉再次打電話約我那天是個周日,我剛剛吃完晚飯。媳婦兒收拾碗筷,女兒做作業去了,我靠在沙發上跟媳婦兒說話。因為是周末,我難得在家吃頓飯,媳婦兒做的又是我愛吃的酸菜燉豬肉,我吃得都有些撐著了,就表揚了她幾句,說還是家里的飯菜香呀,還是咱媳婦兒的手藝好啊。媳婦兒撇撇嘴,家里飯菜好,那你們還總出去得瑟!神色卻很得意。手機響的時候,我還沒接呢,媳婦兒就告誡我,大冷的天,別出去喝了,你明天還要上班呢。說老實話,這種鬼天氣誰愿意出去挨凍啊?可雪眉在電話中都要哭出來了,我想到同樣心急如焚的團長,心一軟,就答應了。媳婦兒聽見了電話中是個女人的哭腔,狐疑地看看我,沒再說什么,看我匆匆穿鞋往外走,她在我背后說,多穿些,暖和點兒!
回家后,我就把跟雪眉見面的經過一五一十對媳婦兒和盤托出,當然,我也是避重就輕有所取舍。說到底,我是為了團長才見雪眉的,我可犯不著給自己背上個黑鍋。團長和雪眉的事兒在我們哥們中間早已見怪不怪,但也沒有誰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回家跟媳婦兒說這些閑話。這也是一種默契。想想吧,一旦男人在外面有個風吹草動的,往往女人知道得比較晚,而且最后那個知道的肯定是當事人的媳婦兒。我媳婦兒跟小鄒關系也不錯,但我相信,她絕對不會把這些事情說出去的。有時候,保守某種秘密,其實是一種善意的保護。
考慮到雪眉的身體狀況,我們約在她住處附近的一家茶樓見面。真別說,在哥們堆里,目前還真就我一個人知道,這個住處是團長給雪眉租的。我猜團長肯定很得意,忙累之余,能摟著個骨感小丫蛋兒睡覺,那簡直就是神仙過的日子啦。設想一下矮胖的團長跟瘦削的雪眉在床上的樣子,就像一只皮球在一塊搓衣板上面滾來滾去,我忍不住想笑。但我現在卻笑不出來了。
仙女雪眉很憔悴,她把自己裹在雪白的羽絨服里,顯得更加柔弱無助。開始都沉默著。我點的綠茶已經續了一壺水,雪眉那杯熱奶還沒動,只是失神地望著小包房中的某處。良久,雪眉說話了。她說,我都快20天沒看到王哥了,一張口,眼淚就在眼圈里打轉了。
他家里出了這么大的事兒,自然不能分心來看你,你也得體諒他。說完我就有些后悔。這話聽上去干巴巴的,沒有一絲溫度。靠,無論換了誰,兒子被綁走了,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哪里還有心思想著女人?
潘哥,這個我懂,放心吧,這時候我不會去煩他的,可我就是太想他了,我真想見他一面,我也想安慰安慰他,這樣下去,我擔心他會受不了的,我心疼啊。可我又不敢給他打電話……雪眉啜了一口都快涼了的熱奶,定定地瞅我:潘哥,你說我該怎么辦呢?
被人信任可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兒。我猜,團長可能是因為比較信任我(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沒有更值得信任的人了),才讓我出面勸說雪眉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結果我無功而返;現在,面對著滿面愁容、可憐巴巴的雪眉,我能給她出個什么樣的高明主意呢?
說實在的,理智告訴我,正好趁這個機會,讓雪眉把孩子打掉。這一則可讓團長解脫出來,二來也讓雪眉絕了那份念想。畢竟她不可能嫁給團長,這也是為她好。團長開始向我問計時,我曾經果斷地告訴他,必須做掉!孩子生下來,你媳婦兒早晚會知道,你怎么應付?即便所有的事情你都能擺平,可雪眉到底是你孩子的親媽,你能不對孩他娘牽腸掛肚?就算你離了,難道你真能娶一個小姐回家?哪怕她已經給你生了個孩子。剎車吧你,別到時候不好收場。
我早已不把雪眉看作混跡于歡場中的小姐,她骨子里其實還是個好孩子,還葆有善良的天性。眼前的雪眉只是個需要幫助的小丫蛋兒,男人總是憐香惜玉的,我也不例外。最重要的是,我幫她,那也是在幫團長。可是雪眉的肚子到底應該怎么辦呢?我望著她,很小心地斟酌著說:雪眉呀,我是把你當作我妹妹,才跟你這樣說的。我在想,要是我的親妹妹攤上了這種事,我肯定也會毫不猶豫地告訴她,把孩子做掉!不管兩個人感覺有多好,感情有多深。你還年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你要冷靜思考,想得周全一些,千萬別沖動,到時候后悔就晚了。其實我還有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如果是我的親妹妹出了這樣的事情,我也會心疼。
雪眉只是用攪拌棒攪著杯中的牛奶,一味地搖著頭,就是不吱聲。團長怎么攤上個這么死心眼的人呢?但那一瞬間我分明有點嫉妒團長了。要是有這么一個動真情、講義氣、不貪財的小丫蛋兒跟著我,那我也算值了。
良久,雪眉說話了,她既像是在問我,又像是在自言自語,語調沉郁卻又有些語無倫次。她說:王哥他是真愛我嗎?他現在會想我嗎?我想他。我是真想把孩子生下來,也不枉我和他好了一場,再說,我可能再也不會生孩子了。我就是想跟他好,我又沒有逼著他要他怎樣,我也沒圖他錢。我想見見他,潘哥你得幫幫我。我有辦法讓他答應我把孩子生下來。一旦他兒子有什么意外,我的孩子也是他的親骨肉啊……
我跟媳婦兒躺在被窩里說起這事兒的時候,沒有復述雪眉這個奇怪的、讓人不寒而栗的想法,有些事情是一定要輕描淡寫的。而另一些就需要大肆渲染,比如說,雪眉這個小丫蛋的種種優點。我說雖然雪眉是個小姐,但她卻是個少有的、講究的小丫蛋兒,我感覺她跟團長是真心的。媳婦兒開始是背對著我,現在把身子轉了90度,變成一個舒展的平躺姿勢,我知道,媳婦兒的氣也逐漸順了。
但她對我說的話還是有些不以為然,語氣里面全是懷疑:照你這么說,這個叫雪眉的小姐倒是女中豪杰了?如果真是這樣,在那樣的大染缸里還有這樣的小姐,還真是難得呀。對了,她肚里的孩子多大了?3個多月?再不做,可就來不及了。
媳婦兒微微嘆了口氣,不知道王遙現在是不是還活著,我看兇多吉少,唉!怎么就攤上這樣的事兒了呢?小鄒都快崩潰了……
媳婦兒又說,團長的事兒你怎么這么上心?你是不是也看上人家團長的小丫蛋啦?你可別趁火打劫呀!連團長這樣老實巴交的人都養小姐了,你能好到哪里去,怪不得你們經常深更半夜才回家,在外面捅捅咕咕的,敢情是有人啦,說!到底怎么回事?
我嬉皮笑臉地往她身上湊,說,媳婦兒你還不了解我嗎,我可不要那種骨感美人,我就稀罕你這樣肉乎乎的……
關于這起案子,玉城人民有著各種各樣的猜測,不時還有人透露一下案件偵破的細節,小道消息幾乎每天都在傳播。老田跑到我單位,把門鎖上,神叨叨地跟我說,軍長,我怎么感覺這個案子跟雪眉有關系呢?我急忙打斷她,你可別瞎說,這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呀,心里卻咯噔一下子,那種似曾相識的、陰森森的涼氣再次從我的膝蓋骨那里咕嘟咕嘟冒了出來。老田說,我當然也沒有什么證據,我就是憑一種直覺,雪眉那個丫蛋兒其實鬼精鬼靈的,根本不是個善茬兒,團長肯定是被她單純的外表給蒙蔽了。我突然想起了什么,就問老田,警察找過雪眉了嗎?老田反問我,你認為團長能跟警察說這事嗎?誰知道呢,這還真不好說。我內心里突然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如果真是這樣,那太可怕了。但我不相信這個案子會跟雪眉扯上聯系。
我領著雪眉去見團長,更堅定了這種看法。我們悄悄來到團長家,用電話把團長叫出來。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在樓梯緩步臺處緊緊擁抱,仿佛要把對方牢牢箍住,不肯撒手。我看到雪眉淚流滿面,那應該是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情流露,眼淚是騙不了人的。
回到單位,我一個人坐在暖氣充足的辦公室里發呆。以前在電視劇里才能看到的綁架案,如今就發生在我們身邊,而且是我的好哥們團長的兒子被綁了。望著窗外斜對面刑警隊的辦公大樓,我一再想起老田跟我說過的話。我一直在猶豫,是不是應該到刑警隊反映一下新的情況,那或許會對破案有幫助。可是,這怎么可能呢?
在12月初的那幾天里,我備受煎熬,直到12月5日案件告破。
關于具體案情,各級媒體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破案后的一個多月里,有數家報紙陸續進行了報道。《玉城日報》動作最快,在2002年12月9日第3版,用一個整版推出了由特約通訊員沉濤、首席記者劉丹采寫的長篇通訊,題目叫《邪惡的念頭,罪惡的深淵》,對這起綁架案的來龍去脈及偵破過程做了比較詳盡的報道。沉濤是玉城公安局政治處的干部,也是個作家,我跟他有些交往,我想他的說法基本是可信的。其他各家媒體的報道,都跟《玉城日報》的口徑大同小異,在篇幅上也都不惜筆墨。某國家級大報在2003年1月14日的報道則比較簡短,還不到300字,就像是用典型的新聞語言對案子進行了一次小結:
綁架殺害7歲幼童玉城一罪犯被判死刑
本報訊(通訊員李萍記者趙文良)因手頭缺錢,竟然把鄰居的7歲兒子綁架并殘忍殺害,事后向小孩的家人勒索50萬元。2003年1月6日,王洪慶被當庭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王洪慶與王某是同樓門的鄰居,因苦于沒有開礦資金,便將黑手伸向王某的7歲兒子王遙。2002年11月13日早上7時,當王遙從四樓家里走到三樓緩步臺時,等候在此的王洪慶用套帽套住王遙的頭部,把王遙拖到自己家。王遙拼命掙扎著把套帽拽掉,王洪慶見已暴露,便兇狠地將王遙捂死。11月15日,王洪慶給王某打電話,告之其子已被綁架,向王某索要50萬元現金。警方接到報案后經20余晝夜的偵查,終于將王洪慶抓獲。
根據民間普遍流傳的一些說法,我再披露幾個在各家媒體的報道中未被提及的細節:
1.王洪慶的最終落網,是因為他用自家的舊臺歷紙所書寫的勒索信露出了馬腳。一位高明的文檢專家經過比對后明確指出,百分之百就是這個人了,警察便對王洪慶用了一些手段。據說王洪慶還扛了一宿,但到底沒有扛住,招了。
2.王洪慶將王遙沉尸東山公園微山湖的冰層下,當他帶著警察指認現場時,差點被群情激憤的數千圍觀群眾給撕成碎片。許多群眾激動地表示,這樣死有余辜的東西槍斃他都是輕的,應該一刀刀把他活剮了才解恨。
3.法院以綁架罪判處王洪慶死刑,這個結果沒有出乎人們的意料。人們普遍認為,王洪慶肯定活不過這個春節。果然,死刑判決很快被省高院核準,王洪慶在壩墻子那兒被執行槍決。他被槍斃的那天是1月24日,臘月二十二,連小年兒都沒過。
好多人都參加了1月6日庭審現場的旁聽,那天玉城下了入冬以來的第一場小雪。說是小雪,其實只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雪花兒在北風中飄來飄去。王洪慶被全副武裝的法警押進法庭時,引發了一陣騷動,靠近前排的地方,是團長的親屬們,他們叫著喊著沖上去踢打王洪慶,被法警隔開。庭審時公訴機關運用了多媒體示范系統,當戴著紅領巾、滿面稚氣、微笑著的王遙的照片展示在屏幕上時,現場哭聲一片。聽到王洪慶被當庭判處死刑時,旁聽席上爆發出一陣陣熱烈的掌聲。
我在庭審現場竟然看到了雪眉。是她,沒錯。一身雪白的羽絨服,罩在她略嫌臃腫的嬌小身軀上。她就在我身后不太遠的地方,正癡癡地望著坐在證人席上的團長,神情專注而又恍惚。我想,她的雙眼一定蓄滿了晶瑩的淚水。
這是我最后一次看見雪眉。
此后,我們這幫哥們過生日聚會的慣例就被打破了,我們甚至再也沒有嘗試著聚過,聚也聚不全,干脆算了。這定期的聚會一斷,漸漸地,哥幾個的感情也有點散,有點淡。
團長那次整禿嚕了的請客直到今天也沒補上,當然,再也不會有誰提起這個話茬。他現在可是真掙著大錢了,據說趕上了好時候,鎂砂行情看漲,他忙得腳打后腦勺,終日見不到人影兒。如果你在玉城大街上看見一輛掛著黑牌兒,車牌號是“遼C××888”的白色本田疾馳而過,毫無疑問,那就是團長的車子了。只要在街上看見我,團長定會停在路邊,搖下車窗跟我打個招呼,然后鄭重表示,這年頭,除了咱哥們感情,別的全都是扯王八犢子,等我忙過了這陣子,咱們這幫哥們得好好聚聚了,軍長你出面張羅,我買單。這話他說了好幾次,我相信團長不是忽悠我,只不過他太忙了。
有一天,我看到車上坐著他們一家三口。小鄒氣色好多了,他們咿呀學語的小女兒正茁壯成長,團長呢,依然嘿嘿嘿笑著,不時露出幾顆大白牙來。好幾年過去了,從他們身上,似乎已經找不到一絲當年那起綁架案帶給他們的創痛。這是團長一家新的幸福生活。
那天,我突然毫無來由地想起一個人,想問問團長她現在怎樣了,可看到他們一家人其樂融融的樣子,話到嘴邊,又被我硬生生吞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