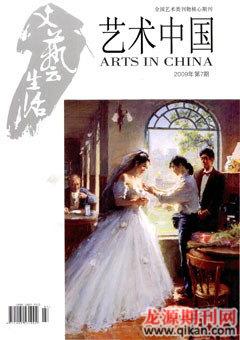“三秋樹”開“二月花”
個 三
人的風景與樹的風景相似,在于春、夏、秋、冬之生理。樹歲依序輪回,周而復始,人歲不可復至,春不二與,然人之思想亦有春、夏、秋、冬之境者,春、夏近于儒,秋近于道,冬近于佛,不依生理次序、輪回,全賴人之情智、思想而縱橫捭闔。在這無與倫比的縱橫捭闔問,思想的“二月花”也許就很自然地出現了。
修到三秋樹
讀鄢福初先生的書法,與鄢福初先生聊書法,總讓我有處春、夏而直達“三秋”的感覺。
“三秋”非關年齡。鄢福初先生說自己為人、為藝有與生俱來的崇尚空靈、簡約的審美理想,做事、說話,干脆利落,一舉中的,力求直達事物的本質與核心。此境界,即穿越春、夏,直達“三秋”之境界。
鄢福初先生“三秋”之樞扭,日戒定、日通達、日擔當是也!
所謂“戒定”,可以從三個側面來認識:一是堅守“個性”認知。鄢福初先生認為世間事物的真善美、假丑惡,都是靠價值觀來判斷的,而價值觀的產生,源于人的思想,不同的思想產生不同的價值觀,然后又產生不同的行為及結果。鄢福初先生書法學習至今經歷了四個階段:1990年以前是學習唐楷的階段;1991年至1997年是學習墓志、碑刻的階段;1997至2002年是學習二王帖學的階段;2002年至今,進入碑、帖互融的創意階段。在每一個學習階段,他能很坦然地面對自己不同的審美追求,因為他知道審美取向取決于自己當時對書法理解的廣度、深度,同時,他也堅信整個過程必然是一個在不斷認知、理解、取舍中得到螺旋式提升的過程,在一個個獨立而不孤立的苦修過程中,堅信藝術個性的形成是“與生俱來”與“后天歷練”的完善統一,從不因瘋狂、流轉的時風而盲目地移易;二是冷靜地面對利益紛爭。在當代書壇各種利益爭端中,莫過于書法市場的利益爭奪,鄢福初先生認為這是書法的審美功能與實用功能能否辯證統一的問題。從純藝術的角度講,他認為書法藝術毫無疑問是以審美功能為終極目標的,但另一方面,書法家是離不開物質力量的誘惑與支撐的,筆墨跟隨時代,當代書法家主動去適應市場經濟,為市場服務本無可厚非,但以書法的實用功能混淆視聽,以致整個書法界出現心理浮躁與急功近利的現象,書法家炒作、推銷自己遠甚于書法創作本身,將本來圣潔的藝術殿堂弄得充滿銅臭氣息。對此,鄢福初先生對這種過頭的現象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拒絕惡意的炒作,并且影響了許多有理想、有作為的書法家。三是超然于“洪流”之上。當代大眾書壇的最熱門、也為大眾書家所津津樂道的“國展”,其所到之處,可謂橫掃千軍如卷席,鮮有不伏者,鄢福初先生則認為:“國展”是一道文化大餐,許多書法愛好者與書法家共同參與角逐,主辦方意圖通過這種形式使傳統文化得到更好的傳承,是很好的,大眾參與者希望通過這個平臺來獲得社會的認同,也是正常的,但現在絕大多數的參與者都是為了一種短期的榮譽,有的甚至將其作為藝術水平高低的唯一評判標準,就與藝術的本質規律相背離了。關于“國展”與“作品”這個話題,我曾向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著名書法家陳振濂教授請教過,得到的回答是:“經典作品不可能在展覽中產生,展覽也沒有產生經典作品的功能。”由此看來,鄢、陳二位所見略同。
所謂“通達”,按湘中俗話說,就是“老”。“鄢老”這稱呼至今在熟悉鄢福初先生的圈子里已叫了近二十年。筆者前年在廣州與中國書協資深評委、著名書法家王楚材先生聊天時,正好帶了一本刊有鄢福初先生書法的刊物,就請他說說意見,王楚材先生略一翻閱,說出干脆利落的三個字——“他通了”。“鄢老”正是這樣一位將人生、藝術揉在一起進行通達認知的智者,這可以從兩個側面來認識:一是他為人、為藝不搞偽學究架子,力求直抵藝術規律的本質。當代中國學術界多怪象,余秋雨先生說自己曾參加一個學術座談會,一學者自始至終多次談到“子先”與“西泰”兩人,而除講演者本人之外,絕少人知曉其所說的兩人究竟為何方神圣。完了,余請教那學者,被得意地告知:徐光啟與利瑪竇也!口稱其理——“古人之名不能直呼”,其實醉心“唯我獨知”之“學術禮遇”。此等說來可笑之人、事,在當今書法界舉目皆是,也極易蒙騙人,并有許多人因此“學問”地占據著書壇的顯要位置。與這類人不同,鄢福初先生的睿智往往是內蘊的,不經意間就在平易、輕松的談吐中出現了,一如他精辟、簡短的文風文詞。當別人還在為搜尋個讓人都不知道的“名字”而苦菌時,他已經在努力思索一種有規律的、定型的思維方式,并且力求讓這種思維方式能夠形成一個嚴密的體系了;當別人在為找到一個他人都不知道“名字”而自我陶醉時,他已經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在對自己進行再否定了。二是他在司空見慣的問題上別有見地的思考。藝術需要創新,人人都知道,鄢福初先生同樣認為一個沒有創新層面思維的藝術家是沒有藝術生命的,并且認為創新是決定一個書家成就高低的關鍵所在。與他人不同的是,鄢福初先生首先主張創新要緊密結合現實生活與實踐,必須要注重生活的積累,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進而他將藝術創新與人生揉合在一起,說:“創新思想的深度和高度,它取決于個人對傳統文化的解析、吸收、取舍的高度,同時也取決于個人對現實生活的理解,及對困境的排憂解難的能力,取決于個人得失觀念的一種正確選擇,人的一生不可能做許多事,要明白自己到底想做什么。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為了自己的事業。肯定會犧牲自己的其他許多利益。包括現實的利益與眼前的利益。”最后,他對創新思維終極實現狀態的認識也是如此清晰:“人的體力是有極限的,能挑多重的擔,能舉多重,能跳多高,能跳多遠,都是有極限的,同樣,腦力也是有極限的,但最后的較量都是在分秒之間,都是微妙的區別,是精細差別,恰好是這一點精細的差別,就決定了一個人的成就,有突破的就成功了,沒有突破的就始終是歷史的重復。”為人、為藝有本質規律,先要認識它,然后要遵循這種本質規律,用鄢福初先生的話說,這樣才能達到人生、藝術的“成熟”之境,亦是筆者所說人生與藝術的“通達”之境。
所謂擔當,就是一個藝術家從內心或行為上積極擔當社會責任,鄢福初先生有怎樣的擔當與思考呢?鄢福初先生除了關心書法人、書法事業的成長與積極組織、參與過多次書法公益活動外,我們不妨到他站在產生時代大家的高度,主張進行的幾個“呼喚”中去找尋答案:
一是呼喚人類道德秩序的回歸。要喚醒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要讓真正閃光的中華傳統文化精髓與道德得到理性的弘揚。書法家加強品格的修養:第一要有胸懷。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第二是要有操守,無論為藝、為人、為官,要保持本色,信奉傳統美德。第三是要和諧,以書會友。兼濟天下,這樣才能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只有人格、人品得到社會認同,才能換得藝術的社會認同。
二是呼喚傳統文化的復興。第一是呼喚與書法密切相關的國學的振興,特別是浩如煙海、光耀千秋的唐詩宋詞。第二是呼喚古代杰出思想家思想光芒的普照。第三是理論體系的延伸與發展。就是
書法藝術本身的理論研究的多樣性,與理論對實踐的指導性,還包括書法藝術理論與其它藝術理論的參與性,或叫滲透性。
三是呼喚傳統文化的開放性與時代性并存。所謂開放性,書法是東方的,同時也是世界的,書法的主要構成元素是點、線、面,它跟美術的點、線、面密切相關,古人說“書畫同源”,就是從這個層面來說的,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以開放的胸襟與懷抱吸收相關的西方文化,書法藝術應吸收、遵循人類審美的共同特性。所謂時代性,就是要認識這個時代里,書法的實用性慢慢消退了,但是它的藝術審美性或審美功能卻凸現出來,這是個過程。嚴格地說,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就是藝術家自我創作意識的展示過程,是一個審美取向的理解、選擇過程,同時也是高雅藝術與大眾藝術的融合過程。
四是呼喚藝術家擔當起自己的責任。藝術家要引領審美潮流,弘揚正氣、正道,要維護傳統國粹的尊嚴,維護藝術創作的神圣,要呼喚時代精英的產生,這樣才能無愧這個時代,無愧于美好藝術的延伸與發展。
自開二月花
思想的高度,決定藝術最終所能達到的高度。歷史上任何一位有成就的藝術家,必然是近道者,或者說是近哲者,而其杰出的藝術成果,必然是這“三秋樹”上開出的“二月花”。
從書法的外在展現形式看,鄢福初至今只走了“三步”:1986年,在硯池里浸泡了近七年的鄢福初先生走出湘中那所山村學校,在湖南省展覽館,舉辦了自己的第一次展覽,這個年僅25歲的小伙子以其功力與靈性兼融的作品,驚動了當時省城的藝術界,得到了周昭怡、顏家龍等湖南書法名家的一致肯定與贊揚;1996年,鄢福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專著——《鄢福初的書法藝術》,再次讓書法界領略到這個年輕人的銳氣與才氣,其聲名再次不翼而飛,從藝術家茶余飯后的風雅談吐中開始向三湘大地的各個領域間不斷擴延;2003年,他作為第二個當代湖南藝術家,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個人書法藝術展,全國政壇、書壇的要員紛紛親臨展館,對展覽表示極大關注,爭相收藏他的作品,中國美術館也收藏了他的力作,他的第二部專著《當代書法家精品集·鄢福初卷》也同時出版。與當代中國書壇此起彼伏、紛繁復雜的運作相比,鄢福初先生這“三步”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恰恰是因為這樣的環境,更凸顯出他的執著、安靜與淡逸,使他區別于那些刻意的喧鬧與叫喊,使他區別于那些書法明星,也更使人關注其書法作品本身的內在魅力,其實,也彰顯出書法作為一門藝術的內在力量。
從鄢福初先生的書法作品本身來看,它深植于傳統而又個性鮮明。極目當今書壇,作品能達此品、此境者,屈指可數。鄢福初先生書法的章法處理往往簡樸,幾乎沒有當代流行的那些花花綠綠的制作;其結字往往空靈,筆斷意連,如同其作人、為文,少筆墨而多空間,給人以想像;其行筆往往靈秀勁健,含蓄沉穩,氣脈貫通,絕不扭捏造作。在其不同時期的各種類型的書作中,有兩樣不變的審美理想始終貫穿其中。一是空靈、簡約,二是文人氣與書卷氣。一個先天,一個后天,兩者都無法復制,何哉?因為那份在含蓄、簡靜與從容問顯露出的正大氣象;因為那份性靈與那些創造是在對傳統進行大量咀嚼后,絕無狂怪、行云流水般地自然生發出來的,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一切都平中見奇,趣味盎然。我敢肯定:當代許多“速成”的書法家在面對鄢福初先生的作品時,一定會感到驕傲或茫然,驕傲是因為“學力才識”的淺薄。茫然是因為“聰明才智”被擱淺。沒有“三秋樹”的底蘊與功力,當然不會明白什么是“二月花”,更不要說享受“二月花”的明麗與燦爛了。著名書法、篆刻家石開先生說這種無法復制的內在東西很能體現一個書法家所達到的高度。
鄢福初先生是一個非專業的書法家,其意志淡淡地指向書法藝術,卻又深深地烙印于書法藝術,他以一個智者的姿態輕松而又專注地游走其間。據說2003年那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展覽時,一位中央美術學院在當代書法創作與理論界有廣泛影響的“巨頭”,獨自靜靜地在鄢福初先生作品前來回品讀了一個多小時。這又讓我想起廣東文史館書畫院院長、著名書法家陳初生先生曾說的“驚四座易,博首肯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