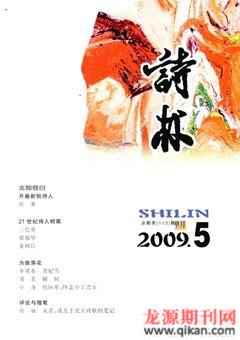我獨處長安,深夜寫詩
燎 原
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詩歌與閱讀之間就日漸明晰地顯現出了一種選擇關系。不同的資質秉賦、人生閱歷、知識結構、生存狀態,都成為一個詩人寫出了這一種詩而不是那一種詩的根據;相應的,也成為身份類同的閱讀者,更易于對這種詩而不是那種詩認同的理由。這就是當今詩壇的“小眾化”寫作現象,也是詩壇大而化之的大一統寫作神話破滅后,詩歌向著自由多元形態的必然回歸。曾經無所不能的詩歌在此表現出了它的有限性,這符合一個詩人是現實生活中常態的人而不是上帝或神甫的基本事實,但詩人之所以又區別于常態的人而是詩人,便在于他以詩歌表達了對于自己生命的敏感。由于這種表達基于自身感受的真實性和直接性,它實際上成為類同生命個體的代言,并在一定程度上抵達了其他人的部分生命事實。
在我原先的感覺中,我大約并不是一個被三色堇的詩歌所選擇的閱讀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的這個名字,讓我輕易地聯想到了網絡詩歌世界,而在這一詩歌世界,我基本上沒有發言權。但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僅僅是,通過兩次詩歌場合中的接觸,我們卻成了熟人。我想這主要緣之于她被小字輩詩人稱作“三姐”或戲稱為“色姐”的通俗性與親和力,或者她身上那種家常氣息與小資情調平分秋色的天然感。這種性格的人無疑讓人感到愉快,于是也就有了我對她詩歌的閱讀契機。
但讀她的詩,再次印證了一種特殊的寫作現象:一個人的日常形象和她的詩作并不完全等同,比如一個笑嘻嘻的爽朗的三色堇,在她的詩歌中卻是一個孤獨乃至頹喪的人,一個哲學意義上的中年危機癥患者。
這樣的癥狀幾乎成了她的詩歌主題。或者說,她是用年齡閱歷和詩歌寫作賦予的雙重感知力,深入到生存腹地斑駁晦暗的陰影區。這樣的陰影,來自陰郁惡劣的季節氣候,來自嘈雜窒悶的空間環境,還來自面具化了的日常生活:“聽命運的鐘擺/在密風斜雨里談論血管里的涼意/這是冬天的西安/倉鼠一樣的天氣漂過秦嶺/生活正在一點點露出劇情的高潮”“我居住的城市嘈雜、憂郁/無所期待/大霧漫過了開花的果園/我站在壞天氣里,沒有方向”“長安城內的青衣不是隱喻/她們的裙裾有著相似的假象/有誰還會喊痛/太多的悲喜劇愈演愈烈”。
事實上,這正是現代都市人基本的生存處境和日常生活。只不過一般的社會公眾已經對此見多不怪,麻木不仁。但這類現代都市綜合癥,并不因此而失去效力,它以強大的潛在毒素釋放,消解著人的生存質量,乃至以生物實驗中慢火煮青蛙的方式,不斷降低生命體的感官預警機制,直至以突然的災變使生命崩潰。在現今都市的不同方位,你難道沒有發現神色各異的狂妄癥、抑郁癥、焦慮癥患者你來他往,而心理咨詢診所遍地開花如雨后春筍?
三色堇直覺性地感受到了波德萊爾式的“巴黎的憂郁”。這種感受當然來自真實的客觀存在,同時還來自她自己人到中年的駁雜心象、一個人到中年的女性詩人對于時間的惶恐,而這種惶恐則從另一個角度,幾乎無法擺脫地控制了她的寫作:“被困在墻外的中年/不敢離水太近……”“多么無力啊,中年的肉體被鋸得血肉模糊/沒人能逃過這堅硬的疼痛”“我慵懶的身體卻難以發芽、抽穗/大把大把的事物就這樣在中年飄去”“現在,我向南而坐/漸漸地辨認自己,在暮年的岸上/看人間蒼茫”。
生命的核心問題其實只有一個,這就是時間問題,哲學的核心問題同樣如此。時間在一個人從無到有的生命中,催發生機、催發活力、催發所有感官的花莖朝著陽光敞開,直至在天天向上的巔峰,使人體會到所謂生命的意義與美好;但同樣還是時間,又在一個人從有到無的生命中,催發病菌、孳生煩惱、消蝕天性、枯萎肌體,直至最終取消生命,指向虛無。而生命在時間中彎曲的分水嶺,正是一個人的中年時期。因此,一個詩人對這一問題盲目而本能的縱深鉆錐,正是通過自身生命的警覺,切入了群體生命的本質。
當三色堇的意識進入到這一層面時,她生命的內在姿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本該簡捷明了的價值標準和行為方式,變得游移、復雜——她在對于生存環境陰影和生命時間陰影的清醒察識和無奈中,以克制與妥協,尋求不逾越底限的恰當應對。比如她在正常天性處處碰壁的現實面前,“學會了用沉默不語/去感知生活”,這顯然是一個人不得不做出的妥協,但即便如此,她卻要堅持表達底限上的自尊:“我不說瑟縮,只說闌珊。”與此相關聯的,是她在高度警覺中,對于真實自我的堅守,“我害怕,我的喉嚨/呼出的是別人的氣息/我擔心,我的內臟/安居著另一個人的秘密”。
三色堇至此呈示了她在生存體認上的兩個環節:其一是對生命和生存腹地陰影的驚悚;其二是在生命之于生存不得做出的妥協中,對于人的自我、自尊不肯退讓的堅守。毫無疑問,這是詩歌賦予她的體認能力和心力。而她又將憑借什么對抗陰影、成全堅守呢?還是詩歌。她用詩歌為自己構建了一個與現實相對應的精神空間,而更具本質力量的活動都在這一空間中進行。
在一些特殊時分,這種活動是激情的、劇烈的:“面對背影中的事物/我試圖粉碎冰涼的思念和卑俗的心/期待更多的日子亮起來/我點著紙燈/在敘述中奔跑,奔跑,奔跑/我有足夠的力氣/將高起來的天空移動得更遠”“我奔跑,靠仰望星辰為生/我無法阻止遠逝的秋意/命里的音符,只能擦亮此生/所剩無幾的蠟燭”。而在通常情境中,這種活動則表現為一個靈魂守夜者隱秘的欣悅與定力:
我獨處長安,深夜寫詩
與孤獨相視而笑
這樣的句式,讓人油然想到了海子“秋天深了,王在寫詩”那種王者造物式的孤獨與自負。而對于三色堇,你當然可以把它解讀為一種小資式的自戀——這是一個在當今屢屢遭受野蠻暴虐的語詞和心靈現象,但一個人連愛自己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還能指望剝奪了這一權利的社會來愛他嗎?
三色堇曾就自己的寫作藝術觀念,做過這樣的表述:“在詩性直覺的無意識中,呈示一種感受狀態。真誠的寫作,干凈的表達。”從她的詩歌技藝來看,她的確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尤其是她在一個小小的斷片式的篇幅中,直取核心的切入方式,和洗練干凈的表達,呈示著一個詩人在詩藝的領悟和磨礪中,水落石出的那種境界。
但我只是三色堇詩歌的不完全的欣賞者。我要說的是,我無緣充分享受她的語詞世界,不能從她的語詞系統中感受到那種機智、詭奇,令人驚奇的語言奇跡。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閱讀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