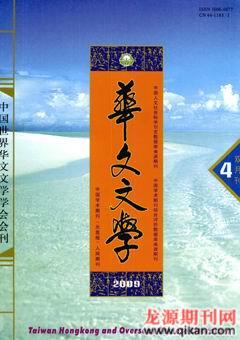棄兒的家庭傳奇
[臺灣]嚴紀華
摘要:張愛玲的寫作曾受到弗洛伊德影響,運用傳統的精神分析方法,從《茉莉香片》中的人物和事件可以發掘出作者的創作心理,而運用拉岡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批評,探討小說人物的欲望的形成、自我主體的建構以及追尋破滅的過程,可以窺見張愛玲如何藉聶傳慶自剖,混同其自身的家庭傳奇,間接重繪一幅陷在時代心獄中的女性畫像。
關鍵詞:《茉莉香片》;張愛玲;精神分析理論
Abstract:As Eileen Chang was once influenced by Sigmund Freuds theory, the classical approach of psychoanalysis can be applied to the discovery of Changs writing intentions for the novel Jasmine Tea. Meanwhile, Jacques Lacans structural psychoanalysis can be used to study the characters formation of desire and the process of their self-construction and destruction, through which to present a portrait of the author herself, as epitomized by the protagonist Nie Chuanqing, suffering from mental imprisonment of her time.
Key words:Jasmine Tea, Eileen Chang, psychoanalysis
中圖分類號:I20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09)4-0022-09
《茉莉香片》1943年7月刊登于《雜志》第11卷第4期,是張愛玲發表的第三篇小說。內容是描述一個年輕人找尋自己真正的父親的故事。20歲的男主角聶傳慶瘦弱、憂郁而帶有陰柔美,與女主角言丹朱的活潑明朗成一對比;小說情節通過男主角憎厭的家、不幸的童年、以及其所發現從未曾愛過父親的母親馮碧落與情人言子夜的絕望的愛,這些如同一把刀一般地絞動著聶傳慶對言子夜的畸形的傾慕。他始終苦惱著——他的父親、他的家、乃至在下意識中認定搶占了他理想的父親的對手言丹朱,于是,內在的壓抑外延到對言丹朱瘋狂施暴,終了卻發現終究逃脫不了既定的一切,如同繡在屏風上的鳥,死也還死在屏風上。于是,故事里的主人翁從一個精神上的殘廢到一個頹廢家庭的犧牲者。夏志清說這是一個動人的故事,而在末尾時讀者又遇到了恐怖。
本文首先分析心理分析理論與張愛玲寫作的接觸與容受;其次由傳統的精神分析批評的角度,試圖通過作品文本聯系作家的主體性(通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來發掘作者的創作心理);最后由拉岡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批評一探小說人物的欲望的形成以及自我主體的建構以及追尋破滅的過程,并由此得窺張愛玲如何藉其(聶傳慶)自剖,混同其自身的家庭傳奇,間接重繪了一幅陷在時代心獄中的女性畫像。
一、張愛玲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
現代文學理論的發展與20世紀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的動亂相關,在社會動亂的同時,也出現著人際關系與人類的存在危機。精神(心理)分析理論就是針對這些人類焦慮、對迫害的恐懼、與自我的分裂所建構的系統性的分析理論,由弗洛伊德19世紀在維也納所開發,從臨床心理學到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都直接間接、或多或少受其影響。成為20世紀影響最大、延續時間最長的的西方文學批評流派之一。而論及張愛玲對于西方精神(心理)分析理論的接觸與容受,自當首從弗洛伊德學說在中國的流行與傳播進行觀察:五四時期,朱光潛、張東蓀、錢智修等分別在《東方雜志》、《民鐸》等刊物上翻譯闡釋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以及現代心理學著論,介紹了夢的現象、潛意識、原欲自我以及變態心理等來解釋人的行為。隨著此一思潮理論的接受與運用,文學藝術作品與評論亦鑒借著夢的解析、發展出弗洛伊德的美學,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實已成為現代派的理論基石。我們想象40年代崛起于上海文壇的張愛玲,她的養成教育中對弗洛伊德應不陌生。
在自己的文章里,張愛玲也屢屢提及弗洛伊德。她在《談看書》中曾引用弗洛伊德與榮(Jung)的通信“凡能正式分析的病例都有一種美,審美學上的美感”。并說明這不是病態美,只有最好的藝術品能比。而對“心理描寫”意識流的難以掌握,她這樣評論:“在過去較天真的時代,只是三底門達爾的表白,此后大都從作者的觀點交代動機或思想背景,有時流為演講或發議論,因為經過整理,成為對外的,說服別人的,已經不是內心的本來面目。‘意識流正針對這種傾向,但是內心生活影沉沉的,是一動念,在腦子里一閃的時候最清楚,要找它的來龍去脈,就連一個短短的思想過程都難。記下來的不是大綱就是已經重新組織過。一連串半角成的思想是最飄忽的東西。跟不上,抓不住,要想模仿喬埃斯的神來之筆,往往套用些心理分析的皮毛。”是由以上言說自可追索弗洛伊德理論對其日常生活及思維行止的有形無形的滲透與影響。
在小說創作上,弗洛伊德思想的烙印更是明顯可見。嚴家炎曾說張愛玲的小說成就首在于其表現都市中的兩性心理的刻劃上具有前所未見的深刻性,并推崇她的出現,使得心理分析小說達到一個小小的高峰。當讀者走入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可以發現除在主題上著意描寫人間情愛的殘缺與畸形,其筆下人物無論是受虐或施虐的角色,無不緊靠其內心活動做赤裸裸的呈現,其透過非理性情欲、變態、歧出的心理描寫來刻畫人性幾乎是全力以赴的。比如《金鎖記》中曹七巧的瘋狂;《沉香屑——第二爐香》里性欲壓抑者蜜秋兒家族的歇斯底里癥;《紅玫瑰與白玫瑰》中佟振保的自戀戀物以及自我建構(“自己的主人”)的挫敗;《封鎖》時電車男女的都市狂想曲;《茉莉香片》的母與子、《心經》的父與女的戀母/戀父情意結;《浮花浪蕊》、《同學少年多不賤》里同性戀情的繪影描圖;《年輕時候》愛畫小人的潘汝良的異想世界;乃至《色戒》里王佳芝的潛意識游走于現實與幻夢、現在與未來;《多少恨》虞家茵內心中天使與惡魔的分裂聲音;《半生緣》中變調的姐妹親情;無一不可視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典型案例,無怪乎毛姆說:精神分析學對小說家具有廣闊的前途。以下本文即選用《茉莉香片》,以精神(心理)分析法治小說,一探“作家主體心靈的自白”。
二、張愛玲與《茉莉香片》
傳統的精神分析學進入文學批評是將作品與作者并同參看:一方面探索創作活動;一方面研究作者心理;其目的是在揭示作者與其作品的關系。根據弗洛伊德在《作家與白日夢》中指出:人類自身有一種能動性與文學創作相類似,而童年時代即是富于想象力的能動性的第一道軌跡。兒童以游戲的心態來創造自己的世界,而作家活動亦如兒童游戲般,依幻想替代游戲,來創造合意的小說世界。其幻想的動力正是尚未滿足的愿望,而每一個幻想都是一個愿望的滿足,都是令人不滿足的現實的補償。由此觀察張愛玲的文學作品正是作家在實現兒童情結的美夢,是經過心理移轉或再造而產生的描述,于是形成一種聲音。比如說棄兒的家庭傳奇。同時作家憑借著自我觀察,將其“自我”分裂成許多“部份自我”(part ego),結果是作家把自己心理生活中相沖突的幾個傾向在小說中幾個主角的身上體現出來,呈現“各有所本”。如此產生著文本性與主體性的互動、對立與消解。
(一)《茉莉香片》與“各有所本”
1971年張愛玲接受水晶的訪問,曾經談到《傳奇》里的各篇人物和故事,大多“各有所本”。張子靜更直言:“我姊姊的小說是她宣泄苦悶的一種方式……她的小說人物俯拾即來,和現實人物只有半步之遙。”根據張愛玲自己先后提及其小說取材與現實人物相關的有《紅玫瑰與白玫瑰》、《連環套》、《殷寶滟送花樓會》、《秧歌》等,張子靜復在《我的姐姐張愛玲》里為《金鎖記》和《花凋》提供了現實背景和人物出處。此外,觀察其小說人物情節境遇如《第一爐香》葛薇龍的香港生活與《半生緣》曼楨的囚禁經驗,乃至新近出版的《小團圓》新秀女作家九莉與有婦之夫漢奸的畸戀都可以看作品情節與作家的個人生命經驗的迭合。其中,《茉莉香片》的情節描述與人物塑型與張愛玲個人乃至家族的生命經歷極為相關;幾疑是張愛玲家庭陰影的記憶。尤其主人翁聶傳慶——此一40年代上海“陰郁少年”的典型,有謂隱射張子靜者;有謂窺見作家張愛玲自身的側影者。綜合而言,張愛玲是把弟弟的外貌特征給了小說人物聶傳慶;而故事中的種種遭遇,牽連著環境的孤獨無助、承受命運的無奈與悲哀以及種種矛盾不安,俱見張愛玲姊弟倆共同生命經驗的文字翻拍。
(二)棄兒的家庭傳奇
根據弗氏弟子阮克(Otto Rank,1884-1939)的研究:幼兒并無法決定自己的出生時地乃至自己的父母,其甫一出生,家庭自為其初始的環境。而父母遂成為其唯一信賴與權威的對象——幼兒想和父母一樣偉大。而自己正是父母唯一的生活中心,于是種下自戀情結的種子。然后成長的過程中,兒童或因為父母的忙碌被疏忽,或發現自己的父母較諸別人的父母平庸……于是,幼兒在認知中產生焦慮、欺騙、背叛的情緒,因此認定自己是棄兒,意圖/假想建立一理想的樂園。乃編織一家庭傳奇,以緩和內心的惶恐不安。小說創作一如兒童做白日夢般,是夢想與現實的溶合體。由于兒童白日夢/幻想自幼深植人心,家庭傳奇幾疑存在于每一個人的潛意識中,超越時間,不斷地浮向意識層面。是以,家庭傳奇可說是一切小說靈感的泉源。許多作家的首部小說大多指向自敘傳或是家庭傳奇的書寫——他們是綜合著兒時自身的幻想(即相信自己編撰的故事),又將自身的經驗與觀察的結果溶入其中。這也就是說,當兒時的家庭經驗在作者內心中埋下了挫折與欲望,在成人后,在寫作時,在有意識與無意識兩個自我雙方的互動下乃營造出一個小說世界(虛構的、夢想的)。以下便分從(1)病態的家、(2)棄兒情結兩個層面,并同參看作家與作品:張愛玲與《茉莉香片》。
1.病態的家
《茉莉香片》里的聶家從外層的描繪上來看,勾勒出的是一個沒落貴族的家;而從里層剝開來看,呈現出的則是一個病態的家。而無論內外,此一描圖俱指向張愛玲姊弟生長的家。如果徑行比對二者的場景氛圍——先看聶家的宅院,那是“一座陰冷灰暗的大洋房外加一個天暖的時候在那里煮鴉片煙的網球場”的組合:
他家是一座大宅。他們初從上海搬來的時候,滿院子的花木,沒兩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陽光曬著,滿眼的荒涼。一個打雜的,在草地上拖翻了一張藤椅子,把一壺滾水澆了上去,殺臭蟲。……屋子里面,黑沉沉的穿堂,只看見那朱漆樓梯的扶手上,一線流光,回環曲折,遠遠的上去了。(頁10)
滿屋子霧騰騰的,是隔壁飄過來的鴉片煙香,他生在這空氣里,長在這空氣里,
可是今天不知道為什么,聞了這氣味就一陣陣的發暈,只想嘔。……客室里有著淡淡的太陽與灰塵。霽紅花瓶里插著雞毛帚子。……
對照張家:
(父親與后母)結了婚不久我們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樣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產業。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們家的太多的回憶,像重重迭迭復印的照片,整個的空氣有點模糊。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而在陰陽交界的邊緣,看得見陽光,聽得見電車的鈴與大減價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著“蘇三不要哭”,在那陽光里只有昏睡。
都是一個彌漫著鴉片的云霧,霧一樣的陽光……在那里坐久了便覺得沉下去,沉下去的一個怪異的世界。
小說中的主人翁聶傳慶是這個病態的家中的病態的人物——一個病崽的陰沉的白癡似的孩子。他有“窄窄的肩膀和細長的脖子,……穿了一件藍綢夾袍……蒙古型的鵝蛋臉,淡眉毛、吊梢眼……很有幾分女性美”。(頁6)這與張子靜的模樣:“成天穿一件不甚干凈的藍布罩衫。……生得極美,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十分相似;而且二者在性格上都一般的軟弱愛哭,就是與習慣被父親打的“這一類事”亦無不同。若論其行事態度上的沉默寡言、懶惰萎靡,則與中學時的張愛玲一樣的是“沉默、懶惰不交朋友、不活動、精神長期的委靡不振”。另外一號病態人物是傳慶的父親聶介臣:形容邋遢躺在床上抽鴉片麻痹自己,與張愛玲記憶中父親打了過度的嗎啡針,離死很近了的模樣……俱是令人厭嫌害怕的。由于出生在這樣一個沒落貴族家庭,深刻體會著腐化的家族、墮落的生活“沉下去”的恐懼與悲哀,乃成為作家揮之不去的夢魘。當她提起筆來,作家個人苦惱的根源:這樣的沒落貴族的病態的家、毫無生氣的生活方式、苛毒的父親,遂結出了一枚苦澀的果實——轉化出難堪人物的不堪情節。而其間人物的性格、心理變態,都由這個家一手造成的。
夏志清曾說:張愛玲對于七情六欲,一開頭就有早熟的興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時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們的動態。《茉莉香片》是她選擇了自己所曾經的這個病態的家連帶著“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弟弟,作為“研究”的“動態”,為作家尋得了出口。
2.棄兒情結
棄兒情結的特色是失去唯我獨尊的往日樂園后,對真實世界認識不足,又無法改變現實,且其自戀情結已深,是以或者逃避現實自我陶醉;或者在自我欲望的掙扎下,意圖改變卻不幸受挫,出現憤恨報復的行為。檢視張愛玲姐弟的童年,從最初的家沒有母親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到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一個形同棄兒的塑像廓出:她的父親是個遺少型人物,嗜毒成癮,對小孩十分嚴苛。四歲時母親與父親不合,出走留學,在她的童年中缺席。而后母也吸鴉片,性情刻薄,虐待前妻留下的小孩。張愛玲曾經這樣自剖:她把世界強行分成兩半:光明與黑暗、善與惡、其中包括母親/姑姑的家里輕柔的空氣與最好的一切的停留以及屬于父親的不好的一面,是一個她所看不起的家。而對前者充滿向往,對后者則是“咬著牙發誓我要報仇”,腦海中滿是靜靜的殺機。像這樣張愛玲成長期間其所存有理想父親的塑造到后來主體建構失敗的恨父心態,乃至于對母親因為現實經濟問題終于也感到絕望的家庭愛的幻滅,還有難以忘懷的被囚禁踢打的經驗以及孤獨情境的所烙下的創傷的童年記憶……等諸多心理歷程,進而比對她的小說《茉莉香片》,自可還原其家庭傳奇的真實脈絡:主人翁聶傳慶同樣有著暴虐的父親與尖酸刻薄的后母,四歲時沒有了母親,主角對自己親生的嚴厲的父親極端憎恨,意圖取而代之;同時他私慕著母親舊戀人、留學歸來的言子夜教授的家。他的行為認知出現著自我分裂——將父母分為好的(馮碧落與言子夜)與壞的(聶介臣與后母);一方面希求著言子夜的女兒言丹朱的愛,一方面卻又憤而對其毆打報復。……小說中呈現著幾乎都是棄兒的聲音:矛盾、偏激、固執、陰疑、乃至整天做著“白日夢”。弗洛伊德曾說:“兒童白日夢中所夢見的事絕非偶然,那么作家的創作亦必事出有因。”由此看來,作家是不滿意現實,企圖營造一精神樂園——在故事里,他們背棄平凡父母、否定現實,他們自我憐惜、熱烈求愛,同時又充滿自戀自卑。作家除了強化想象的極度,并運用著人物重現、虛構人物與真實人物相同,虛構情節穿插于真實事件之中以將心靈的破碎殘跡加以整合。就在《茉莉香片》中,我們可以看見張愛玲將自身的家庭傳奇發揮得淋漓盡致:小說人物尋找父親/愛的主題一如其自身的童年生活的“逃離——尋找——破滅”的父輩關系建構過程,其以小說人物聶傳慶取代自我,作家的書寫往返于作品文本與作者主體之間,過去的回憶與當下的虛構兩種似真如幻的人生交手,正是作家/主角兒時失樂園后的叛逆感的移轉與再造。
(三)陷在心獄里的鏡像/畫像
《茉莉香片》中,張愛玲是以聶傳慶的觀點——透過他的回憶以及種種心靈意識的活動進行敘述。由于人物是其強調的重點,篇中書寫著正是各人生命中的恐懼與憐憫。耿德華說:他們都有著不正常的心理,……他們對時間、環境、常規的抗拒,正宣泄了所有人共同的欲望。而這群有著不正常心理的男男女女,包括內心深懷恐懼而外表殘暴父親,虛榮心支撐下的善女人言丹朱,陰損調唆的后母心態,以及臨水自照的水仙——聶傳慶的自我疏離的特質。以下本文即通過拉岡的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批評,聚焦于聶傳慶與他的父母們一探小說人物的欲望的形成以及自我建構的過程。
1.欲望的形成
欲望是拉岡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問題,亦是其對弗洛伊德本能論的修正和發展。根據他的觀察:兒童初期發展莫不出于自然需要(need即生物性需求),當兒童開始使用語言來表達其滿足性的渴求以及被認識為一個需要的主體時,需要則轉變為需求,欲望亦由是誕生。由于此一欲望是來源于分裂與匱乏,其中即以兒童與其統一體——母親分離以及與其影像分離的創傷過程為一由分離體驗到匱乏的范例。且由于在兒童主體與父、母主體的關系中,嬰兒與母親處于直接的情感關系使兒童誤認為他自己的欲望對象也就是母親的欲望對象,甚至把自己看成就是母親的欲望對象。因之,欲望總是指向一個被壓抑的原始本文:從母親那里獲得完整性,或與母親結合。
由此,我們要了解聶傳慶從原始欲望(成為母親的一切)到想知道(區分)、想占有的欲望的過程,當首從《茉莉香片》中聶傳慶與馮碧落的母子關系檢視起:聶傳慶對母親所知極少,多是由二手數據中拼湊母親的圖像(比如相片、雜志上的簽名以及劉媽的辯白)。而母親在孩童四歲時的永遠消失造成主人翁欲望對象的二次匱乏(第一次是嬰兒自身與母體分離),這樣的匱乏在小說中替換以男主角對母親神秘的認同以及強烈的依戀:比如“聶傳慶守在窗子跟前……說不出來的昏暗的哀愁,那守在窗子前面的人,先是他自己,一剎那間,他看清楚了,那是他母親”。聶傳慶只有從僅存的母親婚前唯一的照片上,在攝影機的鏡子里,隱隱地瞥見了他的母親,擁抱著母親的幻像,如夢一般,在痛苦中,“他不知道那究竟是他母親還是他自己”(頁14)。對于母親,聶傳慶了解:是從沒有愛過自己的父親的。然后等到他發現母親曾經愛過別人——曾有嫁給言子夜的可能性的時候,聶傳慶自然產生了“如果”的幻想——如果母親采取斷然的行動;如果他的母親顧到未來,替未來的子女設想過;如果自己是言子夜、馮碧落的孩子,一個有愛情的家庭里面的孩子,將是積極、自信、勇敢的……。(頁19)然而母親畢竟是不在了。在此,主人翁自我等同于母親,母親的欲望遂轉化成聶傳慶自身的欲望,于是從前的女人輾轉、輾轉、輾轉放在心上的一點點小事——“那絕望的愛的等待”正是他母親心里的一把刀,如今“又在他(聶傳慶)心里絞動了。”(頁14)由于這幼兒與母親的雙重合一與全然共生,由于這原始的匱乏無可挽回的消失遂造成了欲望的永恒性,且不斷地由一個需求能指轉向另一個需求能指。于是,我們得知:《茉莉香片》中聶傳慶是一方面迷戀著母親,一方面又不得不恨著他的母親;前者將母親凝固成一張照片,僅能從美學的距離與之親近,后者與母親一齊化入圖像,成為死在屏風上的鳥;前者畢竟是做了清醒的犧牲,后者則是一點選擇權利也沒有。還有小說中聶傳慶何以對穿著中國長袍流露出一種特殊蕭條的美的言子夜的畸形的傾慕與對妨礙他欲望實現的言丹朱的憎惡是同樣的與日俱增。同時我們更理解到:身為一個女性作家的張愛玲,并不標榜母愛。其筆下的聶傳慶只有借著對母親的欲望對象的認同進行著對母親的認同,乃屬于一種想象的占有。而這些欲望卻被虛幻影像所迷困,在現實中注定難以實現,其被積累壓抑的結果,惟存痛苦。于是悲劇乃成必然。
2.自我建構的過程
拉岡說:主體性和欲望是社會的產物,而非自然或發展的結果。而主體性的發展歷程系起始于鏡像階段(6-18個月),終止于伊底帕斯情結(3-6歲之間)。在“鏡像階段”,兒童受快樂原則支配,不尊重性別差異,無法將自己的身體視為完整的客體,為無政府狀態,是具虐待狂且是亂倫的。這亦是嬰兒對自己的一個想象的認識的過程(亦即自我誤認的時刻),此一想象界是屬于前語言的、前伊底帕斯期的領域。大約就在鏡像階段結束后,嬰兒開始掌握語言中“我”的主體位置,進入象征界,而其入口便是“父親的名字/父親的隱喻”。此一時期幼兒透過意識到自我與他者,本體和外界的區別,而逐漸獲得“主體性”。此即所謂“伊底帕斯情結期”。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母—嬰雙邊結構(二元關系):
在這段期間,嬰兒處于早期發展期中主客不分的存有狀態(“想象態”),兒童認同著母親的欲望。其與母親的身體處于共生關系,互為補充但也有撕裂的幻想。
(2)父、母、兒童三邊結構:
當父親介入母子的二元關系,是以阻撓者的身分出現,兒童開始接觸到“父親的法規”,伊底帕斯情結進入第二階段。其以母親為中介,進而對兒童的欲望產生抑制作用。而說服男孩放棄對母親亂倫欲望的是父親閹割的威脅,此時期兒童適應現實原則,向父親屈服,疏離母親。同時將此欲望壓抑到無意識的場域。
(3)認同父親與父親死亡階段
這一階段是伊迪帕斯情結正式衰退時期。兒童習得了父親的法規,承認父親的象征地位,接受只有父親/雄性才具有陽具,才是母親欲望對象這一事實,從此父親不再是他競爭的對手,而是兒童學習、模仿的對象。兒童由此“二次同化”獲得主體性,克服伊迪帕斯情結,得以從社會的自然狀態進入到文化的象征秩序。此時,其掌握了父親的名字,這也就是一個宣布父親“死亡”的過程。如果失敗,男孩可能在性方面無法充當雄性角色扮演,造成性沮喪,或視母親形象高于其他女人,導致同性戀。
關于聶傳慶的主體建構的過程,我們即借由拉岡的自我建構理論切入。唐文標曾說聶傳慶這個角色的生成應來自舊家庭的束縛使他掙脫不開,轉成憂郁,有極大的不安全感。這些壓抑的因子包括著聶傳慶父母失和、母親的早逝、父親的暴行易怒,已如上述。而根據精神分析,兒子與父親關系往往具有對抗性,因之,兒子反叛父親遂成為最原始的文學主題之一。而在《茉莉香片》中聶傳慶無論是來自法律/名義上的真實父親或是精神中理想的父親一致的嚴厲的對待所造成無情的挫敗感,在其心靈留下陰影,使他無法自立成長,——正如小說中所言“已經給制造成了一個精神上的殘廢”,遑論我父之名。
不僅于精神上的殘廢,在形體上,小說中的陽性角色聶傳慶的描形是一再出現“女性他”的特質,這種“去勢書寫”,張愛玲或從形體殘障、或從精神殘障兩個部分著手。前者多為身體生理上的殘缺。后者則屬內在精神層面閹割其傳統宗法父權中認定的陽性權威。在《茉莉香片》中,聶氏父子俱是頹廢異化一族。例如遺少型人物聶介臣,是一個沉迷于鴉片煙、狂嫖濫賭、不務正業的父親,其昏庸猥瑣.陰鷙殘酷。色厲內荏正是一種外強中干、虛張聲勢所拼貼的變形去勢。由于他的得不到妻子的愛與移轉的恨的矛盾交織,所以刻毒待子;另一方面位居父權中心的他身懷宗法恐懼:敗家絕后的焦慮、子孫不肖棄養的疑懼,故而實施高壓威權統治,家庭封建保守、刻板教條化,是一個無關愛、無生氣的環境。而聶傳慶角色外表形象的女性化設計,伴隨著陰性氣質(如害羞囁嚅、愛哭),再加上孩童化的行止動作。導致一再被視為女人(包括自父親后母、理想的父親言子夜以及陽光少女言丹朱),卻不是一個有擔當的成年人。當然他對這樣的認定是極端痛恨與害怕的:他總是咬牙切齒恨道:“你拿我當一個女孩子,你——你——你簡直不拿我當人!”是以如此“雌雄同體”的寫照,不但暗中顛覆了傳慶的陽性自我。而其孩童化的特征,復直指其水仙子特質(自卑自憐、自戀)。進而明白指陳聶傳慶主體建構為“人”的失敗。另外鮑昌寶、吳丹鳳則指出:張愛玲以女性作家的身分書寫而以男性角色聶傳慶的視點去描述、感覺外在世界,而此一男性主人翁,本身恰恰又出現相當女性化的刻劃,于是父權體制中的男性尊嚴即在一再的性別變裝中被消解。
聶傳慶始終是處于一種原初的自戀階段:包括他把臉貼在玻璃窗上摩擦著(頁8),伏在大理石桌面上(頁10)的自惜自愛,還有由于傳慶的耳朵給父親打壞了,有點耳聾,使他聽不到想聽的東西。這點出了他的自憐心態,而他也不喜歡自己的聲音。更加強了其主體的失落感。(頁7)而吸吮藤箱壓出手臂上的紅痕這個動作亦暗示著其意圖藉此行動重溫置身母親懷抱吸吮母親乳汁的幻想。以上種種俱指向幼兒的一直無法忘懷與母親水乳交融的互相隸屬感,聶傳慶沉溺于這種認同母親的欲望,甚至有著成為母親欲望的欲望,折射的結果即是自戀的欲望,而在這里,自戀十足亦是一種自我防御。也有著自夸與自鄙的成分。
另一方面,小說中的主角是陷入不斷編織將(自我)客體病態的理想化的種種幻想/幻象。比如他整天伏在藤箱上做著白日夢,額上滿是嶙嶙的凸凹的痕跡(頁20)。值得注意的是聶傳慶的幻像中復擬造著多層次的自我分裂:包括將父母分為好的(馮碧落與言子夜這一組)與壞的(聶介臣與后母這一組)形成對照,還有自身形體的分裂的痛苦:如聶傳慶自身是父親的形體和母親的心腸的組合,以及強烈的偏執感所造成了行動的分裂。于是如同母親同樣等著愛的男主角在自我疏離的終點受辱羞憤絕望崩潰,出現了雄性反擊(暴力攻擊),這在心理學上并不意外。因為許多不被認同的案例顯示,這實際上正是該人物透過攻擊其理想的(化身)而懲罰自己的一種手段。末了終究是跑不了,他還得在學校里見到她,一如自己逃不了父親,一如母親逃不了父親,……事實上與其說聶傳慶逃不了言丹朱,不如說他逃不了自己欲望的囚籠。
在人物的勾連上,《茉莉香片》中明顯出現對父母輩中同性的憎惡以及異性的愛戀(“伊底帕斯情結”)。前者比如聶傳慶之于自己的殘暴的父親的厭恨——甚至痛恨自己與之的形體相似性與血緣性。后者比如聶傳慶之于自己的母親乃至假想等同母親之于母親情人/理想的父親的傾慕。當父親介入母子二元關系中,父親隱喻性地對兒童的欲望說“不”,兒童接觸了父親或是父親的法規。小說中則是以“在父親作廢的支票上簽上自己的名,意圖掌控金錢,奪取奇異的勝利”(頁12)被視為弒父過程的操演——其意圖取代宗法的父親,成為母親婚姻中的欲望對象。另如聶介臣亦曾嗤笑自己的兒子“就會糟蹋東西,連個男朋友都沒有,也配交女朋友。又一再強調這個白癡似的孩子讓他難為情,并且警告他再不學好,就用不著往下念了。免得替聶家丟人。”(頁20)我們在這樣的父子關系的對待中看不見愉快的相處經驗,導致聶傳慶對欠缺父愛的渴慕與企羨,于是理想的父親身影一再被幻想制造出來——他迷戀于自己出世之前的過去,拒絕/逃避面對現實,并進行制造一幻想世界,幻想著母親的情人言教授有可能成為他的父親,相對于對聶介臣這三個字的不被看得起,言子夜這個名字卻是理想父親的化身,在其眼中尊貴無比;但矛盾的是他又是下意識中的情敵,不許自己跨越雷池一步。在《達文西與他童年的一段記憶》中曾有這樣一段話:“沒有一個在童年時欲求他母親的人,會不想將自己放在他父親的位置。會不在想象中與他的父親認同,而且后來將超越他視為自己一生的任務。”由于聶傳慶面對父母、同學及一切現實的人都感到自卑、渺小。整日自怨自艾。因之,聶傳慶從未能在父子沖突中學得教訓,尋得/接納替代父親來撫平他的巨大的心理創痛。當權威無情的父系語言如出一轍——言教授課堂上的喝斥怒罵,進一步把他推回他所不愿意面對的現實——一個客觀上他無能為力的現實,一個主觀中自卑自怨自憐自戀的囚牢/世界。如是聶傳慶對陽物父親再度的認同挫敗,轉為內化了的“超我”道德譴責,而呈現出一種“道德自虐”的沖動。另外,聶傳慶潛意識中化成為母親這一世化身的復仇魅影(同樣等著愛的這對母子),在企求滿足的欲望受到箝制以及對任何阻擾欲望的事物憎惡的情況下,故事中的主角出現反常行動,對他人展開攻擊。這是自戀行為的變體,這是以反撲羞辱作為自衛。綜合而言,當他不能接受父親的法規,那么兒童就會認同母親的匱乏,屈從于母親的欲望之下,他仍將停留在伊底帕斯情結的第一階段之上。這意味著聶傳慶再次建構主體宣告失敗。
三、結語
縱觀《茉莉香片》,主角聶傳慶原希望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以及自己在學校課堂上優越的表現,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受肯定贊譽的有為的青年,這代表著聶傳慶的人格理想,是他要達到的人生目標,因此也是他的鏡像。但是他的家庭不完整、理想的實踐屢屢受挫,于是相對地,其理想與自我的距離和虛幻關系就暴露了出來。同時它映襯出自我的另一面,即缺失和匱乏的前鏡像狀態,并引起焦慮和仇恨的負面體驗。于是一種極度分裂的人格涌現出來(比如原來的怯懦柔順竟變得暴力兇殘/狠),這使他嫉妒外表亮麗成功,擁有他所認定的理想父親言子夜的言丹朱,并幻想她們將要迫害他,因而反過來攻擊他的理想的化身——一個代表他的自我理想的演員。因之發生半夜在山上毆打言丹朱的行為。這樣的發展極其戲劇化,說明了聶傳慶主體的追求建構乃至破滅,與其理想母親、父親角色的空缺密切相關。是以本文從心理分析法治小說,初意不再尋求充滿感人效果的陳述命運、性格與欲望之間的沖突,或離析其間的責任歸屬問題,而是聚焦于構成沖突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是流竄于古老心靈與荒唐現實之間的“鄭重而輕微的騷動,認真而未有明目的斗爭”。這騷動與斗爭----在能指鏈中,癥狀是隱喻,指向恨父;而欲望即換喻,指向戀母。其是將最初的性沖動指向母親,最初的仇恨指向父親。不過是滿足了所有人童年的愿望。
再從作品形構的語言觀察,可以發現張氏組織家庭傳奇的書寫策略是:一方面強化想象的極度,一方面運用著人物重現(或以本身的戀母或戀父情結著眼)、虛構人物與真實人物相同、虛構情節穿插于真實事件之中等途徑,此仍是應合著參差對照的手法,將心靈的破碎殘跡加以整合。例如在《茉莉香片》中,母親就是一面鏡子,聶傳慶有著等同母親的欲望,幻想著自己與母親迭影重合,又希冀著成為母親的欲望的欲望,前者連系出對母親情人言子夜畸形的傾慕,后者折射即成為自戀的欲望。此外,張氏是以一種殘缺家庭塑造殘缺男體,并進一步突顯男性邊緣化/去中心的書寫反撲。同時她并無意為一個大時代所束縛、為傳統所拘牽的凄楚女子立傳,寫其哀慘節烈的事跡以供仿效,而是藉由一個畸形的下一代受害者乃至于變態的施虐者的自剖式的視角進行書寫,是間接表露,完成了時代女性浮出地表的危機與自覺。此一作家虛實相間的創作一如兒童以游戲的心態來創造自己的世界,如此作家是將匱乏的愿望編織成幻想,將人與事依其喜歡的原則重新安排,又將文化因素及個人經驗溶入以進行布局敘事。其中多隱含有情欲的沖突以及有關自己的身世故事。于是,家庭傳奇形成,文學作品與心理分析由是展開不解之緣。無怪乎柳雨生說以短篇小說多重結構論之,《年輕的時候》、《茉莉香片》最好。
最后就讀者的接受而言:張愛玲的書寫的傳奇,篇章之充具虐性,其中的恐怖與扭曲,正是基于讀者不平衡需求而設計,根據心理分析研究,讀者的精神的紓解常可經由肉體的折磨而達成,此處經由文本的虐性扭曲,造成了讀者們被虐后的快感,個人的焦慮在比較之后獲得了紓解,個人認知的美感于是乃得開發。是其文本中對時間、環境、常規的抗拒,正宣泄了所有人共同的欲望。故而倘若以讀者的心理和反思來解讀和印證之,張愛玲的失愛的無童年正是人生之始。而其作品主題細節里;有愛與無愛的對峙,小愛與大愛的召喚,文學價值的尊卑貴賤與藝術生命的短暫與永恒一切都臣服于“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然而,如此一來,主角、作者乃至讀者的人生的困境果而真是無法逃脫?新的選項是否有可能產生?倘若從(新精神分析理論的主張)理與欲是互相成立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角度來看,如果壓抑與放縱不必然成為此消彼漲的對立項,那么,壓抑走到盡頭是否將有可能包含扶正與顛倒,如此,在文本中的秩序的崩潰與野蠻的勝利,在現實生活中或許可能是在秩序的欲化當中產生了更徹底、更真實的文明與秩序?這些都將成為耐人思考的課題。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頁,第413頁,第418頁,第413頁,第400頁。
例如:1914年,《東方雜志》10卷11號錢智修《夢之研究》,18卷14號朱光潛《福魯得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民鐸》2卷5號,張東蓀《論精神分析》;《心理》1卷12號余天休《分析心理學》等。
[美]斯佩克特:《弗洛伊德的美學——藝術研究中的精神分析法》,高建平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4頁。
“讀過穆時英小說的人,大概都會感到張愛玲……的寫法很有穆時英的味道。”嚴家炎:《張愛玲和新感覺派小說》,《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3期。
[英]毛姆:《論小說寫作》,《玫瑰樹》,于曉丹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頁。
宋家宏:《主體心靈的自白 人倫關系的審視》,《玉溪師專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6期。
張愛玲:《茉莉香片》,《第一爐香》,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6-29頁,第16頁,第6-12頁,第6頁,第20頁,第27頁,第24-26頁,第20頁,第436-507頁,第23頁,第17頁。
[奧]弗洛伊德《作家與白日夢》,《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長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430頁,第9頁,第20頁。
所謂“各有所本”,包括張愛玲的自述、所見、所聞與她親屬所講的話,還應有另種含義,即是包括張愛玲本人的經歷,她將自己的故事也融入到她的小說中去。參見馮祖貽《百年家族——張愛玲》,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82頁。
張子靜、季季:《我的姊姊張愛玲》,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頁。
張愛玲:《小團圓》,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28頁。
唐文標:《張愛玲研究》,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版,第32-33頁,第24頁,第24頁。
任茹文、王艷:《沉香屑里的舊事——張愛玲傳》,團結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頁。
阮克(Otto Rank,1884-1939):《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傳奇》,轉引自逄塵瑩《從心理分析論小說創作》,《中外文學》22卷第2期。
張愛玲:《童言無忌》,《流言》,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63頁,第15-16頁,第162-165頁,第20頁。
汪宏聲:《記張愛玲》,《回望張愛玲?昨夜月色》,金宏達編,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
耿德華:《抗戰時期的張愛玲小說》,《張愛玲的世界》,王宏志譯,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79頁。
李焯雄:《臨水自照的水仙》,《張愛玲的世界》,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03-127頁。
王國芳,郭本禹:《拉岡》(Lacan),生智文化事業有公司1997年版,第186-189頁。
胡錦媛:《母親,妳在何方?——被虐狂、女性主體與閱讀》,《閱讀張愛玲》,揚澤編,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35頁。
林信謙:《張愛玲論述——女性主體與去勢模擬書寫》,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195-197頁。聶傳慶未能成功克服伊底帕斯情結,雄性建構失敗,遂出現女性化、愛哭、懦弱、陰沉、白癡……一樣的形象,此為“去勢書寫”。
鮑昌寶、吳丹鳳:《性別的建構與解構》,《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5期。
唐文標主編:《“傳奇”集評茶會記》,《張愛玲資料大全集》,時報出版公司1984年版。
楊昌年:《百年僅見一星明(2)——析評張愛玲〈金鎖記〉的藝術》,《書評》第四卷十二期,《百年僅見一星明(8)——評析張愛玲的<茉莉香片>》,《書評》第四卷四十六期。
耿德華:《抗戰時期的張愛玲小說》,《張愛玲的世界》,王宏志譯,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