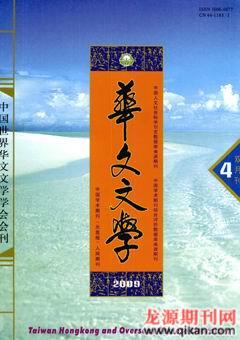美麗的張世界
[香港]黃維樑
一、曉風以劇為文
讀張曉風的作品,看她的生平自述,就知道她多情善感,想像豐富。讀小學時,她因背誦一空軍烈士就義前所寫的“頭上是祖國美麗的春天,腳下是祖國美麗的大地”而哭泣。她喜歡寫作,13歲那年“幻想要成為大作家”。她不斷寫作、投稿、參加征文比賽,散文、小說、戲劇都來;香港的獎項,臺灣的“中山文藝獎”、“青年學藝獎”,一個又一個的散文獎堆疊起張曉風這位20多歲的散文家。到了1971年,她30歲的時候,金光閃閃的“金鼎獎”頒給她的劇作《第五墻》。13歲的夢幻變為現實,她成為大作家了。說她30歲時已是大作家,保守之士會有異議——其實唐代的李賀和英國的濟慈(John Keats),都在26歲時繳出了彩筆,前者升到天上的白玉樓,后者與冥間的荷馬暢論詩歌。30歲如果太年輕,那么到40歲、50歲,在她更多的散文、小說、詩、戲劇作品發表、獲獎,暢銷或長銷,且好評如潮如風之時,文壇和學術界都不能不承認張曉風是大作家了。
眼前這本選集,作品選自張曉風的十三本散文集、一本小說集、一本美學論述、兩本雜文集、一本報道、一本宗教著述、一本兒童作品集。光看文類之眾和作品數量之多,我們就可知道她的筆有多健旺,她的筆有多少姿采。
《文心雕龍?情采》說:“圣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作家之為作家,必須有情有采;大作家自然應該更為多情或深情,自然應該更為多文采了。張曉風正是這樣。她以多產、多文類縱橫于文壇,如果要把她定于一尊,則她的“本尊”是散文家。散文可說理、抒情、寫景、敘事,張曉風對這些樣樣皆能。她最擅發揮敘事性的能量,把散文寫成一個接一個的戲劇場面;她還為散文增光添采,把散文寫成一段接一段的詩章。散文《母親的羽衣》一開頭是這樣的戲劇:
講完了牛郎織女的故事,細看兒子已垂睫睡去,女兒卻猶自瞪著壞壞的眼睛。忽然,她一把抱緊我的脖子把我勒得發疼:“媽媽,你說,你是不是仙女變的?”我一時愣住了,只胡亂應道:“你說呢?”
場面溫馨如晚上黃金時段闔家歡的電視劇集。《驚》一文的開端則如午夜的驚悚電影:“有一次去看畫展,一進門,冷不防地被一整墻的張大千的大幅墨荷嚇了一跳……”這里戲劇的各種元素諸如時間、地點、角色、動作、說白幾乎都一一具備。連一些散文集的書名,也這樣具有戲劇性:《步下紅毯之后》中,不是有“紅毯”為布景、有“步下”為動作,有“之后”暗示時間,而其中有人物呼之欲出嗎?《星星都已經到齊了》這個書名,則“星星”是角色,“已經”隱含著時間,“到齊”是行動。張曉風以劇為文,奉行亞里斯多德的行動(action)律。至于《常常,我想起那座山》一文,記敘她單獨“朝山”的行動,只有主角一人,而獨白之外,還有與途人的對白,且多的是動作。此文第二節《山跟山都拉起手來了》是一個例子:
“拉拉是泰雅爾話嗎?”我問胡,那個泰雅爾司機。
“是的。”
“拉拉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他抓了一陣頭,忽然又高興地說:“哦,大概是因為這里也是山,那里也是山,山跟山都拉起手來了,所以就叫拉拉山啦!”
張曉風所朝的山名為拉拉;在臺灣的泰雅爾族語言里,拉拉是美麗的意思。名字美麗,“山跟山都拉起手來了”的動作更美麗。散文家張曉風通過寫景、寫動作、寫對白這些具體手法來抒情、說理,正是中西文學論者所說的“寓景于情”、“用形象來表現思維”、“以象來表意”(艾略特的“意之象”objective correlative寫法)的創作技巧,也就是余光中在張氏《你還沒有愛過》序言中說的具有臨場感(sense of immediacy)。張曉風把一段一段直接或間接的生活經驗記在腦海中,寫在稿紙上,讓讀者閱讀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觀戲劇,對其描述的世界可觸可感。這位常常感動于天地萬物的作家,表現了豐富的感性。
二、曉風以詩為文
她的另一種感性呈現于其詩化語言。詩化語言的最大特征是用比喻。從亞里斯多德、《毛詩序》作者、雪萊、劉勰到錢鍾書,一切的詩論文論無不視比喻為修辭的關鍵,為文采的象征,為作者才華的標志。
摹山范水時,我們總用比喻,也因此我們有龜山、象鼻山、飛鵝山等等。張曉風把一座山比喻為一方紙鎮:“美的凝重,并且深情地壓住這張紙,使我們可以在這張紙上寫屬于我們的歷史。”在《常常,我想起一座山》這名篇中, 這座拉拉山有歷史有文化,“山是千繞百折的王旋璣圖,水是逆流而讀或順流而讀都美麗的回文詩。”張曉風禮贊這座山,論者如余光中、方忠都禮贊張曉風“山人合一”的這個比喻:
山從四面疊過來,一重一重地,簡直是綠色的花瓣——不是單瓣的那一種,而是重瓣的那一種——人行水中,忽然就有了花蕊的感覺,那種柔和的,生長著的花蕊,你感到自己的尊嚴和芬芳,你竟覺得自己就是張橫渠所說的可以“為天地立心”的那個人。
在這個奇麗的“山人合一”中,人顯現無比的尊嚴。張曉風以詩為文,形容至大的山,也形容至小的精子。她的《人體中的繁星和蒼穹》一文,題目已用了比喻;里面寫精子,則說牠們是生命的戰士,只顧奮力泅泳……“抱著億一成功的希望”而全力以赴。作者在解說生命科學,客串為文筆最生動的“科普”作家。
偶爾科普一下,張曉風寫得最多的仍然是人生。從冰心到琦君到大中小學生的作文,母愛是恒久普遍的主題。關于母愛,張曉風發明新的寫法,她創造了一個奇特的比喻——把母親形容為自甘困鎖在家里的仙女。一個女子結了婚,且生育了兒女,自此成為母親,任勞任怨。有福丈夫兒女享,有苦自己嘗。張曉風寫道:母親總是把紅燒肉和新炒的蔬菜放在父親面前,她自己面前永遠是一盤雜拼的剩菜和一碗“擦鍋飯”。但她不以敘述鋪陳家事為滿足。她說母親一直“把自己牢鎖在這個家里”,而她那象征年輕、美麗、飄逸、自由的仙女的羽衣則鎖在箱子里。母親有鑰匙,知道怎樣打開箱子——
她知道,只要羽衣一著身,她就會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軟白亮的羽毛拍了又拍,仍然無聲無息地關上箱子,藏好鑰匙。是她自己鎖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她不能飛了,因為她不忍飛去。
三、曉風新月,愛滿天地
張曉風這個名字,容易使人聯想到柳永《雨霖鈴》的“曉風殘月”,進一步把她與婉約陰柔的風格等同起來。但張氏的“曉風”,卻是與新月在一起的,是曉風新月,甚至是清風明月,甚至是和風麗日。她觀察明月下麗日下的人間世事,且經常參與其間, 時時使“我在”現場(《我在》是她一本散文集的書名);她多情善感,作品的題材極其多元。母愛和山水之愛,只是她作品內容的小部分。她還寫對丈夫、兒女、學生、朋友、花鳥蟲魚、語言文字、歷史文化以至國家民族之愛。因為愛荷花,一天,她心血來潮,一下課就從她任教的大學乘計程車直奔荷花池。某年暑假她獨自去了一趟日本, 以前曾到富士山, 知道山中有些湖區,這次下了飛機便直奔美之所在, 雇計程車載她繞湖一周。 又有一次,她偶見永和橋邊有駕訓班, 覺得那里落日極其美麗,便忍不住參加了。
上世紀80年代,她在香港的一間學院擔任客座教席,當時香港面臨九七問題,她身處其間,與港人同憂戚,且愛上這個城市。“1984年2月合約期滿,要離開的那段日子,才忽然發現自己愛這座老城有多深。”她用什么方法來回報這個“擁抱過的城市”呢?她決定捐血。捐血時,她“瞪著眼看血慢慢地流入血袋,多好看的殷紅色,比火更紅,比太陽更紅,比酒更紅,原來人體竟是這么美麗的流域啊!”(引自《從你美麗的流域》)張曉風認為捐血對她來說是一種收獲,“感覺自己是一條流量豐沛的大河”,這正是《圣經》所說的“施比受更為有福”。她愛香港,更愛臺灣。臺灣最近數十年來也有危機,有困境,臺灣也有移民潮。張曉風選擇留下來,她愛這塊土地、人民及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