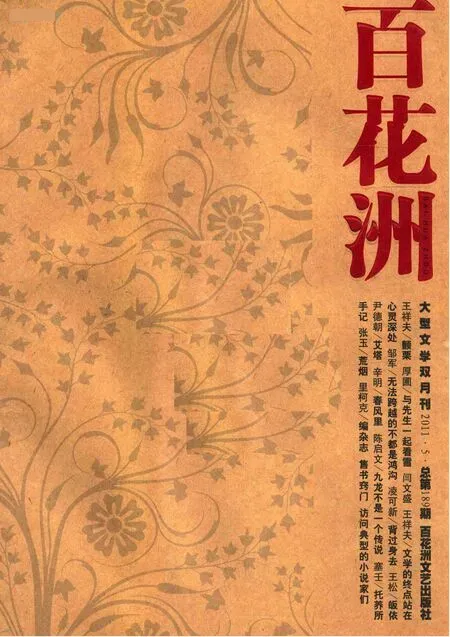第十一年
魯 敏
本刊推薦
小說以小甜兒的視角不動聲色地講述了生活中的溫暖與仁愛,它遠離了世間的黑暗,沿著人情美、人性美的道路狂奔,含蓄、典雅、溫情脈脈,時刻令人感受到人性的溫度。而作家溫柔敦厚的情懷,構筑了小說底片上的暖色調。濃重的人間煙火氣匯入到詩情畫意中,是那么熨帖,成了撫慰小甜兒成長的一服良劑。
1
沒有人跟小甜兒說清楚,要去的到底是什么“遠房親戚”,大人們只含糊地提到“彭家”,他們在倉促地確定每月的伙食費,商量路上的交通與行李,根本不在意她四處探詢的眼光。
是啊,哪里顧得上這個,出大事情了,在銀行的父親,從一個挺高的位置上栽了,除了經濟之事,還扯出來一個外面的年輕女人;隨后,做貿易的姑父也被連根拔起來,接著是大伯伯家的兒子,當初正是父親安排他進的信貸科……家里現在完全沒了秩序,大伯母天天坐在客廳,以各種手法鬧自殺;爺爺在絕食;媽媽請來律師談離婚與財產分割——所有的人物、東西與關系都正蒙受大難,小孩子得趕緊送得遠遠的,這種時候,還要追問細節,是可恥的。
故而,直到在東壩住下一個多月,小甜兒才慢慢搞清楚,這彭家,其實根本連“遠房親戚”也談不上,只是因為東壩這小鎮夠遠夠偏,又正好曾與家里有過一段很小但較好的瓜葛。就這么的,小甜兒被送來寄住到彭家了。
第一次踏上東壩的大地,看著屋頂上斜斜的煙,路面散落的草屑,以及迎面而來的黃狗與不認識的人們,剛滿十一歲的小甜兒不由自主地掙了掙身子:她想使自己看起來更大一點。
彭家有五口人:兒子總在縣里做活,逢上節才回。一個比小甜兒大兩歲的孫子,老不長個兒,綽號叫做地陀螺。實際上,主要就是三個女人:彭大娘老皺如核桃,兒媳婦萎黃似腌瓜,只有做姑娘的,膚白,細眉毛長眼,單字一個青,小甜兒喊她作青小姨。
喊人的時候,小甜兒會配以笑容;所有吃與用的東西,不挑,有什么便是什么;早上再不賴床;還有,哪怕只有她和地陀螺兩個人在桌上,也決不第一個伸筷子——類似的許多小講究,不用教,小甜兒一到彭家,就全懂了;或者說,稍早一點,從家里亂起來的那一刻開始,所有的好惡就都一齊舍了,變成個什么都隨便、都可以的孩子。
彭家人從來不問小甜兒家里的事,當然,這是很好的體貼,可有時想想,也挺別扭挺委屈的,她們明明知道,為什么偏不問一問!就這樣遲鈍地、平淡地,她們把小甜兒納入日常,不特別供著,也不簡慢。青小姨買油球回來,一人一個。彭大娘燒玉米棒子,一個掰作兩半。反正不論什么,都與地陀螺一樣。
可世上怎么可能有真的一模一樣呢。
比如,她們從不對她兇。但對地陀螺就會,挾菜的姿勢,臉上拖鼻涕,衣服勾了洞,她們就講,有時還打。小甜兒在一邊看著——心中一陣空落,一個沒人兇、沒人罵的孩子,真沒意思、真不像個孩子啊。
還有,她們不支派她活兒,只使喚地陀螺。曬鞋子!收痰盂!擺碗筷!偏是不喊她,哪怕她倚著門框子在望呆。只有地陀螺,他氣哼哼地嚷嚷:那她呢!她做什么!于是她便順勢去跟地陀螺一起做。女人們也不攔,但下次仍是不直接支派。
這地陀螺,正是最看不起女孩的年紀,總愛弄出一股冷淡勁兒,可是,又喜歡做主人的派頭,看到小甜兒這里那里都不懂,便要給她講規矩,帶點夸張的語氣,好像都是些了不得的傳統與禁忌。
2
家里的事,在這樣的東壩,自然是看不見、聽不到了,好像是遠了。可小甜兒清楚,不可能遠的,而是變成了頂看不見的帽子,一直壓在她的頭頂上。別人跟她說話、別人看她;或者,反過來,別人不跟她說話、不看她——她都認為:這是因為自己頭頂上的帽子。
小甜兒其實很想找個機會,跟誰好好地說一說,說出來了,就好把這頂帽子給徹底拿下來。可是,不容易呢,她在這里,很少有說話的機會與對象,有時一整天下來,她數數,不過才講了七八句。
是啊,彭大娘是愛說話的,但她大多是跟畜生說。撒雞食時與雞說,掃豬圈時與豬說;睡覺時,跟腳被窩頭的貓說——她的口音很重,小甜兒幾乎聽不懂。
那媳婦兒年紀雖不大,卻灰撲撲的,跟田地的顏色十分接近,她的分工主要在田里,晨起踏露,晚歸披月,吃過晚飯還要在燈下用功,揀種子、拌料肥,或是縫補——絕沒有閑空跟小甜兒說話。就算下雨天,眾人一同坐在家里,她也一邊搓繩一邊用她黃黃的眼珠怔怔地盯著窗外,沉入她那空洞的沉默。
相比較而言,甜兒跟青小姨稍微親近些,因她們每晚都在同一個屋里、腳對腳睡同一張床上。但這親近,仍是十分的有限——
青小姨可正在好年紀上,渾身上下有股說不清楚的姑娘氣和神秘勁兒,她白天在鎮上地毯廠上班,晚上回來洗洗弄弄,渾身搽得香噴噴的,然后便坐在床側專注地照鏡子,表情帶著某種迷幻,又有些超凡脫俗般的,照那么一會兒,就睡下,并不跟小甜兒多話。甜兒不免惴惴,她想,青小姨一定不喜歡有人呆在她的房間,并且還要把床分出一半……
甜兒于是一躺下就不再動了,盡量縮小自己,不輕易翻身,也不去想小便、咳嗽或是哪里癢。這樣一直拘束著,很久才能睡去。
夢里,她總是在一條長長的路上獨自走,四周一片白茫茫的濃霧,好不容易碰上一個什么人,剛準備好好說上一大段話兒,一開口,卻醒了。
黑暗中,聽到屋頂上有家鼠一陣陣歡快地爬過。睡不著,小甜兒便回想一些以前的生活片斷,那些花花綠綠的細節,一家人在新街口的館子里吃西餐,母親讓她把胳膊收緊,父親教她用英語點菜。她發現自己忘了好些單詞,竭力地想,慢慢重新睡去了。
3
時間與環境,這是一對多么好的元素——到第二個月,小甜兒已大致習慣了彭家這種慢吞吞的、沒有驚喜也沒有驚險、甚至也沒有多少對話的日子,永遠是這樣,大片大片沒有盡頭的靜默中,彭大娘在家里做事,媳婦在地里做事,青小姨在地毯廠做事,地陀螺在外面滾鐵環兒。
所以呢,也可以理解,當有人上門給青小姨提親時,甜兒何以會那么的驚喜。可不就是平地起高樓嘛!小甜兒一直盼著這樣的事情呢,這樣,她就再顧不上想頭上的那頂帽子了不是嗎。
小甜兒集中起全部的注意力,暗中盯著媒人,想象著某個陌生的男人將要迎娶青小姨,這很有傳奇色彩不是嗎!她甚至以一種嶄新的目光重新打量青小姨,對她非常的佩服,瞧啊,她那么不聲不響的,可是,有人將要喜歡她!
彭家人都忙起來,甚至用上了小甜兒,讓她到河對面老萬家去換百葉與豆腐。彭大娘稱了一斤半黃豆,讓小甜兒千萬別撒了。
怎么會撒呢。小甜兒胳膊繃得緊緊的,一心一意地往老萬家走,她喜歡自己突然被彭家需要起來。
路上要經過一小片河坡,彭家媳婦舍不得任一小塊地白空著,就是這狹窄的小河坡,也被她種上了幾排向日葵,剛剛長出臉盤子的向日葵正像粉嘟嘟的嬰兒拳頭一樣,整齊地朝著小甜兒打過來,小甜兒同樣對它們揮揮拳頭。啦啦啦,她差點要跑起來。可是,一斤半黃豆可不能撒嘍,她仍舊硬胳膊硬腿地往前走。
萬家只老兩口,都是彎腰駝背,不過駝得很有道理:就著磨臺,正好推磨、正好壓漿;就著灶臺,正好刀豆腐、正好剝百葉。老萬家的豆腐,東壩第一——要是不駝,那哪兒成。
萬家老人認識小甜兒,但也不跟她多話,直到小甜兒提了東西要走,老頭兒突然喊住她,遞給她一張熱乎乎的豆腐皮卷,剛蘸的醬油還在往下滴呢。
小甜兒便接過,站住,一口一口吃。萬家兩個老人仍在忙他們的。可小甜兒覺得,她與他們,已經建立了某種社交關系一般的。
這天的飯菜,小甜兒覺得很不錯:百葉炒韭菜,豆腐燒蝦米,有她的一份功勞。她和地陀螺,一人一碗肉湯泡飯,沒上正經的八仙桌與客人一起,就在廚房里。吃著吃著,地陀螺突然撇著嘴,用一種打破什么的得意口吻告訴小甜兒:哼,你覺得今天有人來提親——很稀奇是吧。其實,在你來之前就定下的,我們全家都知道。那個人,連我都見過,就是崔木匠唄,個子很矮的。
甜兒正挖起一大勺油飯送到嘴里,突然發現,味道沒剛才那樣噴噴香了……是啊,她只是偶然在此落腳而已,這里,她是進入不了的,就像彭家人也不能進入她——每個人都戴著自己的帽子。
而地陀螺也推開碗,帶點怨恨地嘆口氣……姑姑最疼我了,經常喊我替她捂腳。然后,你來了。再下面,是崔木匠,唉,姑姑以后再沒空喜歡我了。
4
崔木匠果真個子矮小,其貌不揚,可他很懂事。每次上門,一身的木頭味,兩手的吃與喝,給彭大娘送油馓子和治骨頭痛的秘方藥水,若逢上彭家的兒子回家,必定另外提著肉、酒,“跟大哥喝兩盅兒”。此外,他幫嫂子擔水、做地里的活兒,還給地陀螺帶各式各樣的香煙紙殼——后者不太領情,故意看都不看,直到等他走了,才拿出來一張張玩。
崔木匠這樣,不知為什么,反倒讓小甜兒有些可憐他。這感覺,甚至從崔木匠的初次登門就開始了——大約因為崔木匠實在沒什么特別之處,彭家女人們略有些擺架子,尤其是青小姨,過分莊重了,顯得冷淡,崔木匠因此十分拘謹,說得最多的就是:哦。哦。好的。好的。介紹到小甜兒時,大約是曾聽聞過背后的來龍去脈,他眼里飛快地閃過一點什么,然后伸出木頭般干燥的手拉拉她,有點巴結地:哦,哦……
就是打這一刻起,小甜兒忽然感到:這個崔木匠,比自己還不如呢,她要對他好!這想法讓小甜兒十分歡喜。
故而,那天中午,當地陀螺惡作劇地往他的飯里悄悄撒了一撮鹽……小甜兒當即以一種從來沒有過的、完全不像是寄居者的姿態,很自然地倒了一大碗開水送過去。她不瞧地陀螺,也不瞧崔木匠,她確切地感到自己的強大,崔木匠的保護人一般。
臨走前告別眾人,趁沒人注意,崔木匠突然對小甜兒悄聲說:下次,我帶我的家伙箱子過來給你玩兒。
崔木匠的家伙箱子外表很丑,一半是封住的,另一半則支支棱棱地戳著各種木柄,完全不成樣子,崔木匠卻用一種溫柔而寶貝的手勢,一一取出來,靈巧地展示給小甜兒看:喏,這是刨子。這是手搖鉆。這是鑿子。這是魚頭鋸。這是角尺。這是木銼。這是刻刀。
他一樣樣講解其用途,一邊往彭家四處看看,變得驕傲了起來,指著堂屋里的長條案、八仙桌,圓杌子與高背椅,甚至穿過墻壁指著看不到的雕花架子床、梳妝臺與五斗柜,這些,我全會做,我的活兒,你不知道有多好!
他翻倒一個木凳子,從邋里邋遢的墨斗里搖出長長的黑線,勾住一只凳子腳,然后拉得無限長,瞇起一只眼,“叮”地在空中一彈,非常了不起似的。他甚至把小甜兒的手指放到鋸子那閃著微光的刃口處,輕輕地來回地銼,讓她感覺一種奇異的疼痛……他盯著小甜兒,眼里閃著突如其來、近乎野蠻的喜悅。
小甜兒發現自己挺中意這套難看的木匠家伙,更中意這個時候的崔木匠。但這崔木匠啊,不爭氣,只在她面前才是如此這般,一到彭家女人面前,尤其是青小姨面前,便是如此那般了。
可能也是青小姨的原因,對于崔木匠,她的態度,怎么說呢,熱絡肯定是談不上的,反是拽著繃著,有點拿勁兒。彭大娘認為這就對了。媳婦卻有不同的觀感:不對,咱家小姑肯定沒感覺。
感覺。媳婦兒冷不丁地竟用了這個詞。彭大娘一聽笑起來:感覺!長的還是方的?
小甜兒也不特別清楚那“感覺”到底是什么,可她知道,崔木匠與青小姨間,的確缺了些什么。她于是全力以赴地動腦筋,走在路上踢石子想,躺在床上聽老鼠爬想——一個人,可以有樣事不關己的事情想想,并且由此去幫了比自己不如的人,多么好啊。
小甜兒最終認定,崔木匠的家伙箱子,是能夠帶來“感覺”的好東西。等著崔木匠再次上門,她便裝著初見且好奇的樣子,抱著家伙箱子把崔木匠往青小姨所在的方位帶,暗示崔木匠再展示一遍那些工具。
院子里,青小姨正坐著梳頭呢,頭發散下來,遮住了半邊臉,有陌生而特別的嫵媚。
崔木匠卻僵硬得很,同樣是往外拿家伙,卻出奇的自卑了,講解的聲音也細,非常的不漂亮。青小姨淡淡掃了兩眼,明顯沒有興趣。小甜兒急了,東指西指,說了一長串家具,挑戰般地向崔木匠發問:會做這個嗎?會做那個嗎?
不等崔木匠回答,青小姨倒走過來,用梳子往小甜兒頭上輕輕敲了一記:你不信啊?不信趕明兒人家做一樣給你瞧瞧。
崔木匠一聽,受到啟發一般,動作定格了,他羞怯而感激地沖青小姨走過的虛空處笑了一下。
這天晚上,青小姨一邊照鏡子,突然說起話來:小丫頭,你好像蠻喜歡那些木器家伙!
甜兒心中一動,啊,青小姨終于跟自己聊上啦,這不是正好可以探聽到青小姨的“感覺”么,面上卻仍裝著粗枝大葉:是啊,挺好玩的,你不喜歡?
好玩——是好玩,但——青小姨沉吟著,表情滯重了,不愿再談下去。她另起個頭。噯,你們在上面,一般晚上都做些什么?
當地人都喜歡把城里客氣地叫做“上面”或“外面”,然后,相應地,把自己的東壩,稱作“下面”。他們會這樣說:某人前幾天到上面去了一趟。又或者,這個比不得外面,咱們下面,只能是如何如何。
看得出,青小姨對于“上面”是有很大的興趣,但她較為克制,從小甜兒“下來”東壩,她還是頭一次談起。
小甜兒頭腦飛快地轉,為了使談話更為豐富,使青小姨滿意,她調動所有的聽聞與見識,使勁說:嗯,有人逛街,有人在茶館說話,在飯館喝酒,在網吧打游戲,在包間唱歌,在健身房打球,有人開著車子四處跑,有人趕最后一班地鐵,還有,小孩子在上奧數課鋼琴課,下課了跟媽媽到必勝客吃匹薩……小甜兒邊說邊想,恨不得把“上面”夜晚所有的事情都概括全了。
青小姨卻猝然打斷,甚至像是帶著某種怨恨:算了,不要說了。所以啊,你才會喜歡那些木器家伙!
難得一次的談話就這么中斷了。這個晚上的下半段,比之以往,甚至更加寂寞。
大約是由于談了一些“上面”的事吧,在入睡前的那一小段時間里,小甜兒竟然想到了媽媽的化妝品,那些色澤鮮艷、散發芬芳的小瓶小罐,構成了一個極其龐大復雜的隊伍,排著隊在她面前轉圈;還有媽媽的圍巾,小甜兒曾經數過,從冬到夏,總共三十一條,它們拖著長長的陰影纏成一團……這讓小甜兒涌起很久不至的難過,然后又瞧不起地在內心責罵自己:又沒出息了吧!他們離不離婚、他們是否惦記自己,想了做什么!就這樣在彭家呆著不挺好嘛!
崔木匠果然真開始打東西。彭大娘、媳婦兒一人一個沉沉的樟木箱;地陀螺是個很神氣的彈弓;小甜兒則是四方方的一個小木盒兒,用來放零碎——小甜兒在彭家沒有零碎,她的零碎全在“上面”的家里呢:動物紐扣、巧克力紙、心形別針。可她中意這個小木盒兒,就是空著也好哇,這可是她在彭家添的第一樣東西,屬于自個兒的。
這么幾下子一來,崔木匠在彭家的地位上來了,彭大娘與媳婦已完全把他看做是自己人了,說話的語氣都帶上了親熱勁兒,崔木匠的生澀于是慢慢散了,做事吃飯都不用再招呼——噯,奇怪吧,這倒讓小甜兒失落起來,雖然她是一心希望崔木匠好的。這挺難解釋的。
5
這天,不知哪里來的興致,青小姨忽然決定,要帶地陀螺和小甜兒到她的廠里玩。
正是東壩的春天,最為濃烈的四月,一切的作物都瘋癲般地日長夜長、繁華似錦,就連道路當中,若有一小塊狹長的空兒未曾被人畜踩到,就會被野草們歡暢地占有,更不要說路邊與河坡,橋邊與柵欄,一切皆不成規矩,以植物們自由自在的發芽、抽莖、開花為至高無上的天理。
青小姨一言不發地領著他們,完全無視四周沸騰的萬物,竟似是心事重重。地陀螺呢,也只顧變著花樣玩他的鐵環兒……哎呀,這么好、這么好的風光啊,他們為什么完全沒有感覺?
“感覺”,這個詞從腦中一閃,小甜兒想起了什么,青小姨的悶悶不樂,也許正是與那個有關的。
不多遠也就到了地毯廠,織機前面坐的全是跟青小姨差不多大的年輕姑娘,加之織機上五顏六色、互相映襯的絲線,整個空間都有種黏稠的脂粉氣,偶爾走過幾個男人,竟是特別的引人注目。
尤其是其中的一個年輕男人,穿著身休閑裝,舉止上略有點與眾不同的做派,小甜兒一眼看出:這人是從“上面”下來的,她能捕捉出一股城里味兒。他走到哪里,都有姑娘要喊住他,喊到跟前,就著圖紙問:這里到底是兩股靛青色還是兩股藏青色?噯,這半邊圖紙說要織二十行,可另半邊,怎么又成了三十行……問題的確是問題,但也算不上要緊問題,可她們全都迫切地喊住他,執著地追問。
年輕男人脾氣很好,一路上走走停停,對任何人都十分親切,他半低下身,把頭微微地那么側過去,一直側到姑娘們的鬢發處,半普通話半東壩話、半是嚴謹半是稀松地一一解答,特別的誨人不倦,如送春風——可能也是帶點表演性的,他知道自己是百花當中的一點綠,索性就綠得感人一點、漂亮一點。
有姑娘往小甜兒手里塞了幾簇彩絲線,可她顧不上玩,只留意用余光觀察那個年輕男人,因他現在走到了青小姨處,青小姨倒是沒有喊他,但他主動停下來,不知在說些什么,青小姨往小甜兒和地陀螺這里指了指,他沖這里點點頭,但并不過來,仍然站在原處,與青小姨交談。
他與青小姨說話時的眼神,語氣,以及站姿——全都是有內容的。某些事情,看到中間就等于看到了前面,甚至也看到了后面。
小甜兒用手慢慢地捋順手中的絲線,可她的心,卻跟這線相反,很是起伏,甚至可以說是沉痛的、不平的、準備去操心的——
唉,崔木匠啊,哪里真正取得什么地位,他還是可憐的!需要幫助的!
重新走上回家的路,青小姨倒稍微活泛了一些,就手扯了幾根長長的柳條,給他們一人編了一頂柳葉帽,一邊有口無心地問:今天見了那么多人,最喜歡誰呀?
地陀螺馬上說:馬春花,她比姑姑還好看,我喜歡她。
青小姨把頭轉向小甜兒。小甜兒依稀有些明白,青小姨為什么要帶他們到廠里了。
哦,我……我沒仔細看,我光顧上看毯子了。小甜兒撒了個謊,她不愿意指出那個引人注目的年輕人。
青小姨卻看出什么似的,不信地一笑:你呀,不說我也知道。好吧,既是看了毯子,要是讓你倆花錢買,挑哪塊?
地陀螺側著頭想了半天,卻吐出一口口水:花里胡哨的,你們女人才喜歡,我一幅也挑不中呢。買回來有什么鬼用。
小甜兒這次也講了老實話:我也一塊不買——看你們織得那么細致那么好看,買回去給鋪在地上踩在腳下,多糟蹋呀!不行,我舍不得買。
青小姨氣得笑起來:唉,真是小孩子。你不知道,我天天在那兒織著毯子,就總想,自己要能變作個毯子多好,被釘到墻上也好,被鋪在地上也好,只要能離了這“下面”到了“外面”,就總是好的……你呀,白心疼個什么!……
小甜兒認真地聽了——她幾乎是欣然地想:她這下是真的有事情煩了。聽聽!青小姨的心思!她可要替崔木匠好好琢磨琢磨。
6
春季的播種結束之后,崔木匠就要到外面做工了,他與其他幾個瓦工、漆工搭成了一個班子,到省城去了,替“上面”的人裝修,運氣好的話還能接到很大的公家活。總之,他將要有很長的時間不會再往彭家跑了。
走之前,崔木匠連趕著好幾個日夜,給彭家做了個大活兒:睡柜。
這種睡柜,小甜兒從未見過,當是東壩特有,它比一般的床要高得多,下部做成大肚的柜子,可供裝糧食,上面的蓋子設計成合縫的暗把手,鋪上被褥,便可以當床來睡人。因是介于柜與床之間,有些四不像,睡柜往往顯得笨重粗糙,可崔木匠做的這睡柜,比正常的規格要稍矮一些、再稍瘦一些,四腳及兩頭都雕了花,崔木匠還親手給它上了桐油,里外都收拾得油光可鑒,很講究,讓人見了,忍不住要伸出手去撫摸兩下。
“這個可真好,再蛀不了蟲打不了眼兒!還不走潮氣!”彭大娘滿心歡喜,思量著要把新玉米啊、新米啊、面粉啊一起裝進去。
可這睡柜,這么秀氣,放哪兒都不對呀,看來看去,只有青小姨房里最合適——擺放停當,大家都沖青小姨笑。青小姨卻沖小甜兒一努嘴:我們房里兩個人哪,早該著有兩張床了。
話雖這樣說,每天晚上,小甜兒都等著,卻一直沒有人讓她睡上去,那睡柜就一直那樣嶄新著,害得小甜兒進進出出的,都要多看它幾眼——其實,她也并不是真的有多想睡,只是心里有種晃悠悠的惦記罷了。
崔木匠走的前一天,彭家兒子從縣里回來了,“哥兩個喝幾杯”到很晚,沒留神外面倒下起雨來。兩個人都喝得手腳熱乎乎、脖子紅通通的,再讓崔木匠走到黑地里走到冷雨里就不好了。兒子媳婦自作主張要留他住下,“又不是沒地方!”“那睡柜不是正好空著!”“還沒人睡過呢!”“你馬上都要上去了,以后都難得來!”彭大娘有些不樂意,照老規矩,沒結婚的男女,是不好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可說不出呀,那柜子還是人家給添的呢。
這么的,簡直就是水到渠成的,崔木匠也就住下了,住在他親手打的新睡柜上。
小甜兒大松了一口氣,沒錯,這睡柜,該著就是崔木匠睡才對。她這下徹底安心了。
她是安心了,可旁人未必就安心——三個人的呼吸,說起來,比之兩個人的呼吸,不就只多了一個么。可是,這個夜晚,大不一樣!到底哪里異樣,小甜兒也說不好。只一條,她知道,這一夜,可不光她一個人在聽屋頂上的老鼠在快活地爬來爬去。
最有意思的是下半夜,或是天色將明未明之際,甜兒約摸還在做夢,可她分明就聽見崔木匠起身了,他半蹲半站地倚在青小姨的床頭,對青小姨細碎地說話,燕子般呢喃不休,溫柔、迫切;隔一會兒,又不說了,什么聲音都沒有,屋子里安靜得像滿滿一大缸清水——讓小甜兒懷疑他是否已經睡去,可她睜不了眼也動不了身,只知道崔木匠那身淡淡的木頭味兒,就在床腳呢,很美很仔細地停在那兒,讓人非常感動似的。
甜兒在夢里欣慰地一笑,就又接著睡了,她甚至夢到了爸爸媽媽年輕時候的樣子,他們竟都不認識小甜兒,只他們兩個人,可要好了,親親熱熱走在一處,頭挨在一起,甜絲絲的,多好啊,小甜兒在后面拼命地追著他們、喊著他們,可他們就是毫不理會……等她在無聲的叫喊中重新醒來,發現崔木匠已經出去幫媳婦忙活了,結結實實的腳步在院子敲打地面。
一貫早起的青小姨沒有起,兩只腳一動不動側臥著并在一處——今天,她到地毯廠上班恐怕要遲到了。
7
現在,到彭家換豆腐換百葉,成了甜兒專屬的差使。每一趟去,她都正好可以看看斜坡上的那片向日葵,它們小小的粉臉兒正一點點大起來,從拳頭大到巴掌大,隨風搖擺著,齊刷刷地、天真地盯著她一路走過……每回,萬家老頭兒也都給她蘸了醬油的豆腐皮吃——其實甜兒不是很愛吃,只是覺得應該接過來吃下去。
萬家兩口總看著她吃,他們盯著自己的樣子讓甜兒覺得這老兩口也像是兩株老向日葵。她喜歡他們的眼神,渾濁,沒有內容。
老向日葵家算是個小小的交際場所,在那里,甜兒能碰得到許多鄰里及他們的狗或貓,次數多了,偶爾也開始搭些話兒。他們喊她一聲名字,然后想半天,避開某些最想問的問題,只挑一些無礙的。“幾歲啦?”“聽得懂東壩話?”“怕不怕狗?”
隔上一段時間,再說話,差不多還是這幾樣,最多把狗換成貓……唉,其實,就算他們真的問到甜兒家里那些事,甜兒也不會當真生氣或難為情的,她只是怕自己說不清楚而已。
家那邊,現在可以說是杳無音信,只每兩個月寄一次錢,有時捎些衣物過來。甜兒甚至想,他們不會真的忘了自己吧——每收到一次衣物,她卻更為不踏實,當天夜里的鼠聲,聽上去分外地響,呼啦啦,呼沙沙,如貼耳邊。
但她不討厭那些老鼠,反之,它們倒能算是另一個世界的朋友,它們最清楚她在半夜醒來的那種難過與孤獨,它們是在陪伴她,呼應她……直到“喵嗚”一聲,彭家的老貓進來。
這老貓本來最喜歡睡彭大娘的床,但這里的老鼠動靜太大了,青小姨便把那貓抓來,可她自己不喜歡貓,這樣,她便讓小甜兒先睡,自己要在外間坐一坐——有時,這很像是個借口,她想在外面待一會兒。
然后,他們一家人便都在外面,聚在堂屋的燈下,一邊剁山芋藤,或是剝棉花果,一邊用土話親熱地聊,越講越快,有時還笑,有時爭執,有時相互罵幾句,她們自是無意的,可小甜兒卻感到一種徹底的被拋棄感。她靜靜地躺在里面的房間里,腳頭臥著那只老貓,被窩一角壓得熱乎乎的,頂上的老鼠很識相地,躲在某個角落一聲不吭……小甜兒眼窩里忽然就濕了,她想念老鼠們快速爬過的聲音!除了這個,她還有什么!
啊對了,當然,還有崔木匠給她的小木盒,可是,某種程度上,她又怨恨那個小木盒——它一直空空的,小甜兒沒有東西可以放進去!在彭家,一切都是對她開放的,可是一切又跟她全無關系:堂屋、灶臺、青小姨的房間、崔木匠的睡柜、媳婦兒的樟木箱子、彭大娘的豬圈與羊圈……看看吧,隨便走到什么地方,哪里有她一個小角落?她怎么好收藏什么東西?包括這個木盒子本身,也就隨隨便便地擱在堂屋條桌的下面第二個抽屜里,在它的邊上,放著別的雜物:兩包撲克牌,一套舊茶具,以及一些別的。小木盒算個什么!
小甜兒用被角掖掖眼窩,她突然發現自己這個動作很像彭大娘,這一想,小甜兒倒又要發笑了。她抽抽鼻子,知道自己其實在惦記什么,唉,那個誰,那個比自己還不如的崔木匠呢,什么時候才會回來?
崔木匠人雖不回來,可他托人捎過好幾次東西給青小姨——粉色絲巾,鍍金手鏈,半跟皮鞋。這些禮物,青小姨從來不用,只在晚上,她才拿出來,在房里一樣一樣試,舉著小鏡子前后左右地照。她的神情很是奇怪,并非是多么甜蜜,反之,是嚴肅的。
小甜兒默不作聲地看,真希望青小姨跟她說點什么。可是不,青小姨故意一般地,自顧對著鏡子試了、瞧了、再收起,打個平淡的哈欠,然后貼上枕頭,就睡了。
這有點奇怪不是嗎?
最奇怪的是,青小姨有天忽然摸出一本書來,端坐在床頭,一本正經地看。
小甜兒要看書名,青小姨一躲,幾乎是驕傲地笑:就不許我學習啦?萬一我將來也要到你們“上面”去呢!
可書畢竟是書,看久了很容易走神的。青小姨一走神,就要走到“上面”去,帶著點憧憬,又裝著若無其事,東一榔頭西一棒地向小甜兒打聽:你們“上面”的姑娘,最時興弄什么發式?你們在外面閑聊時一般說些什么?如果我好好弄一弄,不開口說話,那么我看上去,幾乎像個“上面”的人吧?
——這些問題讓小甜兒深感憂慮,包括青小姨這時的表情,有點像個蕩秋千的人,一下子把自己甩得很高了,風聲呼呼的,她就以為自己真的在空中飛了。小甜兒一下子想到了地毯廠那個穿休閑服的年輕男人……不好的,事情這樣是不好的。可是,誰又能阻止一個人去蕩秋千呢,誰不喜歡那種飛翔的滋味啊,誰不希望自己這輩子可以飛一次啊。
看著青小姨手中雪白的書頁,小甜兒此際忽然深深愛上了青小姨,愛她的夢想以及這夢想的脆弱性。是的,她仍然還是崔木匠的保護人,可她也想做青小姨的祝福者——雖然她是個連自己的命運都不知道往哪里飄的“小倒霉蛋”、“小可憐蟲”。是啊,倒霉蛋,可憐蟲,她聽人這樣說過她。可是,也不見得完全是吧!
8
天熱了,小甜兒想起她曾經有過的那些裙子,一條沒有帶下來,當初一定沒有人想到,她會在東壩一直呆到夏天吧,也好,只要看不到裙子,她就可以完全忘掉以前的那些夏天,媽媽替她抹上防曬霜去玩水上樂園,她們在電影院一邊吃冰淇淋一邊抱怨冷氣太足……所有還不曾忘掉的,統統趕緊忘掉吧,她不再是一個孩子了不是嗎,應當像大人那樣硬邦邦的不是嗎。
還是接著去關注青小姨好了,用別人的大事情,取代自己的小事情……瞧瞧,夏天里的青小姨,她多甜美啊,看她只穿薄襯衫的樣子,只穿小衣服的樣子,側臥與趴下的樣子……還有她沉甸甸的頭發,她額角的一點汗,以及那亮滑滑的皮膚。不過,越是仔細看,小甜兒倒越是有些不放心了——青小姨中午要在地毯廠午睡呢,她這瓷器般的好模樣,倒給旁人看了去,而崔木匠,還一眼都沒看過呢。
青小姨卻把中午那一覺看得比什么都重似的,今天夾一床涼席去,明天帶把折扇去,甚至把風油精與小毛巾都一齊帶走了。為了個中午的午休,連晚上的正經覺都睡得不安分了,夜里很遲,小甜兒都能聽到她在腳頭眨眼睛,是的,青小姨的眨眼睛是可以聽到的,她似在苦苦地想著什么,想午睡的事情?
甜兒于是也同樣苦苦琢磨起地毯廠中午時分的情形:所有的姑娘都可以休息還是青小姨有特別的待遇,她有單獨的休息處還是幾個人共用……也許,她不應該那么好奇的,但她是個守護者不是嗎——得替崔工匠看著,也替青小姨她本人看著。
這中間,最熱的幾天,崔木匠倒也是回來過一小趟。
外面小半年的生活,他變得更瘦小了,衣服顯得拖沓空蕩,看了有些不大入眼,但他卻帶著一種小滿足似的,跟同樣回來歇夏的大哥喝酒時,一一排出他前段時間做過的活兒,其實無非是柜子,閣樓,床與書桌,旁人聽來未免顯得重復而枯燥,他卻毫不自知,記不得處偏還要花很長的時間去竭力回憶……直聽得大家都要瞌睡了。好不容易講完一長段,喝下一大口酒,突又喜不自禁地宣布,他有個重要的好消息,本以為是什么呢,他嬉笑了半天,獻寶一樣地說出來,嗨,卻還是木匠活——歇過這個周末,他接下來要出省做活!他們的“隊伍”找到一個度假村的大活,恐怕一直要干到臘月呢。
“噯,到時可就攢上一小筆錢了!”他用淺醉者紅紅的臉朝青小姨笑了一下,又掃了大哥嫂子一眼,帶著誠懇的羨慕,大膽地吐露心聲:“我其實,沒別的,就想像哥哥嫂子一樣,一個外一個內,這樣熱乎乎地過日子。”
不知為何,這句發自衷腸的話卻讓青小姨的臉色暗了下來,她順著崔木匠的眼,也從大哥大嫂的身上掃過,尤其掃過后者那長年操勞的黃褐色面龐與干枯的身體,眼里竟是閃過一種近乎絕望的神情。她很快站起來,隨意支吾了個借口便回房間去了。沉湎于對平淡生活無限向往的崔木匠,卻抬起他微腫的雙眼幸福地目送心上人。
——坐于桌子一角的小甜兒則看著崔木匠,她真想把他的目光拽回來,拽到桌子上歇一歇、想一想,仔細動動腦筋啊。
接下來便是這個中午的午覺了。
不光是青小姨要午覺,大家都是要午覺的。夏季的漫長中午,不歇歇干什么呢。那睡柜不還是在么,它的主人不就是崔木匠么,再去睡就是,又不是沒睡過。彭大娘去收拾睡柜了,小甜兒主動地幫忙——她很懷念曾聽到的燕子呢喃,再說,她正希望崔木匠可以欣賞到青小姨的睡模樣呢。
可青小姨這次卻無論如何不答應了,當然,她什么都沒說,半個“不”字都沒說,只東一樣西一樣動作挺大地收拾著,要出門的樣子。
彭大娘覺得怪:咦,你們廠今天不是休息么。
是,是休息。但我中午在廠里睡慣了,我要到那邊去睡中覺。青小姨用一種很冒犯的口氣,決意我行我素了。
大哥大嫂都被她那鐵板一塊的樣子給逗笑了,認為她真是莫名其妙。崔木匠連忙上來打岔:天兒這么熱,我看……也不方便,要不,我先回吧。
沒事,你在這里歇著,我反正要去的。青小姨忽然換了一種幾乎是溫柔的口氣勸下崔木匠,在后者迷惑的感動中,她已經戴上遮陽帽、提上她的小包,邁著一種筆直的像是孤注一擲的步子走了。她隨身的包里,有新買的一瓶芳香宜人的桂花香水,小甜兒瞅見青小姨剛剛塞進去了。
說話間,她也就走了,不知為何,在她留下的灼熱與空虛的空氣里,小甜兒嗅到一股危險的氣息——今天廠里完全沒有人的呀,也許,除了那個穿休閑裝的男人……
直到崔木匠走了好幾天,關于午睡的小疙瘩還留在小甜兒心中,讓她重重地上了心,卻又無處下口,直到看到地陀螺——最近這家伙越發不愛理自己了,眼睛都不愿往她身上靠,小甜兒有主意了,他不是一直喜歡扮演得無所不知嘛,不如慫恿他……
見小甜兒要正經跟自己談事,地陀螺急忙給自己的光膀子套件黃巴巴的汗衫,然后愛理不理地用腳尖敲打門檻,瞇起眼:這么說,你是叫我去打探姑姑在地毯廠的午睡?這太怪了吧,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小甜兒給一下子說破,倒啞口無言、忽而語塞了。
地陀螺仍是用那種老氣橫秋的語氣:別看我不注意你,哼,其實我知道你想什么。不過呢,你怎么想都沒有用……那個畫圖員……
聽到這個稱謂,小甜兒心中一蕩,猛然呆住,地陀螺馬上警覺地不做聲了,隔了好久,才帶點推心置腹地,用一種當家人的神態:……嗯,其實,告訴你也無妨,但只能你知我知,可不要走漏到奶奶和媽媽那里。關于畫圖員,怎么說呢,你想想,總歸要比崔木匠強的,姑姑的心意我最理解,她一向就是眼界很高的,若真能成了,不是天大的好事情……總之你就別操心也別多手腳啦,這又不是你家里的事……
中午的太陽很辣了,小甜兒卻丟下地陀螺,獨自跑到向日葵的坡子上。
那些向日葵的臉現在長得多大啊,并從原先的翠綠慢慢變得深了,有點老了似的,也不再隨風擺動了,正午的烈日下,它們黑著臉,嚴肅地盯著小甜兒。小甜兒也嚴肅地盯著它們,一直把眼睛都看得花了。
9
青小姨的書,通共也就看了一個夏天吧,到秋天將至,她忽又不看了,另換了個新毛病:發呆。
她這個發呆,不一般,一是朝向很固定,必然是背著睡柜,哪怕無意中轉了個身,也即刻又轉回去,眼睛絕對不往睡柜上停;二是時間漫長,上來就是一整個晚上,從剛吃過晚飯進房,到小甜兒做完作業躺下要睡,青小姨還保持著最初的姿勢與表情,整個人都像給念了咒語或是罩了鐵布衫,靈魂出竅,并且刀槍不入——她既是不開口,小甜兒也決不愿貿然發問,她想:青小姨一定碰到個大問題,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大問題,就讓她好好發呆吧。
到底還是青小姨自己沒憋住——著實并無旁人可說,或是覺得小甜兒反正是個外人,又是孩子,說了無妨。不過,嗨,也不是正經的說話,只是問了幾句而已。久不交談,她的聲音十分生澀。
你,看看我,有什么不一樣嗎?
像有人在暗中捏自己的手,甜兒感到一種巨大的責任。她沒敢亂動頭,只用眼珠把青小姨上下左右看了好幾遍,然后才謹慎地說:有。
哪里?青小姨也不動頭,眼睛朝她照了一下,特別地亮,泛著寒光似的。說說呢。
變好看了。甜兒說的是真話。
還有呢?青小姨對這個答案不滿意,她在等下文。
呃……甜兒又仔細看了一圈,看到青小姨脖子里鎖骨處的陰影、微微凹下的眼眶,幾乎著急了,終于想出一個。你瘦了。
瘦了?青小姨抓著這個詞,拿起小鏡子前后照,竟是信了。她笑了一下,像是心情好了些。她耐心地等小甜兒說完躺下,然后關了燈,兩人一起睡了。
甜兒也挺高興。瞧青小姨多待見她啊,她一定沒對其他人討論過這些問題。
這樣想著,甜兒忽然沖動起來,大起膽子,想說一句她一直就想說的話。沒有開燈,也沒有坐起來,甜兒只在黑暗中對著被窩大聲說:青小姨,崔木匠人很好,很好的。
青小姨卻在被窩那邊抽泣起來,聲音不大,但一直不停,直到甜兒睡去,腳頭還在哭。
到第二天晚上,哭的人又多了一位:彭大娘。并且,她偏偏要沖到房里來倚著睡柜來哭,像是跟睡柜有千絲萬縷的瓜葛似的。她涕淚漣漣地癱在睡柜邊,用力捶打著,邊哭邊含糊地罵:丟死人啊,丟死人啊,怎么能出這種事情,你叫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倒說,是誰的啊?是哪個畜生?有本事他來提親娶你啊!她又拍起睡柜。
兒媳婦直盯著青小姨的嘴,青小姨則白著臉,抵死不開口,甜兒站在家具的黑影中,疑惑地望呆,忽被地陀螺一扯,拖到外面。
出什么事兒了?
不關你的事兒。地陀螺站在窗戶外墻根下的燈影里,學著大人那樣,把他能想到的都罵了一遍:他媽的,他奶奶的,龜兒子的,祖宗八代的,看上去人模人樣。
罵誰呀?
你不懂的!總之是你們“上面”人干的好事。地陀螺激憤而瞧不起地看看小甜兒,一雙小男孩的眼里,滿是羞惱而疼痛的淚。
此后,青小姨的嘴上像掛了把鎖,更加不說話了,每日很早就上床去睡,好像只有夢,才是她最舒適的去處。這樣睡下去,使得她從短暫的瘦又變回到平常,甚至微微胖了起來。甜兒很想告訴青小姨,她卻不再關心任何有關胖瘦的問題了。
彭大娘兩只眼睛腫腫的,在睡柜上鋪開新彈的棉花胎,找出泛有光澤的牡丹花緞面,縫起被子——那是嫁妝被。她的動作遠不如平常漂亮,拉線的手扯得一點不高,顯得一點不自信。若有人來串門,她就放下來不縫,以免別人攀談詢問。
有一天,家里無人。彭大娘突然把甜兒喊過去,有些結結巴巴,老臉都有些漲紅:你……你可知道……
甜兒不十分清楚彭大娘要問的是什么,或是隱約知道但又不敢輕易作答——不等她反應,彭大娘卻先搖上頭了:唉,算了算了,你不會知道的。你去吧,什么都不知道最好。
一邊說著,大娘把她粗粗的手指從眼角掠過,止住一串渾濁的淚。
10
東壩的各樣景物中,諸如晨霧、小河坡、收割過的地面、生有青苔的井臺、新堆的麥稈……小甜兒最中意一樣:星空。只要是晴朗的晚上,把頭一抬,就在那兒呢。
在“上面”的前十年,她從沒看過這樣的星空,飽滿而沉甸甸地覆蓋著,那陌生的黑藍里,幽暗而龐大的心事,從天上一直垂到地面……當她想一個人待一會兒,或者想起了家里的從前、眼下與以后,便總是假裝要到后屋有點什么事情,然后,她便穿過彭家的小院子,走到黑糊糊的后門外,一直磨蹭在那里,站在星空的眼皮下,站在星空的懷里,站那么一會兒……慢慢地,便會升騰起一種奇異的感受——她覺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了,她不是爸媽的孩子,也不是彭家的寄居者,她不是在這么一個具體的人世間,而是在一個抽象的看不到的地球上,在空氣里,在宇宙間……
這天,小甜兒仍是站在后門外,正被那些無邊無際的玄妙弄得暈乎乎、空茫茫的,忽然聽到有人悄悄地站在自己身邊。聽那氣息,是青小姨。
青小姨吸了一口清冷的夜氣,似乎抖了一下:知道嗎,小丫頭,我最羨慕你了。
小甜兒仰著頭:我?我有什么好羨慕的,什么都沒有,連家里人都快忘掉我了。我羨慕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