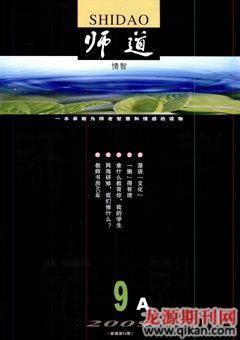日本小學社會科教育一瞥
何清鳳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國內專家學者都關注英美等西方國家的教育經驗,而對諸如日本等亞洲國家的教育情況則缺少應有的關注。日本中小學社會科建立于1947年,替代了戰前修身、歷史和地理三學科,作為民主主義新教育的象征而成為中小學課程中的核心學科。
貼近孩子生活的教材
日本社會科的教材可以是地方性的教材,只要通過文部省的審核就可以投入使用。因為這樣,不少教師編寫教材,內容與教學大綱大體方向一致,但具體的一些操作,著重于本地的現實狀況,貼近孩子們的生活,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
下面就簡要介紹幾例地方性教 材的內容。
1. 關于廢棄物的處理的教材,會讓孩子們親身參與富士山粗大垃圾的處理。
“修學旅行”是每個日本小學生的“必修課”。如學校會組織學生去富士山看火山地貌、撿垃圾。這樣的風景陶冶下,孩子們看到垃圾給美景帶來的破壞,都非常積極配合清理工作。孩子們還有機會去垃圾場調查細致的處理方式,通過親身勞動來體驗書本外的真實生活。這與倡導本土文化教育是相輔相成的。這也是名勝古跡成了“修學旅行”首選地的原因。“修學旅行”不僅讓學生開闊眼界,同時也讓他們有了探索自然和社會的機會。這些舉措與中國古代“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教育思想有一脈相承之處。
2. 關于社區生活和生產的教材,會讓孩子們了解社區的消費狀況和商店街市的買賣情況。
有的教師就讓孩子們去了解當地著名的靜岡橘子。首先,從“觸摸到的東西”入手,如觀察買橘子的人如何挑選,賣橘子的人如何經營。其次,通過“觸摸到的東西”去探索“用心領悟的東西”——社會的存在意識。此時教師就會運用恰當的指導,因為人們的消費愿望等種種“用心領悟的東西”,既不能用教材簡單地固化,也不能單純地指望學生自己消化,尤其是讓學生通過鮮明的表象看到“買與賣”的社會意義,更不是看看、聽聽就能夠理解的。這就存在著一個教師將教材的意義和界限明確,上升到意識化的過程。
此外,讓學生親手體驗學習制作以橘子為原材料的食品等活動也頗受歡迎。
這些看來好像都很有難度,對于一個小學生來說,他能做好嗎?比如說了解垃圾分類、處理方法以及基本程序,然后畫出示意圖,寫出調查報告。我一想到這一系列的任務都是由八九歲的孩童來完成,就不由地嘆服于日本教育的效度。事實勝于雄辯,不少日本小學生做出來的報告可以媲美大學生的作業了。
個性化的教學
起初,日本教育要讓學生絕對平等地學習,但很快日本就發現了這種“絕對”平等的壞處,這與教育追求個性化的初衷相悖,在文部省的鼓勵下,一些獨特的教學方法也漸漸出現了——
(一)讓黑板成為學生的發言記錄
在中國,黑板是教師板書的載體,但在日本一些社會科的課堂上,教師寫在黑板上的不是準備讓孩子們掌握的知識,而是學生的發言內容。這種板書有利于學生對自己和同學的觀點與見解進行思考、對比,也有助于學生將感性的和粗淺的片面認識提升至理性認識。這種距離感的拉近讓學生更加活躍于課堂,也讓他們明白抒發自己觀點的重要性,知識的授予也是從學生的能力增長上滲透到他們的思想上的。
(二)展現每個學生個性的工藝品
走進日本小學的教室,你可以看到很多工藝品,走廊、校道里也擺放著許多藝術作品。他們認為這些都是孩子們個性化的制作,既然大家有平等的受教育權利,學生的作品無論好壞都應該被展示出來,正是這種尊重使孩子走在了“自由、平等”的學習之路上。
切實可行的課程評價制度
很多課程都會有一套較全面的評價制度,日本小學有它自己的評價制度。比如拿孟令紅先生翻譯的教材中關于“水”單元的教學評價看:單元的教學評價都有“興趣、熱情、態度”、“科學的思考”、“技能、表現”、“知識、理解”四個方面的標準。雖然,不能說每一堂課都要兼顧到四個方面,但都要對某一方面有所側重的。例如,“水跑到哪兒去了”中,對于洗的衣服里水的去向問題,就是側重“技能、表現”方面的評價。這里主要評價學生是否在思考的基礎上,理解實驗方法并進行驗證的,以及評價學生是否能夠把實驗中的各種細節與水的狀態變化聯系起來進行再思考。因此,教學評價就是對課程標準中規定的教學目標與課堂教學實際情況的具體評價。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小學的教學目標與教學評價在堅持一致性的基礎上,具有可行的操作方法。
深入童心的應急教育
特別要指出來的是日本社會科對孩子們應急事務的教育。日本是個多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國家,他們在應急險情的教育上早已從娃娃抓起。
一位來自四川在日本生活過的女記者說到自己女兒在日本所受的小學教育時,提到女兒的社會科課內容相當多都涉及到應急教育。日本的避難訓練其實是從保育園就開始了,即使是在保育園里的三個月大的嬰兒,也要由老師抱到一起訓練,在老師臂彎內躲在床邊。到了小學, 這位記者的女兒還在社會科里做關于消防的社會調查。她的女兒跟著班里的小組,去消防隊了解消防部署過程、消防基本程序,然后畫出消防部署圖。這又令筆者感嘆日本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社會能力。
另外,這位女記者說,她在日本教小學生學中文的時候,有時會讓孩子們畫畫,再用中文說明畫的內容。一個6歲孩子的畫讓她感觸特別深。他畫了一棟樓,盡管這棟樓缺了很多元素,但是卻清楚標注出了逃生通道。“日本的避難訓練真的是深入到每個人的骨髓里。”
北京的一位校長應日本某教育組織的邀請,赴日做教育考察。她在接受記者的訪問時提到:“培養出優秀的學生,物質條件不是最重要的,觀念的作用不可小覷。”日本有眾多博物館和科技館,陳列內容有地方特色與時代特征,是理想的課外學堂。例如在奈良大和房屋研究所,孩子們能通過模擬演示體驗免震住宅的工作狀態;在神戶人與防災未來中心,孩子們能通過簡單實驗了解地震原理,將防災遇險時的求生知識意識化,而不是“填鴨式”地灌輸。更為重要的是,這些應急觀念的形成過程中還注重弘揚日本人民的不屈和互助精神。神戶防災中心有段介紹阪神大地震的影片,通過一位幸存者的目擊口述地震發生、救援、災后重建全過程,處處突出人們的友愛精神和責任意識,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今年四月日本的小學教材改革,第一次發放補充教材,其中包括科學教材的補充,涉及到應急教育的內容也有所增加。
我們常常提起“減負”“素質教育”。日本則提倡培養學生的“生存能力”,提倡“寬裕教學”,這兩種精神在教學中常常表現在孩子處理應急事務的能力和參加興趣班上。日本小學生必須參加社團活動,而且每天要有三小時的訓練,因此你能看到放學后很多學校里仍然呈現出一派活躍歡騰的景象。
(作者系暨南大學華文學院學生)
責任編輯蕭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