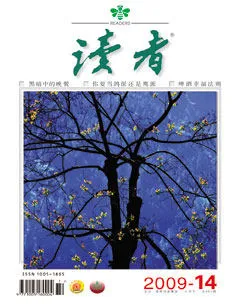林庚:布衣情懷
劉超
林庚出身世家,其父林宰平,“生平愛藝術,好朋友,精書法,能詩文”,身在北大,兼職清華,在學界與梁啟超、王國維等同為清華國學院德高望重的大學者。按說,這樣家族出來的該是做派盎然的世家子弟才對,可是,先生不然。
那時,先生家在福建會館,離魯迅、周作人住的紹興會館僅八丈之遙。先生自幼酷愛放風箏,家門前有個大操場,每當風起之日,天空中就飛舞著他的風箏。
先生少年英發,從國內頂尖的中學畢業后,于1928年考入清華園,讀物理。兩年后,林庚突然發現自己對文學居然如此難以忘情。有一天,他找到了國文系主任朱自清,申請轉系。不久,他就成了國文系的學生。從此,他與吳組緗、孫毓棠成為同窗密友。在此后不長的時間里,他發表了二三十首舊體詩詞,以至于在舊體詩詞中流連忘返。只是突然有一天,他醒悟到:古典詩詞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已近極致,無論今人怎么努力,都難免嚼前人嚼過的饃——一樣的格律,一樣的措辭,一樣的風格,一樣的主題……現代人無論有何等的才力和心氣,都難以超越古人而另拓疆土。
從此,開始寫起新詩來。
不日,先生在《現代》發表了第一首詩《風沙之日》,寫出了對現實的不滿:北平太荒涼,太死寂,實際上完全是個“邊城”。先生的新詩生涯,從此一發而不可收。自此,詩人林庚橫空出世,聲名鵲起。其詩既有翩翩欲飛的少年精神,亦別有一抹晚唐詩的風韻,故在眾多詩作中獨標高格。可以說,如此年少而成就如此大名者,在彼時的清華,大概唯曹禺一人可比。
當時,季羨林、吳組緗、李長之諸人亦頗為活躍,四位少年,聯袂清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遂得“清華四劍客”之美譽。
1933年,著名詩集《夜》的出版使得先生順利畢業。同時畢業的,還有吳組緗、錢鐘書、曹禺、喬冠華、孫毓棠、王鐵崖、巫寶三等,這就是清華歷史上極其著名的“神奇的33屆”。近乎同期在校的還有華羅庚、胡喬木、吳晗、錢偉長、葉篤義等。所有這些人,日后都成為各界的一流巨子,為中國現代史畫上了極其璀璨的一筆。
畢業后的林庚,開始擔任朱自清的助教。
1934年的夏天,東北烽煙漸盛,陰影直逼北平。這時,先生下江南了,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杭州,一路山水,一路詩文。在這煙雨江南的山山水水中,先生且走且寫,且行且歌。可身在六朝金粉的江南,他還是不忘烽煙彌漫的北國。
在上海,他見到了施蟄存,二人遂莫逆終生。經此南行,長居北方的先生亦與南方結下了不解之緣。抗戰爆發后,先生作別北平,揮戈南下,在廈門大學開始了其嚴謹的學者生涯。抗戰勝利時,先生也完成了其皇皇大作《中國文學簡史》。此書甫出,文林為之轟動,先生亦成新一代文學史家之殿軍。先生出身詩人,談詩論藝自是牛刀殺雞、勢如破竹,其書于楚辭、唐詩、魏晉文章與明清小說,均有新論,筆之所至,蔚成經典。尤其是“盛唐氣象”和“少年精神”,更成為中國詩論中的經典論斷。
新中國成立后,清華、燕大文科盡數歸并北大,先生與季羨林、吳組緗、周一良、王瑤等齊集燕園。從此,先生在燕南園一住就是55年。
世易時移。“文革”一來,烽煙再起。先生是林中喬木,樹大就招風。有一日,先生接到一個電話,讓馬上到北京火車站,有要事。時已子夜,燈火寥落,天宇一片晦暗,這根本就不是個夜出的時候。可是,“上面”之言就是命令,怎么能不去呢?怎么敢不去呢?
先生匆匆忙忙地來到北京站。過去一看,原來是江青要去天津。那一次,看到所謂的全民詩歌運動后,先生深覺錐心之痛。
江青一次次的邀請,讓先生苦不堪言。到后來,他已不忍再去。一個矢志追求唯美的詩人,卻不得不在政治漩渦中應酬,其滋味何如?那酷愛自由、放達瀟灑的天性早已融入骨髓的詩人,又怎能任人擺布?
又一個深夜,他接到了電話,還是江青讓他去講詩歌。
先生咬了咬牙,橫下一條心:“對不起,我夫人身體不好,我要留下照顧她。”
對方幾經邀請,先生仍是咬緊牙關,不松口。須知,那年頭,能夠和通天人物攀上關系,搭上線,該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榮耀啊。可先生卻不以為然,他不屑于做這紅頂詩人,硬是拒絕了。
他知道這次拒絕意味著什么。此事當然不能算完。1974年初,國務院記者招待會前夕,先生收到了請柬。此會由周總理親自主持,規格極高。先生得知后極是興奮。“文革”以來,總理獨撐危局,身心俱疲,先生多想看看他啊!可是,正在這時,先生得知:這請柬原來是江青讓人送來的。詩人大窘,繼之大怒。
顯然,如果這次去聽報告,下次就不能不去講詩歌。
先生唯一的選擇,就是把請柬擱置起來。就此,詩人失去了生平唯一一次親見他最心儀的政治家的機會。
說也奇怪,“文革”結束后,某些“四人幫”的猛將,轉眼成了反“四人幫”的斗士,“變臉”之速,堪稱卓絕。先生不屑此道,卻成了被甄別的對象。在北京體育館的甄別大會上,先生名列榜首。甄別完畢,主持人問先生有何感想,先生一言不發。
自此,先生絕意俗事,專情研究。他以“遠離功利,抗拒誘惑”自守,亦以此要求門人弟子。國內外的一切邀請,他都拒絕;一切媒體,他都回避;一切榮譽,他都不要。照理,名利權位于他不過唾手可得,然而先生早已無意于此。他只是固守著自己的大寧靜,清清靜靜、自自在在做著自己的事,全然疏遠了外界各種熱鬧場、名利場。人說:“先生從不涉足權力名利,這不是自命清高,不是不屑于談名逐利,他是壓根兒就沒有這些概念。詩歌和學術,才是他一生的修行。”信然!
年深月久,因著先生的徹底低調,外界竟也將先生淡忘了,真是“山中有高人,世上無人知”了。先生卻不以為意,仍舊專注于自己的創作和研究,并在80高齡時出版了童趣盎然的《西游記漫話》,遂成明清小說研究的又一高峰,直令無數內行大呼相見恨晚。92歲那年,先生又出版了新著《空間的馳想》。然而,年歲日增,寫了七十多年詩歌的詩人,已漸漸走出詩歌的畛域了。“我到這年紀了,什么都看透了。看透了,說透了,還怎么能寫詩呢?”詩人如是說。詩是需要朦朧感的,因為朦朧,才有含蓄,才有魅惑,才有創作。若是看透了,這一切也就沒有了。
后來,北大成立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各方千難萬難才請動先生出山。
此外,先生再沒有擔任任何社團的任何職務。畢其一生,先生最高的官銜,就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正科級。
1986年,年事已高的先生決意退出講壇。這時,系里正籌劃著請老教授們為學生講課,錢理群就出面把吳組緗、王瑤、季鎮淮、游國恩等都請了過來。這其中,也有先生,主題是講屈原和李白。由這樣一位楚辭和唐詩研究界的翹楚,來講這兩位最杰出的浪漫主義詩人,絕對是當之無愧的不二人選。先生決定把自己畢生的功力、才情、學養統統毫無保留地傳給學子。為著這“最后一課”,在講臺上已躬耕了五十余年的先生,整整準備了一個月。先生開講那日,名流如云,燕園為之擁塞,場面極一時之盛。鈴聲一響,身高一米有八的老先生,穿著嶄新的黃皮鞋、黃大衣出現在講臺上。
整整一節課,先生只講了一首詩,然而,卻講得激情飛揚,貫通古今,縱橫捭闔,出神入化,爐火純青。在先生的講授中,長眠千古的屈子和詩仙奇跡般地得以復活,帶著五千年華夏文化的精魂,洞穿時空,直擊今人的心靈世界。
這堂課下來,大家都蒙了:詩歌竟然可以講到這個境界!
然而,也正是這堂課之后,先生就大病一場,倒下了,休養了好長一段日子。
從此,先生蟄居燕南,讀書寫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蕭然自遠,既不媚世,亦不怨世,保持著本真自然的心境和生活。那些年,燕南園中常見一位清癯挺拔的老者在園中散步,此公仙風道骨,目光清朗,面色和煦。
95歲時,先生對畢生的詩路歷程做了回眸。先生斷然否決了戴望舒、李金發等人的論斷:“不,我不是現代派。”
原來,外界一直以為先生詩風耽溺小我,不涉世事,尤其是左翼陣營對此大加貶斥。先生一直不曾辯解,此次才直陳心曲:“過去一直說我寫詩脫離政治。我是不關心政治,因為我不了解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政治很復雜,但是我從來沒有脫離社會生活。我生存在社會中,我了解社會生活,我也熱愛社會生活。我的詩,涉及當時的國家命運,寫的是我的經驗,我所理解的社會生活。”
其時,弟子們送給他十六個字: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懷。
先生藹然頷首。
又是一年,快到中秋了。這將是詩人此生的第97個中秋。國慶后的第三天,先生獨坐窗前,仰望蒼天,唯見皓月當空,一層薄薄的月光灑落下來,地上鋪了一層軟軟的清輝。先生用他那清瘦的手盛了一汪清輝,靜靜地把玩著,體會著。不經意間,他又想起往昔的種種:想起幼時的城南舊事,想起少時的沙灘風景、紅樓月色,想起青年時清華園中的荷塘月色,想起燕南園中冰心院落里的新月往事,想起壯年時鼓浪嶼的海上生明月……想著想著,他漸漸地漾出了一絲微笑。
“月亮,什么時候才能圓呢?”詩人自言自語。
再過兩日,就是中秋了。然而,先生等不了了。就在那個晚上,那個月色皎潔的晚上,我們的詩人,去了。
(馬佩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筆桿子——晚近文人的另類觀察》一書,李 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