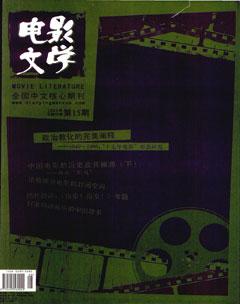論弗言尼亞·伍爾夫的現代小說觀
李權文
[摘要]伍爾夫的現代主義小說觀主要體現在她的論文《論現代小說》里。該文論及了傳統小說觀與現代小說觀的分歧,提出了小說真實性,指出了作家的使命,日月確了小說技巧和小說選材范圍等一系列內容。大膽預測小說的體系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伍爾夫的現代小說觀是她在對現代小說觀察分析的基礎上,發表的看法和作出的設想,預測了小說可能的發展方向。但是她的批評過于注重情感、印象等內心精神層次,未免落入了印象式批評的窠臼,夸大了精神在小說創作的作用。
[關鍵詞]弗吉尼亞·伍爾夫;現代主義;意識流;印象式批評
弗吉尼亞·伍爾夫是英國著名的小說家、文學評論家和女性主義批評家。她自幼便開始閱讀各種書籍,通過大量閱讀完成了自我教育而成為名噪一時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的主要成員.經常與當時的文學界名流往來,從事創作。伍爾夫主要從事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伍爾夫的小說多以她熟悉的倫敦及童年與家人度假的康沃爾郡海濱為背景。關心的主要是個人獨有的經驗與主觀感受,以及超出于具體社會環境之上的人與人的關系。雖然對政治不太關心,但是對婦女的權利,特別是有才能的女子的權利十分關切。她的這些主張在小說《奧爾蘭多》及論文集《一間自己的屋子》(1929)、《三個畿尼》(1938)中集中反映出來。(王佐良,2005:221)伍爾夫以她的文集、書信為媒介,闡述現代主義的小說形式、小說時間、小說人物和情節結構的主要觀點。說明以反映個人印象的直接性、內心意識的真實性為主要任務的現代小說觀與傳統小說理論之間的差異與聯系。她的作品的獨特之處在于她在小說的內容和創作方法的創新方面所做的努力與取得的成就,這使她在現代主義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眾所周知,伍爾夫是英美女性主義學界的先驅之一。瑪麗·伊格爾頓認為,伍爾夫是“當代女性主義論爭開創之母”.她“宣布了”許多后來的女性主義者們爭論不休的問題.而且她本人也成了某些論爭展開的場地。她的兩個關鍵文本《一間自己的屋子》和《三個畿尼》對女性主義理論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其主要貢獻就是,她認識到性別、身份是一種社會構建,能夠受到挑戰和發生形變,關于女性主義批評,她一直探索的主要是女性作家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社會和經濟方面的障礙。她拒絕“女性主義意識”.要求自己的女性性處于無意識狀態,她挪用布盧姆斯伯里文人圈子里“雙性同體”的性倫理,希望在男性的自我實現與“女性的”自我消滅之間實現一種平衡。(參見拉曼·塞爾登.2006:143—144)
伍爾夫的現代主義小說觀主要體現在她的論文《論現代小說》里。她在文中論及了傳統小說觀與現代小說的分歧.提出了小說真實性概念,指出了作家的使命,明確了小說技巧和小說選材范圍等一系列內容,并大膽預測小說的體系是開放的,而不是封閉的。
她采用形式主義的語言,把它作為女性主義策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爭取權利。(Reed,1992:26)她把矛頭直指英國19世紀末的現實主義作家:威爾斯、班納特和高爾斯華綏,貶稱他們三人為“物質主義者”。伍爾夫認為他們沒有重視人物內在的心理結構,即她所稱的“內在的主觀真實”.“他們之所以令我們失望,正是因為他們關心的是軀體而不是心靈。他們寫了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他們浪費了無比的技巧和無窮的精力,去使瑣屑的、暫時的東西變成貌似真實的、持久的東西。”(伍爾夫,2000:4)這實際上與20世紀意識流小說作家的觀點不謀而合,后來她自己確實在意識流小說創作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績,與喬伊斯、勞倫斯等人齊名。
真實觀是伍爾夫拿來駁斥“物質主義者”的有力武器。她所說的真實是積累在我們內心深處而又不斷地涌現到我們意識表層的各種印象。“把一個普普通通的人物在普普通通的一天的內心活動考察一下吧。心靈接納了成千上萬個印象:瑣屑的、奇異的、悠忽即逝的或作者用鋒利的鋼刀深深地銘刻在心頭的印象。”她認為他們忽略現代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因而“往往使我們錯過、而不是得到我們所尋求的東西。不論我們把這個最基本的東西稱為生活還是心靈,真實還是現實。”作家尤其是現代主義作家的創作目的就是要精心地捕捉這些真實,而小說本身就是一系列感官印象、知覺以及思維活動的集合。
伍爾夫認為這些“物質主義者”的觀點和創作技巧過分哲理化,甚至有些刻板。伍爾夫發現這些都有悖于生活的本來面目,生活不是那些結構工整以及說教的規訓。而是“來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計其數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當這些原子墜落下來,構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生活是什么?伍爾夫運用了一個生動有趣的比喻,她把生活說成是一個光環、一個包圍著我們的半透明的封套。她說:“生活并不是一幅勻稱地裝配好的眼鏡:生活是一圈明亮的光環。生活是與我們意識相始終的、包圍著我們的一個半透明的封套。”
顯然,伍爾夫的“封套”并不是一種束縛限制的條條框框。而是“透明柔軟、容易滲透、富于彈性、伸縮自如、可以延伸的一層云霧一般的氣氛,它的功能不是去強加某一個觀點,”而是“包羅萬象地容納了各種主觀印象,容納了變化多端、不可名狀、不受限制的內在精神,容納了整個世界。”由此,伍爾夫明確主張作家(主要是小說家)的中心任務:即采用一種無拘無束的方式來記錄人們內心的意識流動。于是她向小說家們呼吁:“讓我們按照那些原子紛紛墜落到人們心靈上的順序把它們記錄下來:……不論從表面上看來它是多么不連貫、多么不一致……”
這種無拘無束地記錄人們內心的意識流動的創作方法顯而易見就是后來的現代主義小說家所熟練采用的意識流技巧。在這個問題上,伍爾夫決不啻是一個小說理論家.她更是一個小說創作的踐行者,并取得了豐碩成果。她為小說家探尋到一種新的技巧,“讓他們能夠真實地去描述內在的現實,并表明這個現實只能是內心的。她既不做評判,也不去說教。她惟一關切的是,要給讀者提供一種對生活更加清新鮮活的感受,以期開拓讀者視野,讓其透過表象發現思維和情感的運動方式。”(Fleischmann,1977:541)如在她的《達洛維夫人》和《到燈塔去》兩部小說中,她都恰到好處地采用了意識流技巧,如間接內心獨白、自由聯想、象征手法、蒙太奇和多視角敘述方式等,使其成為意識流小說的典范之作。
伍爾夫認為,在她的同時代作家里,能夠采用這種伸縮自如的意識流模式創作的,正是以喬伊斯為代表的年輕的現代主義作家。她對喬伊斯贊賞有加,把他稱為與她所貶斥的“物質主義者”相對立的“精神主義者”,認為他超越了“物質主義者”的傳統方法,敢于探索新的模式去記錄“內在的現實”,“他不惜任何代價來揭示內心火焰的閃光.那種內心的火焰所傳遞的信息在頭腦中一閃而過,為了把它記載保存下來,喬伊斯先生鼓足勇氣,把似乎是外來的偶然因素統統揚棄。”(伍爾夫,9)
接著,伍爾夫對作家如何選材發表了自己的洞見。她
認為選材一定要與過去作家的做法有所不同,敢于打破傳統的羈絆和約束。現代作家應該想方設法、自由自在地選材并進行描述,必須要有足夠的勇氣公開聲明:“他所感興趣的不再是‘這一點而是‘那一點;而他必須單單從‘那一點選材,來構成他的作品。”這里的“那一點”是指作家的興趣所在,它應該存在于“心理學曖昧不明的領域之中。”顯然,這仍然是針對“物質主義者”只重視軀體而言的心靈層面的東西。在該領域的選材形式上可以別具一格,內容沒有任何規約性,沒有既定的或恰當的選材。她一針見血地指出:“一切都是恰當的小說題材;我們可以取材于每一種感情、每一種思考、每一種頭腦和心靈的特征:沒有任何一種知覺和觀念是不適用的。”
那么選材是否等于新的文學傳統的誕生呢?伍爾夫認為作家必須還要不斷地探索。在此她明確提出了小說創作的實驗主義觀.她歡迎一切實驗和探索。為了塑造鮮活的人物形象把握內在的現實,她提倡藝術家要自由探索,獨辟蹊徑地去找尋最理想的藝術形式,以表現技巧和創作題材。因此她大膽預測:“沒有一種實驗,甚至最想人非非的實驗——是禁忌的。”她的創作方法的無限性恰好印證了世界的廣闊無垠,以及內在現實本身的無窮無盡的特性,正因為如此,小說家的探索與實驗便具有無限的樂趣和重大意義。
總體來看,《論現代小說》是在伍爾夫對現代小說觀察分析的基礎上發表的看法和提出的設想,預測了小說可能的發展方向。小說是一種自發的靈感爆發,作家的任務就是記錄心靈對于各種印象的被動感受,而不必修改剪輯或操縱這些印象,因為它們就是真實的。從伍爾夫對生活以及真實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她把人的物質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置于生活的范圍之外,認為生活存在于人的主觀頭腦中,它是一種內在的精神,是各種雜亂的印象和感性活動的總和。伍爾夫的這種‘內在主觀真實的觀點決定了她在反映生活、刻畫人物時,把重點放在探索人的內心精神世界上。”(李森,2000:63)她批評愛德華時代的三位作家威爾斯、班納特、高爾斯華綏是“物質主義者”。因此,伍爾夫和他們徹底決裂,尋找一種更為深刻更富有暗示性的全新的方法來如實地呈現生活。這種“全新的方法”即她的獨特的意識流技巧。
伍爾夫做出的結論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伍爾夫比較英國和俄國的小說之后,認為盡管前者受到后者的影響較大,但是前者也有其自身的幽默和魅力。她認為這些小說,尤其是現代小說都為讀者開啟了無限的可能性。它們像潮水一般向我們涌來,帶來了“一種藝術具有無限可能性的觀點.并且提醒我們,世界是廣袤無垠的……”而且沒有哪樣東西是禁忌的。說實話,她的批評過于注重情感、印象等內心精神層次,未免落入了印象式批評的窠臼,夸大了精神在小說創作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學關注的不僅僅是人與自我(內心)的關系,更要關注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的關系等重要內容這一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