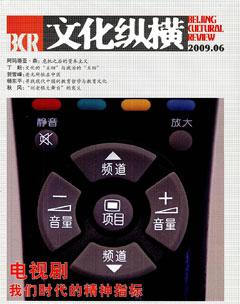第三代詩人的商業化轉向
燕 舞
5月中旬,《南方周末》刊出一篇報道《民營書商的新財富游戲》,將備受爭議的當紅暢銷書《中國不高興》的策劃人、新近成立的北京鳳凰聯動文化傳媒公司總經理張小波放在“詩人書商”的大背景下評述。張1980年~1984年求學于華東師大中文系時,躬逢“第三代詩歌運動”,與人合出影響一時的詩集《城市詩人》;1991年后,張減少甚至放棄詩歌寫作,通過出版香港武俠名家溫瑞安的小說而掘得第一桶金,近年更是通過《求醫不如求己》(“國醫”系列)、《山楂樹之戀》《風雅頌》等賺得盆滿缽滿。
張小波的“詩人書商”同行還包括出版“黑鏡頭系列”的萬夏,出版《誅仙》《明朝那些事兒》《盜墓筆記》系列的沈浩波,出版《藏地密碼》的吳又,以及李亞偉、郭力家、趙野、葉匡政和蘇非舒等。
《民營書商的新財富游戲》這篇報道略欠專業和純熟,所以在看新書《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柏樺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4月)的同時,我就拿出了束之書架久矣的《燦爛》(楊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對照著讀,發現《燦爛》堪稱以點帶面地考察了當代中國詩人的分化,特別是后北島時代的“第三代詩人”的商業化轉向。主流文學史史家如洪子誠、程光煒,將“第三代”定位于“存在多種探索路向”的“朦朧詩之后青年先鋒詩歌的整體”,其“標志性”作品在1983年和隨后幾年中陸續出現,其活動主要以組織社團、“非正式”出版詩刊(詩報)的方式進行,涌現出了一大批以韓東、于堅、李亞偉和海子等為代表的優秀詩人。
1985年年末,萬夏和楊黎在成都合作開過“一家圈子味非常濃的書店”,這家生意馬馬虎虎的“Y咖啡”終因與另一位合作者駱耕野的利益糾葛而終止,“萬夏走了,去和陳禮蓉另外開了一家咖啡店”。
1990年代初,萬夏一夜之間攢出的《葉子媚葉玉卿大寫真》狂賺十幾萬元,他拿出其中的12萬元在1993年自費出版3000套豪華精裝本《后朦朧詩全集》,當時還高調表示要出版《朦朧詩全集》和《前朦朧詩全集》。在后來的“黑鏡頭”和“紅鏡頭”系列大賣特賣后,萬夏利用雄厚的經濟資本繼續圓了很多詩歌夢,包括資助楊黎全國范圍尋訪“第三代詩人”(還有紀錄片性質的拍攝),并出版《燦爛》一書。
楊黎為寫《燦爛》去上海采訪時,住的是張小波在浦東的豪華寓所,“我從北京出發時,張小波把鑰匙給了我。他把鑰匙給我時,還對我說,不要偷我的書哦。我說,那誰知道。”“不要偷我的書”,短短六個字就暴露了張小波作為詩人(讀書人)的本性和嗜書如命的特質。
“我做生意真的比他們要強悍,李亞偉和萬夏啊,我覺得李亞偉的心態很好,不疾不徐的那種,包括他對他的手下小張那種(態度)”,張小波在接受楊黎采訪時很真誠地進行了自我反省,“我這個人對人要求高,性格比較急,那這個性格還是沒有轉變。有時候對人家是不近情理的要求,當然是自己感覺要不近情理了就想拉回來,應該對人好一點,就這種時候比較多,性格不斷跳越。”
張小波在個人性情上的反省固然可貴,但他操作《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等超級暢銷書時更多地帶有投機成分,在賺取巨額財富時,他對提升中國出版品質和凈化本土商業倫理的實質性貢獻其實并不大——盡管他像萬夏一樣會從經濟上援助昔日詩友或新晉詩人。
《燦爛》全書洋溢著楊黎對物質享受無可厚非的強調和訴求,但那些對他坐出租車、被萬夏在凱賓斯基請喝80元一杯(2001年的價格)的純正德國啤酒等細節的過分強調,反而顯現了詩人在經濟上不獨立,通過“茍富貴,毋相忘”的江湖俠義而過分依賴他人的一面。《燦爛》中不止一處出現了萬夏、楊黎等14位同齡詩人2002年兒童節集體過40歲生日時的照片,我很擔心這場小規模狂歡全由萬夏一人埋單。即使是萬夏心甘情愿,詩人本應比其他人更自尊更獨立,更應知道“我們不能是寄生蟲”(楊黎語)的承諾有多重!
《燦爛》楊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58元。
(作者單位:《中國青年報》評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