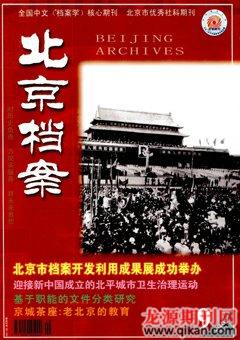從志愿軍戰俘到崆峒高僧
吉 路
搜索“崆峒”一詞,無意間在甘肅省靜寧縣民政局的網上看到《從志愿軍戰俘到崆峒高僧》(魏柏樹/《駝鈴》一九九九年四月號)。這篇紀實文學是在十年前發表的,看得出作者費了很大功夫采訪,許多細節做了一定的核實,力求還原現場,很是難能可貴。此文不失為對史料的一種補救,有助于我們了解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自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到現在已整整三十年過去。期間,京臺兩地的人員往來從無到有、從單向到雙向、從民間到政黨、到官方,如今是遍及多領域、多層次,交流與合作絡繹不絕。時光不會倒轉,但臺灣工作者、文史工作者、檔案工作者或許都有責任在前進中回望歷史,為后人留下研究相關文史、檔案的實證和佐證。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臺灣當局宣布解除在島內實行了三十八年的戒嚴體制。過了五十天,我和同事第一次接待繞道日本回來的在臺志愿軍戰俘,他就是張旗,同時,這也是我們第一次接待臺灣僧人,他就是釋會善。
九月五日上午,張旗從北京站下了火車。出站后,他向一位出租車司機打聽,那位師傅直接把他送到北京市臺灣同胞接待辦公室問訊處。
接到信息,小彭帶我趕了過去。見到穿著灰藍色袈裟的客人,我們愣住,一下子不知道怎么稱呼好,還在猶豫是不是稱“師父”,他先爽快地說:“我叫張旗。”我們趕緊順著稱呼他“張先生”,他反而說:“還是叫我‘張旗比較好。”
張旗把身份證件給我們看,是中國駐日使館簽發的旅行證,寫著“持此證者系臺灣同胞”(大意)等字樣。他自述原名叫張琦,是甘肅人,當過和尚、鄉長,后來又當了和尚。一九五一年參加志愿軍、赴朝參戰,受傷,被俘,進戰俘營,一九五四年被強迫去了臺灣。在臺灣,住過監獄,當過苦工,最后又當了和尚,云游四方。他一口氣講完曲折的人生,我們聽得都懵了。
下午,我和小彭回單位后迅速報告接待情況,主任與有關方面聯系、協調之后,由中旅北京分社臺胞接待部負責安排張旗的食宿。經理李自衛親自送張旗在僑園飯店住下。
張旗住在僑園時,我陪主任去看望,同他交談。他非常健談,非常激動,談了幾個小時還停不下來。談到他在巨濟島戰俘營的苦難,他先把袖子挽起,后又把領襟拉下,揭開他覺得最恥辱的部分(“反共”內容的刺青)給我們看。看著他手臂、后背上被暴力刻下的字和他經年刮磨留下的傷疤,真是“一字一淚,如泣如訴,令人不忍卒讀”。
我們按照與他交談的內容以及他所希望的,如實向上簡報了他有關在臺志愿軍戰俘境遇和心路的反映。
張旗是兩萬多去臺志愿軍戰俘中的一員,他反映的情況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們交談后不到兩個月,即十一月二日,臺灣當局有限度地開放島內民眾赴大陸探親。臺灣老兵如潮水般向大陸涌來,一如輿評說的:他們“一天也不愿再多等”,只是多數的志愿軍戰俘,還缺少張旗那樣的勇氣,他們寧愿先等一等、看一看再說,強忍住對父母妻兒的無盡思念。他們內心深處最大的猶豫和顧慮,不能不說就是身上的“字”,一些人最終還是選擇了走進美容院去“洗字”,盡管那很痛,也很貴。
張旗是拜觀音菩薩、皈依凈土宗的。回到故鄉,中共甘肅省委統戰部、對臺辦根據張旗本人的意愿,將他安置在天水市崆峒山,由政府每月發給生活費用。
每每見到來京的甘肅臺辦同事,我們總會問到張旗,因為見過他后都有幾分牽掛。我們知道,省里對他還是盡力照顧的,他很信任省臺辦的一位老主任,有事沒事都會找他,和他聊上一陣子。
很快,二十年過去了。在二〇〇七年二月十四日的《平涼日報》上,有以《甘肅省臺辦領導看望慰問臺胞臺屬》為標題的一條消息,報道說:“在新春佳節即將來臨之際,甘肅省委臺灣工作辦公室主任、省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趙少智一行四人,在平涼市、崆峒區臺辦負責同志的陪同下,帶著慰問金和禮品登門看望了平涼市臺灣籍人士林愛玉女士、定居臺胞王清海、張旗老人及其家屬,向他們送上了黨和政府的關懷與問候。”這條消息傳達的意思就是“張旗還好”。
張旗給過我一張名片,是油印的那種,上面極其簡單地寫著“觀音閣 主持釋會善 平涼市崆峒山”,沒有聯系電話,沒有通信郵編。
崆峒山,看過金庸武俠小說的,都會對它神往。資料介紹它位于甘肅省平涼市西十一公里處,屬六盤山的支脈,佛、道、儒三教并存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
在崆峒山管理局信息中心的網頁,官方發布有關資料如是說:“觀音閣,舊址在月石峽路口東側。元代創建,清咸豐年間廢。一九九七年,由臺灣歸來和尚釋會善多方募資復建,大殿三楹、廂房六間。” 盡管是寥寥數語,其中有多少不為人知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