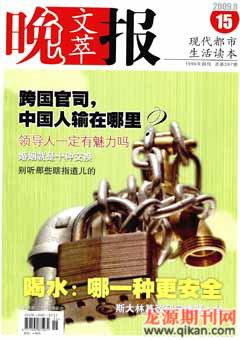追憶
葉延濱
其實(shí)就是一列火車從身后開過去了。
先是聲音,漸漸放大的車輪與軌道的撞擊聲,好像一下又一下地敲打著胸脯,從“咕咚咕咚”變成“轟隆轟隆”。這聲音在敲打大地的胸脯之前,曾叩打過一根根整齊排放的枕木。枕木是一個(gè)時(shí)代的士兵,真是士兵!它們原先不會(huì)想到后半生要躺著,躺在兩條冰冷的鋼軌下,它們原本是站立在大山上的,是一群山野村夫,自由自在地活著。有太陽照耀著它們,讓它們伸展枝葉,“好好學(xué)習(xí),天天向上”。誰說的這八個(gè)字?不管是誰,這句話對于陽光下的森林來說都是美好的祝愿。有快樂的成長,當(dāng)然也有快活的回憶。
什么時(shí)候有了鄉(xiāng)愁?就是離開的那一天,那一天!那一天有人夸自己了:“真棒!”那人用手拍打著樹干,仰著頭圍著自己轉(zhuǎn)了一圈,然后,搓著兩只手,還往手心里吐了點(diǎn)唾沫,舉起一只呼呼叫的機(jī)器,靠近了樹干,吱!……以后,以后就被巨大的震動(dòng)喚醒了,醒了,卻動(dòng)彈不得,兩條巨大的鋼軌壓在身上,幾根像鷹爪一樣的鋼釘抓緊身體,讓一個(gè)個(gè)呼嘯的巨大的鋼輪從身上飛快地壓過去,壓過去,再壓過去,把所有關(guān)于樹和大山的形象壓成記憶,把枕木這個(gè)新身份壓進(jìn)年輪,把關(guān)于站立的所有習(xí)慣壓成回憶,把躺著,一動(dòng)不動(dòng)地躺著,變成命定的生存方式。當(dāng)然,枯燥而艱辛的生活開始了,作為補(bǔ)償,常聽到這樣的話,“社會(huì)前進(jìn)的戰(zhàn)士”“時(shí)代的尖兵”“承擔(dān)起時(shí)代的重負(fù)”等等。這些話,開始是聽不懂的,不僅枕木聽不懂,我們不也一樣嗎?時(shí)代是什么?誰見過?什么模樣?然而聽多了,也就覺得你知道“時(shí)代”是誰了?還有什么“社會(huì)責(zé)任”“歷史使命”,好像我們都知道說的是什么,但真的知道嗎?天知道!
好了,這個(gè)世界少了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森林里少了那些參天大樹。人們假裝忘記了這一切,因?yàn)樗鼈円呀?jīng)像陣亡的士兵,一排排地躺在鐵路鋼軌下。人們知道它們在想什么嗎?它們在想曾經(jīng)站立的那些歲月。
烈士總應(yīng)該得到光榮,枕木就是烈士,是森林死去的兒子們工業(yè)革命的烈士,枕木!人類用暴力掠奪森林,將那些撐起天空的森林王子變成工業(yè)的奴隸,剝掉上帝賦予它們的美麗外衣,截?cái)嗯麙熘G葉的手臂,然后用工廠的法則,將它們交得彼此一模一樣。最后,再用鉻鐵烙上不同的編號(hào),一串長長的數(shù)字告訴枕木:“記好了!你不是第一個(gè)殉難者。”事情就這樣開始了,就這樣從暴行變成了榮耀,就這樣變得理所當(dāng)然,變得讓枕木也認(rèn)為這就是“棟梁之材”的用武之地。鐵路一寸寸地向前延伸,一棵棵的樹就倒在路基上,讓整個(gè)路基成為森林的“士兵公墓”。鐵路像蛛網(wǎng)一樣充滿這個(gè)小小的世界,這個(gè)世界也充滿了森林的哀傷和痛楚。一年又一年就這么過去了,一次又一次那轟隆轟隆的時(shí)代最強(qiáng)音,驚醒了枕木們的夢,夢里有不死的鄉(xiāng)愁。
這一天,又有一列火車開過來了,沒有什么新奇之處,只是,列車運(yùn)來的不再是枕木,而是水泥和鋼筋鑄成的“水泥枕木”——屠殺中止了……我這么想。這一天,我離開了秦嶺深處的這個(gè)小站,我從這個(gè)車站的站臺(tái)上,看到了那列運(yùn)送“水泥枕木”的貨車。那年是1977年,那個(gè)車站叫橫現(xiàn)河,我在車站旁的一家工廠里工作了4年。那天,我離開它,調(diào)回四川的母親身邊。哎,枕木回不去了,我向鋼軌下的最后躺成一排的士兵們告別,轉(zhuǎn)身登上列車,消失在秦嶺的云霧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