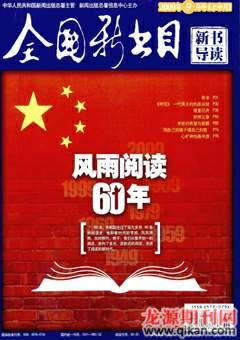書情舊夢鄧云鄉
侯 軍
仿佛還在昨天,鄧云鄉先生帶著我去上海福州路舊書坊淘書;仿佛還在昨夜,我在鄧公的“水流云在書室”的淡淡書香里安眠。孰料逝水無情,驀然回首卻發現,鄧公仙逝已經10年了。
一直想寫寫我與鄧公的書緣,卻遲遲未敢動筆,原因其實很簡單,這個話題在我的心中實在太沉重了,以致于我不敢輕易去觸碰它。
我與鄧公結緣于書。那是在1993年夏天,我所供職的報社要開辦一個綜合文藝副刊,定名為《雅園》,顧名思義,這個版面的內容主要是刊發中國傳統文化中與“文人雅事”相關的文字。在商量約稿時,責任編輯畢敏提出想請鄧云鄉先生給我們撰稿,我當即表示贊成。此前,我讀過鄧公的一本小書叫《草木蟲魚》,知道這位民俗學家具有旁人難以企及的本事,就是把原本很民間的東西寫得很雅致,把原本很淺顯的東西寫得很精深。這是需要大學問大視野大手筆才能辦到的事情。若能請到鄧公這樣的重量級作者給我們撰稿,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是當時我們都沒接觸過鄧云鄉先生,不知道他肯不肯為我們這樣一個剛剛創刊的小副刊屈尊賜稿?我們商定,先由畢敏寫封約稿信投石問路。不想,鄧公很快就寫來回信答應了,這使我們喜出望外。
我與鄧公是在文字交往了半年之后才見面的。從此,魚雁往還不斷,遂成忘年之交。在此期間,鄧公每有新書出版,必先寄贈給我,每本書的扉頁上均以從不變樣的格式簽名,且在名下撳一精巧圖章。每次寄書還必附一封短箋,那一筆清秀瀟灑的鋼筆字以及充滿書卷氣的行文,總是令我如沐春風,依稀看到中國傳統文人那種氣定神閑的優雅情致。在當今浮躁蹇促的世風中,這種情趣盎然的贈書方式本身,就如同是山陰道上的空谷足音。
陸陸續續的,我得到鄧公十幾冊簽名本,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先在我們的副刊上首發的。我每每在書中發現這些熟悉的文字,都會感到由衷的欣喜并會心一笑。鄧公當時非常勤奮,真可謂文思泉涌,新作迭出,《水流云在雜稿》、《文化古城舊事》、《水流云在瑣語》、《增補燕京鄉土記》(上下卷)、《春雨青燈漫錄》、《黃葉譚風》等等,都是在那段時間問世的。據我所知,鄧公不習電腦,所有稿件都是手抄。作為編輯,我深知如此浩繁的文字量,要一筆筆一頁頁寫出來,那要耗費多少心血和精力啊!鄧公畢竟是七旬老人了,何堪如此重負?因此,每回與他通電話,我都會發自內心地勸導老人家放慢節奏,注意節勞,不要給自己規定寫作任務。我還特別告訴他,我從來不允許編輯們向他催稿,以免給老人造成壓力。但是,鄧公卻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回答——有一次,他在電話中很認真地對我說,你不要說是編輯催稿給了我壓力,我的壓力不是來自他們,是來自我自己,是我自己催著自己要趕緊寫,還要多多寫,為什么?因為我耽誤不起!你們還年輕,你們哪里知道我們當年那種有話不能說、有筆無處寫的痛苦啊!你算一算,反右,文革,我們耽誤了多少時間啦……
我攥著電話聽筒,默然良久。鄧公少讀群書,懷抱利器,本有兼濟天下之志,但卻生逢亂世,早年多經戰亂,顛沛流離。此后又在極左風潮盛行的幾十年中,雖風華正茂卻無用武之地。只有到了改革開放之后,他才像被發現的出土文物一樣,重新為學界所重,他的才思與妙筆也才得以像火山爆發一般,噴發出多姿多彩的錦繡華章。是的,對于鄧公來說,八九十年代堪稱是他文化生命的浴火再生和鳳凰涅,他像一匹久困樊籠的駿驥,一旦掙脫韁索,立即縱橫馳騁,騰驤于中華文化的廣闊天宇之間——鄧公本名云驤,而后來被他改為云鄉,一字之易,或許正折射出鄧公坎坷的人生境遇對其心態的深刻影響。
我與鄧公的書緣,不光體現在互相贈書上,更令我深感幸運的是,鄧公還曾帶著我專門去上海福州路的舊書店淘書。那天,下著小雨,我們一老一少興致勃勃地來到福州路,鄧公對這一帶是熟門熟路,很多店員見到他都非常客氣地打招呼,有幾位老者還要湊上來跟他竊竊私語一番。可見,鄧公在這個領域是絕對的“大腕兒”,我跟在鄧公的身后,一邊看書,一邊聽鄧公給我講在上海舊書店淘書的門道——鄧公告訴我,上海是三四十年代的出版業中心,你要挑選那個時期的圖書,非到上海來不可;還有,上海還是五四新文學的主要集散地,出版的新文學書籍比北京、廣州都要多,你要淘這方面的書籍,也要到上海來;此外,上海的線裝古籍也不少,這是因為周邊的江浙一帶,都是富庶的魚米之鄉,讀書的風氣自古就很濃厚,古舊書的流通量自然是其他地方所沒法相比的,而這些古籍善本一般都要拿到上海這個大碼頭來交易,所以,時常能在這里遇到意外的驚喜……
我們那天在福州路遇到的意外驚喜,是淘到了一冊由江陰謝初霆編撰的《漢熹平石經碑錄》稿本。這書是我在一個角落里發現的,粗粗一翻,發現有些頁眉頁腳處,寫著些蠅頭小楷異常精美,便拿給鄧公審看。鄧公看過也覺得這書稿單憑這一筆小楷,就值得收藏。更何況書中所講的漢石經,乃是印刷術發明前,中華文化典籍傳承發展的最重要途徑。這樣一部很有學術性的手稿,不知什么原因,今日竟流落到書肆冷攤了。鄧公說,你如果有興趣,還可以繼續研究這門學問。要知道,石經的研究原本是一門顯學,顧炎武、萬斯同都寫過《石經考》。只是近代以來,西學興起了,這門學問才冷了下來。我見鄧公如此看重這個稿本,當即不講價錢收入囊中。我見鄧公面露喜色,不禁自忖,鄧公應該不只是因為幫我淘到好書而高興吧,他老人家心里或許還有更深一層的欣慰:畢竟這些老祖宗的學問,又有年輕一輩關注并且喜歡了,這當中不正蘊含著“薪盡火傳”的象征意味么!
回到鄧公的“水流云在書室”,我們都有些興奮。吃過晚飯,鄧公把那稿本要了去,說是再仔細研究一下。我當然很樂意請老人家多過過目。那天晚上,我發現鄧公的房間一直亮著燈,直至深夜時分。
第二天一大早,鄧公就起床了。他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間里,指著攤在桌面上的那冊書稿,說他昨夜細讀了一下,覺得這位作者很不簡單,不光字寫得漂亮,學問也做得扎實,對漢代熹平石經殘石很有研究,對殘石上殘存的每一個字,都逐字逐句做出了精審的校訂和考證。“你瞧,我剛才已經把我的‘讀書心得給你寫在卷尾了,供你回去讀書時參考。”我連忙俯過身去觀看,只見在書稿的最后一頁,鄧公以那特有的清秀瀟灑的小楷行書,為我題寫了這樣一段跋語:“侯軍兄自深圳來滬,聯袂過福州路書坊,以五百番購得此冊。歸后于燈下細閱,似漢石經制版付印之剪貼校正清樣,以線裝《辭源》零本翻轉面粘貼成冊者,應為七十年前之舊物也,彌足可珍。惜不知編者江陰謝初霆生平,唯其所注之蠅頭小楷舒展挺秀,一筆不茍,足見前輩學人功力及嚴謹之態度。晴窗展對,景仰久之。爰志數語于卷末。乙亥重陽于水流云在延吉新屋南窗下。蝠堂鄧云鄉。”下欽兩枚小小私印,跋前也蓋上一枚迎首印,為鄧公常用的“紅樓”二字。
這冊手稿不啻是我此次滬上之行的最大收獲。然而遺憾的是,得到這冊珍貴的稿本已經十余年了,雖然也曾數度研讀,且又購回幾冊與漢代石經有關的古籍(如嘉定瞿中溶《漢石經考異補正》),但真正如鄧公所期望的投身于對這卷稿本的研究,卻始終未能起步。一是因工作繁忙,無暇他顧,二是這門學問確實艱深,我初入門徑,難以上手。如今,捧讀鄧公十多年前的跋語,字跡猶新,聲猶在耳,慨嘆書存人杳,不禁心生愧怍,悵然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