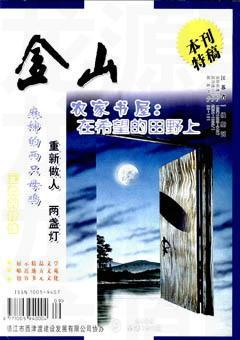小山樓前思張祜
古渡渺千秋
我似乎突然感到,張祜就在眼前,他那雙平和遠眺的眼睛卻讓人震撼,正是那種穿透歷史的目光。
我又來了,在這滿天春風的日子。說不清自己是第幾次來到這座硬山式二層傳統建筑前,說不清我是多少代景仰這位先賢的后世子孫,更說不清我是第幾個到張祜小山樓來感受詩人心靈的學子。
一、
我是來看張祜的。
在我的心目中,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小山樓佇立在滾滾江水邊和花草與修竹掩映的小街一側,兀立于如煙波一般浩渺的文化時空里;在我的心目中,在許多人的心目中,小山樓只有張祜屹立在這里,屹立在歷史的蒼穹之下。
江上的霞暉剛剛散去,張祜先生漫步爬上了小山樓,幾分沉思,幾分惆悵。他推開樓上雕花的窗子,凝望萬里長江,寫下了佳作《題金陵渡》:“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兩三星火是瓜洲。”這首詩首句交待地點、方位,次句寫事明情。三、四句放筆寫遠望,融情人景,夜色之迷離與行人之旅愁交織一片;落潮濤動,旅愁難眠,夜江遼闊,靜夜傷感。天上一輪孤冷的斜月,凄凄地給江面罩上了一層迷蒙的色調。遠方那點點燈光是那樣吸引人,是低垂天幕上的星光浸入江中幻化為燈光漁火,還是江中的燈光漁火幻化成天上的星光?水天一片,不復分辨,這是一幅情、事、景水乳交融的夜江遠望圖。許多學者和游客將這首詩與唐詩人張繼的《楓橋夜泊》詩相媲美,稱其“同寫客愁,各臻妙境”。
是的,張祜雖然是路過西津渡,但是。他把自己最好的創作靈感留在了小山樓,他把自己最有影響力的作品留在了小山樓,他把憂國憂民的人生境界和生命表現留在了小山樓。
不曾有過干戈擾攘的著名戰事,不曾有過或實或虛的傳說故事,小山樓的悠遠,小山樓的名望,是靠文化構筑起來的。說得具體些,是在1140多年前的那個風雨如磐的日子,一個官場失意、生活困苦的人來到了這里,在這里觸景生情,留下了幾行文字以后,就把這座小山樓高高地墊起,讓世人刮目相看了。
如今,不聞低吟高詠之聲,橫笛漫吹的悠揚也已漸漸遠去,但有張祜佇立在這里的歷史。無論是秋色中的金陵渡,還是春陽下的小山樓,讀到《題金陵渡》這首詩句,都能讓人遐想聯翩。
二、
不過,9年前那個和煦的秋日,我頭一回來到了小山樓,歷史上的小山樓已沒有了蹤跡,這是復建的一處歷史遺跡。我來到了這里,并不是來看張祜的,只知道他曾在這里寫過不朽的華章,只是為體驗他詩文里所描述的那種古樸,飄渺的江水、新月、漁火、星光的妙境。
還有,一個來自蘇北的小伙子,在這座臨江小城感受到了溫和的江風和陽光,感受到了江天一色的茫茫大地。并且,還偶然遇到一位少女穿著平口布鞋,在我們與她迎面而過時,她竟投給我們一臉清純的微笑,使我感受到整個西津渡街的殷殷笑容。
所以我來了。同學特意為我借了部照相機,我們一邊欣賞這千年流傳的建筑奇葩,一邊和小山樓親密接觸,用攝影把我們的身影和建筑融為一體。
雖然那時我沒有把千年文化的氣息與現代小街的秋意融合在一起,也無意于古街上綠樹亂磚墻襯映的瑰麗典雅,更領略不到偉大文學創造的莊嚴,但我還能夠隱隱約約地意識到,是因為有了張祜、蘇東坡、王安石、孟浩然……才有了現在這個歷史的小山樓,才有了這個文化的西津渡街。
三、
那是一個讓人永遠無法悟透的文化話題,本是一場人生游戲,卻導致了一次生命意義的至高升華。在我們今天為唐詩、宋詞、唐宋散文這些巨大文化財富而備感驕傲的同時,只能慶幸當年的西津渡,不是今天人們印象中的這座大江似鏈、山水如繪的美麗街區。否則,上蒼就不會將那次重大的文學孵化選定在這里。
西津渡有幸。當年,這處在人們看來十分偏僻的蠻夷之地,卻意外地迎來了才華蓋世的詩人;加上它四通八達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還有那數不清的詩人、詞人在這里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飄渺的夜景、迷人的新月、隱約的漁火,使得詩人才情大發,使得這座平淡無奇的小山樓得以崢嶸出世,使千萬年安然流淌的江水在文字的畫卷中顯得潮落夜漲,江上的漁火、天上的新月晝夜更替,使得這座小山樓負起了一次重大的文化使命。
詩人有幸。作為生活游戲的主角,張祜有心報國,然而南北奔走30余年,投詩求薦,終未獲官。使他只好“幽棲日無事,痛飲讀離騷”、“千年狂走酒,一生癖緣詩”。是西津渡街淳樸的民風撫慰了他遭受過重創的心靈,是小山樓依山面江的壯麗景色激發了他的才情。盡管人生厄運和功名未成難免使他感傷,但他得以在這個小小平臺上一覽遼闊江山,走向情動千古的高遠之境,以江水凄情卓然獨步,為中國文化史寫下了精妙的一頁。
古往今來,每一個追求文化高度的漢語言書寫者,無不苦思冥索地探尋過方塊漢字的最佳組合之奧秘。而當年詩人站在小山樓上遠眺,借著如紗的月光,隨之揮毫寫下了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曠世之作。那樣的夜晚,詩人忘卻了身處逆境的狀況,在這夜闌人靜之時,一會佇立窗頭默吟,一會秉燭研磨,其神情之從容,其筆鋒之流暢,猶如天授。
天地廣袤,山水無數,為何西津渡能夠誕生出震古爍今的文學作品,造就出一代文化奇人,這里的山水蘊藏著怎樣的靈性,張祜先生曾在這里受到了怎樣的靈感支配,才完成那樣絕妙的文字組合?這種問題也許有無限玄虛,但并不是一個可笑的話題,否則就不會有那么多學人向往西津渡,向往小山樓。現代文學家余秋雨先生曾三次來到西津渡,并在小山樓前接受鎮江電視臺記者訪問,樓上“金陵渡”的牌匾也是先生留下的墨寶。這些學者除了游覽名勝,還希望從這里尋訪到什么,感悟到什么。或許,這就是文化的魅力所在,這就是文化名勝對尋訪者的誘惑所在。
優秀的文化成果,幾乎不可刻意培植。張祜失意路過此地,本是歷史對道義和文化的一次暴虐踐踏,本是命運對他的一次極不負責任的安排,但他卻在這種艱困和屈辱的境遇中,實現了一次被歷史大書其功的文化突破。驚世之作如此出現,除了神靈相助之功,似乎沒有誰能夠作出符合現實規律、并且令人信服的解答。
四、
江水依舊靜靜地奔涌東去。小山樓依舊靜靜地守望著已經遠離的大江。只是那一塊塊略有殘損的包括《金陵津渡》等古詩詞內容在內的書畫碑刻,被嵌入了小山樓背后的長廊墻上,只是那樓旁的院內新植了翠綠的蕉葉和修竹,還有樓東西兩旁各建了一處亭子,一切是那么的古樸滄桑、平靜祥和。
可我每次來西津渡街,還是要到小山樓一游,盡管我沒有能力來破解杰出文化的誕生之謎,連張祜路過西津渡的經歷也缺乏研究,甚至不清楚自己一次次反復而來有什么實際意義。
然而,每次前來,我總要站在小山樓前久久凝望,眼前浮現出當年張祜夜宿小山樓的情景:看他峨冠博帶的衣飾,看他并不偉岸的身軀,看他自然平靜的表情,看他穿透歲月的眼神。文化偉人生榮死衰,不像帝王將相那樣,活著沒有人敢靠近,死后沒有人愿意靠近。一代代后人讀著先賢的作品,總想象他們還活著,不管他們離自己多么遙遠。
這回,我再一次來到了小山樓。再一次屏住氣息仰望,再一次留影紀念。可是我似乎突然感到,張祜就在眼前,他那雙平和遠眺的眼睛卻讓人震撼。正是那種穿透歷史的目光。原來,自己無法走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