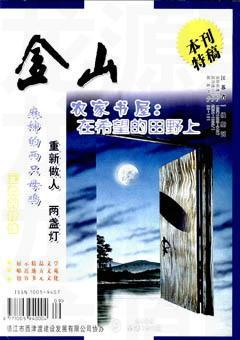請聽題:婺源的油菜花為什么這樣黃?
周志良
習(xí)慣和厭倦了一種行走,就應(yīng)該和渴望另一種行走。來自城市的報告總是想發(fā)散一種鄉(xiāng)村情懷,醉心于清山不斷綠水長流的素面朝天,醉心于黑白村莊粉壁黛瓦的簡明古樸。比如江西的婺源,比如婺源的江灣,一個用淙淙水聲彈奏著無數(shù)傳說的迷人地方,在三月和四月,她用油菜花的盛開招呼天下行者,說,來吧來吧來吧來嗎?
來!我們已經(jīng)春醒,直立的軀體飽滿有力,像花房一樣的激情蕩漾在風(fēng)里,天地喲,油菜花的魂魄是在婺源的大山里么?是在中國最美的鄉(xiāng)村里么?誘惑之妖始終揮之不去,只有一種選擇,學(xué)習(xí)實踐去!看看婺源的山村為什么這樣美名傳揚,婺源的油菜花為什么這樣騰達飛黃。
現(xiàn)代化的大巴接過四月的貼子上路,豪華地沿著古老的山腳奔馳,車里的我們一路撒著歡地歌唱,與“盤踞徽饒三百里,平分吳楚兩源頭”的大彰山交臂而過,還未到目的地。就遠遠地聞到了來自婺源的體香。
婺源的翠秀是豐滿而另類的。另類的令人驚詫;它的綠意是那么養(yǎng)眼,又那么養(yǎng)心。婺源雖說由八分半山組成,但婺源溫潤的脾氣養(yǎng)育了山山翠色,峰峰秀發(fā)。余下的一分半便是水、坡和很金貴的平地了,婺源被30多條知名江河水與千百條無名小溪水滋潤著,那是已經(jīng)不多見的清明的地表水源,置身其間,使我一下子回到了小時候的水環(huán)境中,那鷗鷺、牛羊與我同飲的一灣純凈水,如夢一樣的波瀾,起伏著藍天白云和童年的無數(shù)奇問。
自然山水一定要有文化的提升才會產(chǎn)生靈氣,否則,大活人行走在原始森林,就仿佛一群野獸。這就是為什么當人們看到荒水上一座小橋,深山里雞鳴人家時會產(chǎn)生親切愉悅感的原因。婺源,那真是升值于自然的人居故鄉(xiāng),叢林野趣中一處處炊煙曾經(jīng)迷戀的年、月、日。
而李坑是一個鄉(xiāng)村經(jīng)典。不遠,從婺源縣城向東北行數(shù)十里,一片秀山環(huán)抱,綠水纏繞著的260多戶古民居就是。這一天,在費翔《故鄉(xiāng)的云》下,正淅瀝著卓依婷《三月里的小雨》。我們撐起剛剛買的十元人民幣一把的折疊傘,走進大夫第就誦讀起春藹堂上的一副對聯(lián):及時小雨敷桐葉,借得春蔭護海棠。村中存留著一座國內(nèi)罕見的“申明亭”,這是宋元以降國家權(quán)力下移后鄉(xiāng)村治理受到重視的一個見證物,它以一種高貴傾聽著歷史的言說,讓是是非非自定乾坤;而高高的馬頭墻、兩澗響滿歡暢的溪流和石橋、石板路也已載不動當年徽商官宦的深宅豪門,這里已被另一種文化替代,夠格的古老典雅在洪流般的游客心中先供奉起來,然后慢慢品味。
歷史可推溯到有唐一代以前的江灣鎮(zhèn),清麗秀美不讓左村右坑,而古街古宅古井透出的歷史文化氣息,因久遠而顯厚重。在這個經(jīng)濟繁華、名人輩出的婺北重鎮(zhèn),最感興趣的是發(fā)現(xiàn)了婺源的江氏家族原來是齊梁帝故鄉(xiāng)——丹陽東城里蕭氏的后裔。帝王將相,學(xué)人良醫(yī),蕭江氏一脈果然了得!我在想,婺源與丹陽,應(yīng)結(jié)對發(fā)展,造福人民。當肅立在江上青烈士的石碑前,一抹霞光正與白云齊飛。真正心懷天下救濟蒼生,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用油菜花獨釣天下客,不失為婺源人的文化經(jīng)濟新理念。當我們用幾近唯美的詞語贊美婺源的秀美山水而似乎流連忘返時,是否真的讀懂了一種生活狀態(tài)的全部。以往,數(shù)千年歲月,深深的大山是閉塞的同義詞,一塊坡地,幾戶人家,荒村野老,常常“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今天,聰明的婺源人為什么要讓這里的油菜花開出一片金黃,黃得讓我們這些從小就枕著油菜花長大的飲食男女愿意掏錢到這兒來一睹油菜花黃的盛開?因為婺源人要沖破一種包圍,一種陶醉,要與新經(jīng)濟接軌,與和諧小康擁抱。
沒有看到油菜花,卻看到了婺源人超越粉墻黛瓦的新觀念。此刻,站在深宅老院的門楣前,脊梁會挺得很直,雄糾糾一步就往來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