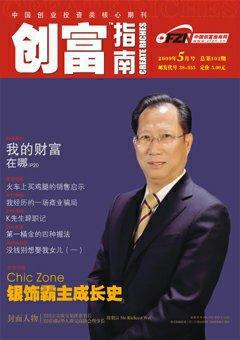深圳山寨江湖的興與衰
濟 世
在深圳華強北路某高層寫字樓28樓,一片熱火朝天,員工們有的在接聽業務電話,有的在裝配手機部件,有的正埋頭調試手機……
這里的老板馬先生剛送走了一批經銷商后,便坐回了大班椅。
老馬從不和客戶交換自己的名片,手機是他聯系業務的唯一工具,僅是和對方互留手機號碼。
老馬的警惕與小心有著邏輯的必然——在深圳從事手機生意逾六年的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沒有獲得國家頒發的手機牌照,他運作的手機未經過入網檢測。但這些都沒有妨礙他“制造”的手機,最終同諾基亞們一樣,在中國這個世界最龐大的手機消費市場恣意伸展。
悄然之間,他“制造”的手機被冠以一個別樣的名字——山寨機。
憑借低廉的價格和某些匪夷所思的創新,山寨機在廣大三四級市場迅速“躥紅”,并對傳統的國產品牌手機構成直接沖擊——近年,在一些國產品牌機日顯頹勢的年報上,“山寨機泛濫”均被視為其銷量下滑的主要原因。山寨機產業也因此備受指責,甚至引發了以政府主導的針對山寨機的嚴打行動。
“與品牌軍相比,我們幾乎是在夾縫中生存。”老馬感嘆,但這并不妨礙他比品牌機“混得更好”——在多年的“山寨生涯”中,老馬積累了頗讓旁人羨慕的個人財富,盡管他還算不上是山寨江湖中的大佬。
深圳市手機協會副秘書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山寨機的存在有著自身的產業邏輯,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市場的切實需求。”這亦是老馬們得以“笑傲江湖”的深層原因。
暴利催生“山寨機”橫空出世
在中國手機產業起步階段,國產品牌手機可謂風光無限,一款國產手機的廠商利潤,好的能做到千元以上。據TCL通訊一位負責市場的人士透露。當年,TCL通訊主營業務收入73.92億元,同比增長21.39%,凈利潤更是高達18.90億元。
“2003年前后的手機行業,處在暴利時代。”當時,還在從事某國產品牌經銷商的老馬憶述,“整個產業鏈都充斥著暴利,當時僅TCL的省包商,一年利潤過億元的,不下十個”。
也正是在這一年10月,國產品牌機的市場份額達到60%——首度超過外資品牌,成為市場的主宰。此時,整個市場充斥著狂熱,中國作為制造大國的產能動力,再度被空前激發。一時間傳統電話機廠商、數碼廠家紛紛轉型手機生產。
“還有不少品牌廠家的研發、銷售人員合伙出來做手機的。”原來在某國產品牌廠商任職的人士透露,當時私底下流傳一種說法,“有本事的出來單干,沒本事的才在廠里呆著”。
另一個更為龐大的群體來自經銷商隊伍。通過手機銷售積累大量財富的經銷商,開始向更高的產業利潤進軍。
在“由商轉廠”的大軍中,老馬就是其中之一。一個典型的公司架構是:“幾個國產品牌廠家出來的技術人員、其他電子行業從業者和手機經銷商湊成一家公司。因為經銷商對市場渠道最為把穩,往往是項目的出資方。”
由于珠三角地區長期以來形成的電子制造產業鏈的基礎,讓其責無旁貸的延續到手機制造業的輝煌。在華強北,可以采購到生產一款手機所需要的所有配件。相比較品牌廠商,這類手機廠商的產業分工更為細化。
就是在這個時候,此前曾制約手機產業普及發展的技術門檻也不復存在。2004年,來自聯發科的手機解決方案在這些手機廠商中規模應用,大大降低了手機行業的制造門檻。在此之前,穩定而廉價的芯片供應,一直是這個“江湖”的瓶頸——無論是2000年初使用較多的wavecom模塊,還是2003年左右的ADI芯片,其價格和穩定性均缺乏競爭力。也正是因為如此,2004年,被視為“山寨機元年”。
自2003年起,在東莞、寶安一帶陸續建立的手機代工廠就超過百家,年產能超過千萬部。而在產業上游的方案公司,也不下200家。從理論上說,在深圳你想要玩手機,唯一需要準備的就是籌集資金。
“山寨機”的繁榮與暴利神話
“幾乎每一天,你都能看到有新人進入手機行業。”2005年前后的“手機江湖”是“最瘋狂的年代。”
一個細微的變化是,投身手機行業的,已經不局限在手機產業鏈上的從業者,很多與電子產業毫不相干的人,也瘋狂涌入。不少從事礦業、房地產、甚至服裝行業的商人,都開始將現有行業積攢的“熱錢”,投資于手機業。
據多位深圳手機界業內人士估計,2005年初,深圳及周邊地區大小“山寨機”廠商大約在200到300家,到2006年陡然擴容到至少上千家。
與品牌手機相比,山寨機在運作方式上表現出超強的靈活性。由于分工細化,一款機型從立項到開模,再到生產,最快15天就搞定。相比之下,部分國產品牌廠商僅立項環節,就需要半年。
而低廉的價格和多元化的功能,則成為山寨機迅速切入市場的利器。2005年,山寨機售價較品牌機約低40%。而雙卡雙待等“創新”功能率先在山寨機推出,更讓山寨機一度引領手機創新潮流。
在廣大三四級市場,山寨機迅速成為熱銷品。
與此相關,一條與傳統渠道并行的山寨機銷售渠道,也悄然成形。山寨機有別于品牌手機走正規國包商渠道,往往更傾向省包,甚至更下一級的地包商直接供貨。與此同時,憑借價格利器,山寨機也開始揚帆出海。在印度、中東、非洲等地,來自中國的山寨機很是暢銷。
“大約從2006年開始,在華強北一帶,你就能常常見到很多中東商人。”老馬告訴筆者,他們有的甚至干脆在深圳設置專門的辦事處,“都是來尋貨源,做手機生意的”。
瘋狂的背后,追逐的依舊是手機行業的高利潤,盡管逃脫不了電子產品利潤下滑的規律——2006年下半年山寨機單機利潤已跌至百元以下,但成幾何倍數的產量增長,依舊維持著手機行業的暴利神話。
2006年底至2007年上半年,山寨機出貨量每月高達1200萬部。以每部80元的利潤計算,每月山寨機總收入近10億元人民幣。
同樣在2007年初,老馬賺到了做手機生意以來最大的一筆錢。這也是老馬這樣的“山寨人”津津樂道的黃金時代。在華強北振興路的西餐廳,最常見的一個情景是,兩個相熟的手機商相視而笑:“兄弟,這個月又掙了一輛奔馳。”
“山寨機“的衰落與利潤崩盤
暴利時代總有終結的時日。只是山寨商人沒有想到,來得竟會那樣的快。
大約從2007年10月開始,老馬發現生意越來越不好做了。這個月在中國手機界發生了一件里程碑意義的大事件——沿襲多年的手機“牌照制”正式取消,手機生產改為“備案制”。
據老馬分析,手機銷量的下滑,與“牌照制”的取消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兩件事之間,并無因果關系”。
市場熱潮期,在逐利的沖動下,盲目的入市者不會去思考市場的承受程度。而市場的需求總歸是有限的。2007年年底山寨商人感到從未有過的庫存壓力,“頭一次意識到,手機也會賣不動”。
一度聲名顯赫的“山寨機王”中天通訊,由于市場下滑,2007年底,其生產幾乎陷于停滯。像以前那樣流傳的,某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因為某款機型熱銷,一夜之間就賺了千萬,甚至上億的神話,已經越來越少了。
2007年,山寨機產量大約在1億部到1.5億部之間。而來自國家統計的數據顯示,2007年國內手機的總銷量約1.49億部。由此可見,山寨機的產量,已大大超過了市場的承載能力極限。
在這種情況下,山寨機利潤崩盤,已成必然。時至2008年初,相當部分山寨機單機利潤僅在10元左右,有的甚至跌至5元。在此背景下,與當初瘋狂涌入相反,每天都有人抽身退出。
2008年11月,中天通訊董事長黃朝暉突然“失蹤”,一度享譽市場的“山寨機王”轟然坍塌,不亞如在山寨江湖投入了一枚炸彈。在投機主義盛行的手機行業,中天通訊的遭遇應不足為奇。
經歷了長達一年的行業寒冬,山寨機行業安靜了很多,而這個行業不再是暴利行業了。
自2008年下半年,“嗅覺”靈敏的山寨人紛紛開始尋覓新的商機——轉戰“山寨上網本”。這是個看上去頗似“藍海”的市場。他們希望在那里,能夠延續山寨機的神話。
在短短半年時間,僅深圳的山寨上網本廠家已過百家,其中不少是山寨機的轉投者。
這,是否又是另一次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