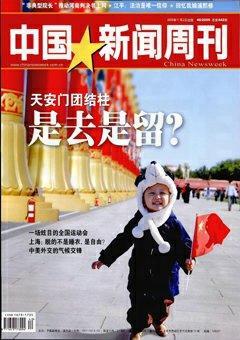回憶我娘浦熙修
袁冬林 羅雪揮 房一盟
“我能在逆境下像娘那樣面對人生嗎?被劃為右派后還會不會堅持入黨的信念?有人說,這是‘愚忠。但我理解娘,這不正說明那一代人對終生所追求的理想的執著嗎?”
浦熙修(1910~1970),民國時期著名女記者,先后供職于《新民報》、香港《文匯報》,采寫了不少當時轟動全國的進步報道。她認為,一個記者的職責是“監督社會走向進步方面去”,并身體力行,一直站在民主斗爭的前列。1946年,浦熙修在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中遭到國民黨特務毒打。1948年,國民黨以“共黨”嫌疑將她逮捕入獄。毛澤東曾稱她為“坐過班房的記者”,在參加開國大典時受到毛澤東的接見。1957年,浦熙修被錯劃為右派。罪狀包括“同羅隆基、徐鑄成等一道把文匯報變成反動的宣傳工具”“合謀寫文章為儲安平的‘黨天下謬論辯護”等,浦熙修由此結束了新聞記者生涯,抑郁成疾,于1970年含冤去世。1980年,黨中央作出改正浦熙修被錯劃為右派的決定,為她恢復了名譽。
[采訪前記]
在20世紀末,浦熙修的女兒袁冬林、兒子袁士杰才有條件將母親一生中大部分文章收集成冊,編輯成《浦熙修記者生涯尋蹤》問世。由浦熙修的親朋從不同角度著筆的《憶浦熙修》亦獲出版,袁冬林寫的《浦熙修:此生蒼茫無限》也隨后同讀者見面,這使得袁冬林的心中稍許有了些安慰。
袁冬林至今保存著兩本發黃的病歷。在住院號為112936的那頁病歷記著:“1966年12月10日,今日上午10時余,病房全體休養員召開大會,并寫通令,對大右派分子浦熙修批斗,令下午出院。”彼時的浦熙修已經身患直腸癌,病情惡化,但是住院數次都被趕出。1970年4月23日,北醫附屬人民醫院急診室走廊里,浦熙修苦苦掙扎后醒來,她說:“別費事兒了。”自己拔掉7輸氧管子,背自著沉重的政治包袱,經受著精神與病痛的雙重折磨,她孤獨悲涼地走了,身旁沒有一個親人。當時兒女均在外地,昔日故交則大都斷了聯絡。有人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才敢打聽浦熙修的下落。連昔日并肩與她作戰的名記者彭子岡,曾經在浦熙修身患絕癥時候去探望,后來也不無辛酸地回憶,“她和我之間還是1957年的同患難者,若不是領導讓我去北京醫院探望她,我是不會也不敢去的。”
那些叱咤的風云都拋在身后了。浦熙修是民國時期著名女記者。她曾滿懷愛國激情與責任感,疾惡如仇,采寫并刊發了大量文章,其中不乏切中時弊的“闖禍”新聞,被譽為“勇于披堅執銳,敢于短兵相接的新聞戰士”。1941年12月,香港緊急疏散,許多民主人士未能及時撤離,但是孔祥熙夫人宋靄齡居然帶著洋狗從香港飛抵重慶。浦熙修正好在機場訪問,捕捉到這樣的消息,如何能在當時國民黨嚴厲的檢查制度下刊發出來,浦熙修想盡了辦法,她采用了點滴方式,一條一條地寫,先寫孔夫人來渝,再寫重慶忽然多了幾條吃牛奶的洋狗的消息……這些消息分頭送檢,檢查后拼起來發表,再加上一個巧妙的標題,于是轟動全國的新聞誕生了,輿論為之大嘩。
1957年,以“左派”記者聞名的浦熙修,突然成為了資產階級大右派。《人民日報》社論指明點7時任《文匯報》副總編輯的浦熙修,說她“是一位能干的女將”,并且說,“羅隆基-浦熙修一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著名漫畫家華君武發表了一幅應景漫畫:一女子藏臉孔于琵琶后,琵琶上寫著“羅隆基立場”,旁白則是“浦熙修自我檢查”。1980年6月,黨中央為浦熙修恢復了名譽,漫畫家華君武寄來了一封遲到的道歉信。“我曾畫過一幅漫畫諷刺過她,這張漫畫現在認識是錯誤的,也是不應當的,此事久壓心頭,趁此機會,只好向她的家屬表示道歉了。”1997年,華君武發表《邪正自明》一文再度為此道歉,“我畫的這幅畫,題為‘猶抱琵琶半遮面,是對浦熙修的不嚴肅態度,也可以說是一種人格侮辱。”華君武回憶,當時康生說他這張漫畫畫得好,他還很高興,但是鄧小平看后說,以后不要畫這種漫畫了。
干戈化為了玉帛,浦熙修卻早已在積郁成疾后撒手人寰。1957年,在沒頂的政治風暴中,浦熙修反復“檢討”自己,她被迫揭發羅隆基,甚至在親友的壓力下,不得不交出7日記和羅隆基多年來給她的私人信件,以證明自己并無反黨之心。而她和羅隆基“十年最親密的朋友關系”,卻因此恩斷義絕。浦熙修亦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她病重時,民盟中央派人去看她,當時她提出的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把羅隆基給她的十幾封私人信件還給她,信件歸還后,她非常感激。
自始至終,浦熙修從來沒有埋怨過共產黨,始終相信毛主席,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際,她還寫了一份自傳,向黨傾訴衷腸,盼望歷史給出公正的評價,在劇痛難忍之際,她一段一段地抄寫了大量毛澤東的文章和詩詞,以求得精神上的支持。
由于時間關系,我只能談我娘的一些片斷。直到今天,毛澤東主席為什么點我娘的名還是個不解之謎。那是1957年夏天,我上大學四年級。當時同學拿了一份《中國青年報》給我看,登載了批斗大右派浦熙修的新聞與照片,我嚇了一跳,覺得腦袋都大了。娘被特務打過,又被國民黨監獄關過,差點犧牲,怎么會反黨呢?我真是想不通。但我思想里有一條,相信黨,聽黨的話,肯定是娘在哪方面出了問題。我按黨的要求表了態,說她是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她所受到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因此,她具有資產階級的新聞觀。
好人和壞人
我認為娘是真正的新聞記者,她對付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就采取了很多辦法。她對新聞很敏感,但是這種敏感后來被壓抑了。
娘最意氣風發的時候還是從抗日戰爭到解放前。在娘的記者生涯中,值得大書一筆的,是她對國共和談及政治協商會議的采訪報道。1946年1月,國民政府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那是國共和談的產物。娘采訪了當時的38名政協代表,那時辯論的一個主題是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孰先孰后的問題,38位代表各就此發表意見。代表中最難訪問的是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杰。因為他素來謹慎,而且據說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以上。娘連去了三次,這位要人只好與她見面了,但要求娘不寫出他的姓名。靈活機智的娘答應了,使對方在訪問中感到輕松愉快。娘是守信的人,只在訪問記中寫“某代表”,但因為訪問的其他代表都有名有姓,與總名單一對,便知道“某代表”是誰了。當時有人稱贊娘,說她使得一位老練的外交家成為了她這個無冕之王的敗將,但娘只淡淡地說:“這只能算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

娘在政治上比較單純。娘在飽經政治風波后,才終于體悟自己的人生:“當時自己是一個新聞記者,東跑西跑,混在政治漩渦中,卻不懂得政治。”
在重慶時期,娘經過慢慢對比,越來越傾向于共產黨。她像小孩似的,常說好人和壞人,認為國民黨貪污腐化,不抗日,
搞摩擦,不民主,無自由,盡做壞事,令人憤慨。而共產黨說真話,講道理,有辦法,關懷人,做的都是好事。她愿意站在好人一邊打擊壞人。而好人的一切她都相信。三姨浦安修對她也有影響,三姨抗戰時就去了延安,后來嫁給了彭德懷。娘到了重慶,三姨通過關系介紹她和八路軍辦事處的人認識。周恩來非常關心娘,娘常去周公館,把周恩來對形勢的看法帶回來給報館,有時《新華日報》不能登的東西,就與娘協商,登在《新民報》上。
娘那時身后常有特務跟蹤。后來周恩來和董必武分別撤離南京的時候,娘特別傷心。娘在南京梅園新村共產黨代表駐地,到晚上兩點都不想走,就是合不得走。后來周恩來勉勵她,你還是多讀點書吧,她當時做新聞記者那么忙,哪有時間讀書啊!到董必武撤退的時候,娘大哭一通,被勸解說,她留在國民黨統治區,比到延安發揮的作用大,娘才留下來了。
從新聞記者到“舊聞”記者
1949年,娘是帶著對國民黨反對派勢不兩立的感情和對共產黨的熱愛、信任步入新社會的。剛解放的時候娘特別高興,就好像成天沐浴在陽光下,簡直就是滿心歌唱。你看她剛解放時拍的那張照片,娘胖了,肯定是心情舒暢,這也是她最喜歡的一張照片。
娘參加了中共召開的第一屆政協會議,是以自由職業者代表身份出席的。解放后,她去了面向知識分子讀者的《文匯報》。娘的人脈關系特別廣,什么事她又特別熱心,想給哪兒掛電話抓起來就打,解放后想找中宣部部長,說找就找,還是沒有等級觀念。娘的朋友說,那會兒他們都覺得浦熙修跑獨家新聞的鼻子怎么還那么靈啊,其實言下之意是說形勢都變了。

娘很快就陷入苦惱中,當時所有的政治新聞都要用新華社的通稿,娘那個時候不知道自己該怎么發揮作用,因為她是以發表獨家新聞和專訪著稱的。她未能入黨,在政治上有失落感。她因為覺得在北京辦事處過于自由,還希望黨組織加強對《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的領導。可她骨子里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娘所說的自由并不是無組織無紀律,而是要求思想上的獨立思考,要做有獨立人格的真我。
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正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特殊年代。階級斗爭要日日講,月月講,年年講。正好娘請了一個地主出身的保姆,我們都勸娘趕緊辭退她。娘就說,她現在已經不是地主了,地已經沒了,她憑自己勞動吃飯,為什么不可以?后來迫于壓力娘還是把她辭退了。那個時候所有的道德底線就是階級立場,否則在道德上就要被歸為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但娘腦袋里就沒有這根弦。娘對此接受、“覺悟”得慢。記得報上批判《早春二月》《北國江南》《舞臺姐妹》等電影,娘多次對我說;她沒有這個批判水平,自己身上就存在著這些被批判的人道主義思想。50年代初那些接二連三的批判中,批《武訓傳》《清官秘史》、批胡適、俞平伯、梁思成,批丁玲、陳企霞,直到反胡風,我后來還專門查了那段時期的《文匯報》,沒有看見娘的署名批判文章。
娘曾經是個很開朗的人。被打成右派后,她思想很苦悶,抽煙越來越厲害,娘用寫毛筆字來平靜自己的情緒。1959年,中央為一部分右派摘帽,其中就包括娘,她被分配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文史資料選輯》。娘意味深長地說:“新聞記者當不成了,娘又當了‘舊聞記者。”
與歷史重逢
《往事并不如煙》那本書在海內外影響非常大,也有個別年輕學者質疑娘揭發羅隆基的行為。他們不了解,一個人的言行處事,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這絕非是受到“威脅”“逼迫”而“交代”問題這么簡單。在那個年代,黨的威信很高,娘又是那么相信黨,當組織與周圍群眾全說你“錯”時,只能自己找“錯”了。聽一位新聞界的老人說:“當她被斗被折磨得傷心落淚的時候,可能只是覺得自己受了冤屈,誤解了她。”
1957年,毛澤東點了羅隆基和娘的名后,大會小會開始批斗娘。親人們也逼她拿出日記,找材料,幫助娘上綱上線,揭發羅隆基。娘的交代材料有些不是她的原話,而是大家“幫助”的結果。當時大姨比較厲害,我也幫著翻箱倒柜找材料。娘自己也被人揭發,我曾問過一些當年揭發我娘的老朋友,說當時你們認為浦熙修是真的反黨還是逼不得已?誰都無法應答。
娘曾想以死來抗爭,我被黨組織派回家,默默地注意她安眠藥不要吃多。娘心靈深處滴著血,卻又無法傾訴,她還是挺過來了,但是她和羅隆基徹底沒有來往了。1965年,羅隆基去世,我不曉得娘是否知道。當時她自己也得了直腸癌,信息來源很少。
對于這段歷史,我覺得有篇文章說出了我的心里話:“他們都曾經獻身或向往一個人民的新中國,一些人被錯劃為右派恰恰是出于這種理想。當他們被劃入另類后,言論、行動,不得不符合當時的政治、法律、是非、道德標準,都做過一些今天才可以說不必做或不當做的事情。”
娘開追悼會是很晚的,受“兩個凡是”的影響,政策的落實仍然困難重重。悼詞也幾經修改才確定下來。我們提出來請全國政協副主席康克清主持,娘的朋友說,反右最厲害的時候,康克清曾堅持說浦熙修不是右派。
這個心愿達成了。1981年3月19日,娘的追悼會在政協禮堂第二會議室舉行,娘那些記者朋友們來了,不像是開追悼會,大家高興啊,久別重逢,就覺得哎呀,浦熙修怎么走啦,怎么沒有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