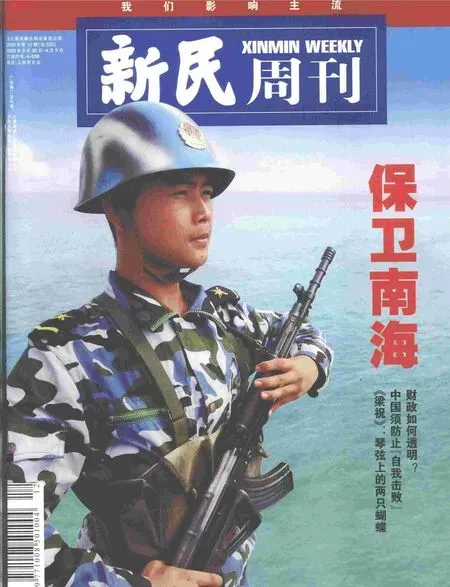精英道德:被遺忘的改革資源
童大煥
在近日一個慈善論壇上,“中國首善”陳光標面對60個北京各界普通百姓做起了現場調查:對中國富人印象好的請舉牌。結果是所有人保持靜默,只有一個老太說:我們喜歡你,但不喜歡中國富人。陳光標對這個結果并不驚訝,他接茬說:在我們企業對1000人做的關于這個問題的調查中,還有90人左右表示喜歡中國富人呢。其實這個比例也只有可憐的9%。 這也許是迄今為止國人“仇富”的最直觀量化,從一個側面坐實了國人多有“仇富心理”的判斷。
不僅僅是富人,我認為中國整個的精英階層,不論是政治、經濟還是文化精英,正處在歷史性的十字路口上,向左,可能成為貴族和英雄;向右,可能成為笑柄和罪人。在短短三十年里,中國很小比例的精英階層占有了很大比例的社會財富,順利實現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以后,其中的大多數人卻沒有像馬斯洛的需求理論所描述的那樣,順理成章地邁向更高層次的人生追求:尊重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通過謀求全社會的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在造福于社會的同時,實現自己更大的安全與社會認同與尊重,而是在人性貪婪的道路上繼續一路狂奔。
哪怕到了今天,世界金融危機引爆國內經濟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失業問題嚴峻,民生如此多艱,我仍然看不見既得利益階層讓步的意思,不指望他們拿出千金散盡還復來的慈善勇氣,但指望社會保障來得快些好些,指望資源和基礎服務領域的行政壟斷打破得快一些徹底一些,民眾就業和創業的門開放得大一些、門檻低一些,指望減稅和壓縮行政開支的力度大一些,但這些方面,似乎都是“吹面不寒楊柳風”,石油、天燃氣等卻在醞釀逆勢漲價。
許多人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奉為圭臬,對其中描述的“經濟人理性”和人性的自私本性視為天經地義,殊不知亞當·斯密還有重要性絲毫不亞于《國富論》的另一部扛鼎傳世之作《道德情操論》,其開篇的第一句話便是:無論人們會認為某人怎樣自私,這個人的天賦中總是明顯地存在著這樣一些本性,這些本性使他關心別人的命運,把別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雖然他除了看到別人幸福而感到高興以外,一無所得。他說:“這種自相矛盾似乎扎根于不變的人性原則之中。”
市場是看不見的手,道德同樣是一只看不見的手。但是過去很長時間里,中國精英的群體道德,基本處于休眠狀態,傳統的道德,多是統治階級用于馴服民眾的工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達則兼濟天下”的古訓,也基本上屬于道德自覺,未能成為社會對精英的軟約束。乃至于大眾傳媒發展到今天的互聯網時代,如本文開頭所言的“仇富”,也基本只停留在“腹誹”階段,沒有在社會上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
在1978年前的半個多世紀里,20世紀前半葉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半葉的前三十年,又是各種政治運動的無孔不入,朝不保夕的人們不可能生發道德自覺。但是經過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和平發展,時間也進入更為和平的21世紀,該是全面喚醒和激活中國精英道德的時候了!
必須全面喚醒政治、經濟、文化精英的道德感使命感,才能為中國社會的改良注入新和活力與動力。有西方學者指出:如果既得利益群體強大到一定程度,或者說超過某個臨界點,則一切改革皆無可能。這是普世經驗,并不特指中國。我們傳統的蛋糕做大理論是無法扭轉局面的。因為在不合理不公正的機制下,蛋糕越大,占社會大多數的窮人獲得相對份額反而越小,這就是所謂“悲慘式增長”。丁學良先生撰文《“還債”觀:重建改革道德之源》,提出了改革要“向中國人民還債”的觀點。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在制定具體政策的時候以民為本,才不會把改革變成一個分肥的過程,而是變成一個持續富民的過程。薛涌先生說“要刺激出健康的經濟倫理”。即如韋伯強調的《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克勤克儉,多工作少消費,自覺貢獻于社區建設,貢獻于社會的公平正義。而不是像豬頭一樣只知一己之奪取、占有、享樂與揮霍。
我對喚醒和激活精英階層的道德擔當抱以信心,如當今世界首善比爾·蓋茨,當初也是鐵公雞一毛不拔,以為辦好企業是最大貢獻,但母親去世和社會道德壓力使他幡然醒悟;近的如一些企業高管的天價年薪遭譴責后,在今天的危機面前已經不止一人宣稱“零年薪”。如何喚醒和激活精英階層的道德資源?少不得要把本文開頭所說的“仇富”從壓抑在抽屜中的“腹誹”旗幟鮮明地放到桌面上來:不是要用暴力手段打家劫舍奪人財產與生命,而是用理性、和平的輿論手段,理直氣壯地仇視腐敗,光明正大地鄙視為富不仁,義正辭嚴地譴責和聲討各種制度性、非制度性的掠奪與非正義,讓精英階層只有在慈善與各種正義行為中才能獲得尊重與自我實現的感覺,而不是因他們對社會資源的占有而獲得推崇。(作者系知名評論員,雜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