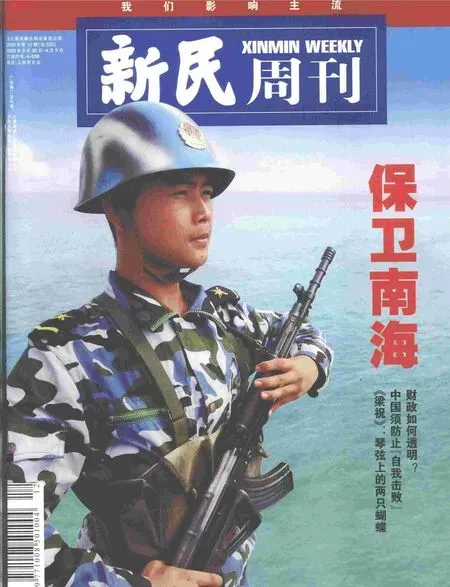《梁祝》為何成絕唱
周晏珵 錢亦蕉

《梁祝》的出現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是在特定時代環境下出現的特有的作品。不要再留戀于當初的形式,應該有新的尋找和突破,沒有創新就永遠走不出囹圄。從這個意義上,讓我們忘卻《梁祝》,往前走。
說到交響樂,似乎離不開“西方人的音樂”這樣的印象。事實上中國交響樂發展已近百年,共有370多位作曲家創作了2800余部作品,其中公開發表的約有1500余部。蕭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拉開了中國交響樂創作的幕布,黃自的《懷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之后的半個多世紀,中國音樂始終致力于中西語匯的交融……
然而,留在普通人記憶中的旋律并不多,我們能記住什么?那千余部作品中,是否曾有一串音符敲響你的耳膜、柔軟你的心房?唯有《梁祝》家喻戶曉,五十年來仍余音繚繞。
集體創作是時代特例
“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的成功綜合了很多因素。好的創意,適合的語境以及集體的智慧三者缺一不可。每一個人的長處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上海音樂學院作曲系副教授葉國輝認為,天時、地利、人和,在時代需要《梁祝》的時候,在音樂學院這樣一個合適的環境里,通過創作者們的努力,誕生了這部傳世之作。
“這是一個在特殊背景下,集體創作的成果。”上海音樂學院音樂學系副教授郭樹薈說,“不得不承認,即便后來仍有好的作品出現,也無法超越《梁祝》那樣的成功,因為再沒有這樣的珠聯璧合。”50年代的“民族化試驗”在各個領域遍地開花,集體創作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直到之后的樣板戲,也是這樣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創作模式。并且現代京劇在隨后的十年間始終占據著主流的地位,而交響樂的創作則因為意識形態的關系遭遇壓制和否定。
改革開放后,大批國外新思潮涌入,作曲家終于擺脫束縛,著手實驗和先鋒作品的創作,如譚盾的交響樂《離騷》,葉小鋼的《第一小提琴協奏曲》,郭文景為兩架鋼琴和交響樂隊而作的《川崖懸葬》,朱踐耳的音詩《納西一奇》,瞿小松的混合室內樂《MONG DONG》等。那個年代人們追逐內心,探索精神世界,照劉索拉的話說,“那像是另一場文藝復興”。狂潮直到80年代末才逐步散去,純樸悠揚的旋律和唯美的主題再次被懷念。然而,無論民樂作曲家創作交響或是交響作曲家轉投民樂,始終無法做到二者兼顧。格局已然改變——音樂創作從集體回歸個人。
中國幾千年來始終沒有“作曲家”這個概念。遠的不說,近代著名的《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華彥鈞)其實也只是以演奏者而非作曲者聞名的。因為中國音樂沒有“創作體系”,所有源自民間的音樂都是在歲月的打磨中形成的。有人演也有人改,靠口傳心授的唯一途徑來傳播。由于沒有真正嚴格的記譜法,中華民族的藝術確實是群眾的結晶,能夠留下來的作品更是歷史的選擇。自從劉天華將西方記譜法植入中國音樂后,個人作曲才成為可能。從此以后,作曲家擁有了署名的權利,作品有了保持不變的途徑。一部作品表達了作曲家獨一的思想,自然且統一,更完美地體現了藝術的完整性。然而到了《梁祝》年代,情況又突然不同了。在政府的強力號召下,人們懷揣著同樣的理想走到一起,集中力量為“民族化”努力。這樣高度統一的精神理念,過去不曾,如今也不會再有了。“集體創作可以看作是中國特有的一種方式”,葉國輝說,“個人創作才更符合藝術發展規律。”
交響樂就像F1
如果要解釋為何《梁祝》之后再沒有一部中國交響樂能夠獲得如此成功,答案恐怕只有一個:“時代變了”。除了作曲本身因素外,傳播方式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事實上,現在即使再創作一部《梁祝》,也不可能取得當時的效果。郭樹薈這樣形容:“現在是音樂盛宴的年代,不像那時候廣播里到處都是《梁祝》。現在什么都可以聽,好像面對自助餐,沒有必要單一地選擇。”當生活充斥流行、爵士、搖滾等各種音樂,人們已然無法回到那個被動接受的年代。熱愛流行還是熱愛古典,這只是一個選擇,并非對或錯的問題。
西方古典音樂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走出了純粹歐洲的范疇,世界各地的音樂家都站在本民族的舞臺上展現才華,當今樂壇早已不再僅有“德奧”。由此,“嚴肅音樂”一詞替代了傳統意義上的“西方音樂”,涵蓋了各種傳統經典音樂和一切專業作曲家用傳統或現代作曲手法所創作的音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交響音樂本就是屬于小眾的,它的現狀只是一種回歸”。在這個問題上,身為作曲家的葉國輝對此似乎并不在意,“這就像是F1賽車,它永遠不可能在馬路上與普通車競技,但一個國家仍然需要這樣的比賽去跟上世界的步伐。”
近年來中國“嚴肅音樂”作曲家在世界上也取得了顯赫的成就,不少作品在世界比賽中獲獎,但中國聽眾卻鮮少在音樂廳中聽到他們新創作的音樂。“這是目前國內的創作體制和演出體制共同造成的問題。”葉國輝透露出一絲無奈,“中國的年輕音樂人的機會太少了。”要知道,當年創作《梁祝》的陳鋼只有24歲,演奏小提琴的俞麗拿才19歲,最年長的何占豪也只有26歲,這部作品同時是陳鋼和俞麗拿的畢業作品。這放在現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集體創作回歸個體,就需要更加完善的體制和成熟的平臺來進行創作激勵。”當前作曲家創作主要依靠作品委約,而持續創作的源動力則來自作品演出。據葉國輝介紹,目前國內委約情況呈現兩極分化的趨勢,一些業已成名的作曲家積壓了大量的委約要求卻應付不過來,造成粗制濫造,而年輕作曲者始終無法得到創作的機會。“而在國外,規定一旦對作曲家給予委約,3年內不得再次委約同一作曲家。而如果2年內作曲家手上已有委約,其他人和機構一般也不會再找他委約。這樣的限制保證有足夠的時間使作曲家創作出高質量的作品。”
演出體制方面,目前中國能夠真正獲得演出機會的作品很少。“寫了,放在抽屜里是沒用的。”好比葉國輝在2007年獲得德國“青年·歐洲·古典音樂節”大獎的作品,卻一直未能在國內與聽眾見面。在世界樂團的交流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如BBC交響樂團到匈牙利演出,首先演出英國當代最好交響樂作品,之后是當地匈牙利作品,再有一首是最適合自己樂團表述的作品。但是國內邀請世界級樂團來演出時,卻一般不遵守這樣的規則。管理高層并未足夠重視中國作品在本國的演出,各種國外團體到中國訪問演出中幾乎沒有被要求演奏當代中國作曲家作品的例證。同時,國內演出團體由于考慮到作曲家知名度與樂團表現質量等種種原因,始終沒能跨出上演中國作品這一步。
葉國輝指出:“我們往往低估了聽眾,有許多人已經提出諸如‘國內交響樂團總在反復上演的作品過于老套,新鮮作品不多等異議。因此我們或許可以更加多元,于眾經典中加入一抹新鮮。在國外,‘世界首演這四個字對許多聽眾來說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他們認為能夠親身經歷一部新鮮出爐的作品,是一種榮幸。”
說到演出形式如何嘗試突破一些固有的思路,葉國輝提出“非音樂廳音樂會”的概念。其實,近年來也不斷傳出嚴肅音樂在音樂廳票房不佳的訊息,但是否每一場音樂會都需要放在音樂廳這樣的“高雅環境”里呢?“比如在國外,會把音樂會放在廣播電臺錄音棚,它賣現場演出票(100人左右),同時現場直播,第三還可以有錄音產品,文化資源被最高效地共享。”還有英國BBC交響樂團著名的“逍遙音樂節”。草地,舞臺,人群和音響的組合更像是一個戶外的大型派對,這樣的演出雖然幾乎沒有收益,但卻因其多元化的選擇,滿足了更多樂迷的耳朵。針對國內新作品知者寥寥的現狀,葉國輝也有自己的設想:“我們可以走出音樂廳,比如在大學圖書館的走廊、在教學樓的大堂、在錄音棚里,我們都可以去演出,讓那些新的聲音直接面對聽眾。最后再將那些被大家認可的成功作品搬入劇院上演。”
這就是一個絕唱
也許我們仍在感嘆至今沒有第二部《梁祝》這樣的作品,或者我們還在尋找契機成就另一個輝煌。
一方面,那些技巧繁復或是深沉內省的作品終不能成為大眾音樂。對熟悉單線條旋律的廣大普通聽眾來說,著實對更高層次的音響技術沒有過多的要求,能夠聽得懂的,有簡單的旋律音調,并且依靠標題來幫助理解才是好的音樂。另一方面,如果以大眾為出發點進行創作,必須認識到這些年來國人的耳朵或多或少已被錘煉。在聽覺不斷發展的情況下,《梁祝》這樣的作品只能有一部,任何刻意的模仿都將被審美疲勞所淘汰。對此,郭樹薈持有自己的觀點,“《梁祝》的出現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產物,是在特定時代環境下出現的特有的作品。不要再留戀于當初的形式,應該有新的尋找和突破,沒有創新就永遠走不出囹圄。從這個意義上,讓我們忘卻《梁祝》,往前走。”
“交響樂民族化”也早已不再是一個口號,葉國輝認為,當下在作曲前考慮是否需要“民族化”是很荒謬的,音樂中使用什么技巧、加入什么元素都是自然而然的。當然,作為一個成熟的中國音樂人,他一定會在交響樂中流露出自身傳統文化的因素。問題是,從最近三十年來看,“西洋音樂在中國的命運遠比中國傳統音樂的命運要好,所有學前兒童接觸的樂器一般都是西洋樂器,而音樂學院的學生了解的西洋音樂的知識也遠比中國傳統音樂多。對創作者來說,他們缺失的反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因子”。
《梁祝》擁有一個永恒的主題,抗爭體現了對于愛情的追求,化蝶則成就了生命的升華,這正是人類最為本真的情感,或許也正是這兩點鑄就了它在世界范圍的成功。同古希臘的“悲劇”一樣,觀眾因為對劇中人物的憐憫和對變幻無常之命運的恐懼,使感情得到凈化。悲劇中描寫的沖突往往是難以調和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堅強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氣概,卻總是在與命運抗爭的過程中遭遇失敗。故事所表述的重點并不是純粹無盡的哀傷,而是對命運的一種認識。然而和古希臘不同的是,中國人在宿命的最后加上了更高升華的體現——化蝶。令人感嘆的是,這個曾經在小提琴協奏曲《梁祝》創作階段差點被刪節的片段,最終被保留了下來,由此也使這部作品遭到種種坎坷卻仍被傳唱。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許多中國“民族性試驗”作品乃至之后中國的音樂創作對人性的表述并未引起太多共鳴。由此看來,《梁祝》的確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創舉。
經典,可能就是這樣的令人惆悵。超越總是在理性上體現,卻無法在感性上達到。就西方音樂而言,古典主義音樂的完美結構,始終沒有磨滅復調音樂在歷史上的卓越;19世紀浪漫主義的小品達到唯美藝術的高峰,卻沒有達到古典主義的嚴謹與深度;20世紀無論“印象派”還是“簡約派”的腳步,終還是回歸到了“新古典主義”。從中國音樂藝術來看,雖然沒有西方音樂那樣流暢的發展體系,但古琴、京昆戲劇這樣古樸的藝術形式無論如何都在時代的洪流中存在了下來。因為“經典”是一種對過往的追憶。
《梁祝》已然過去,烙印永恒地留在歷史長卷上。也許正是“化蝶雙飛去紅塵,終曲四寂留絕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