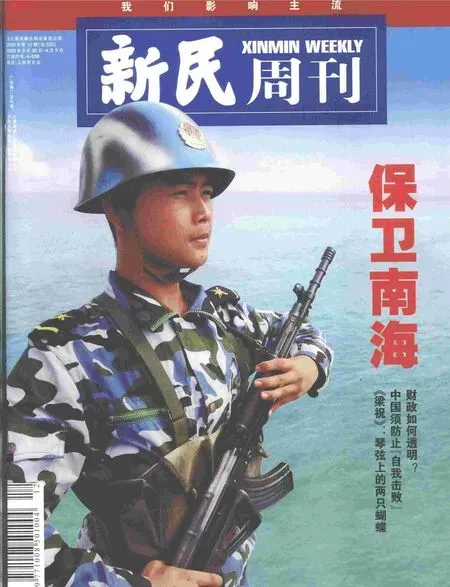《梁祝》的非典型“蝴蝶效應”
沈嘉祿

當年,何占豪、陳鋼、俞麗拿等人共同造就了《梁祝》,《梁祝》也成就了他們。但誰也不曾料想,《梁祝》這對蝴蝶起飛后,產生了極大的“蝴蝶效應”,深刻影響了幾代人,甚至改變了一些人的命運。
以我后來就自學了五線譜。練習曲拉到一定段位后,再將《新疆之春》上手,如小菜一碟。再后來,也能拉《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壯錦獻給毛主席》等正宗的小提琴曲了。
此時,小提琴獨奏曲經常在電臺里播放,剛從牛棚里出來的陳鋼應上海交響樂團首席潘寅林之邀請也創作了好幾首,比如《苗嶺的早晨》、《我愛祖國的臺灣》、《恩情》、《戀歌》、《金色的爐臺》和《陽光照耀在塔什庫爾干》等,經潘寅林演奏后大獲成功,在荒蕪的藝術園地里它們無疑是一朵朵奇葩,給劫難中的人們些許慰藉。潘寅林因此名聲大振,騎著自行車經過十字路口時,交警也會將紅燈翻到綠燈,請他先行。
《爐臺》和《陽光》我也是拉過的。但我們對潘寅林首演的《千年的鐵樹開了花》特別買賬,他演繹得絕對輝煌。這首曲子是阿克儉根據同名花腔女高音獨唱歌曲改編的,在革命的名義下,充分展現了小提琴的各種技巧。在無法接觸帕格尼尼、海菲茲、斯特恩的那個年代,潘寅林就成了我們的偶像。
這類曲子后來被陳鋼稱為“紅色小提琴”,我想這可能是為了界定某個時段而貼上的一枚標簽,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都知道它的涵義。但我覺得,“紅色”兩字是容易被誤讀的,不希望它被當作一個賣點。
為《梁祝》殉情的女孩
不過,許多學琴的青少年都埋藏著一個夢想:有朝一日能拉一拉《梁祝》。因為它是如此優美,包含了愛情、叛逆與獻身。從技巧上分析,它不如《千年的鐵樹開了花》和《戰斗進行曲》那般花哨,有悟性的人在學琴四五年后就會起野心,希望攻它下來。更主要的原因是被禁演了。禁果的誘惑力是不可抵擋的,也是人類啟智的第一動因。
陳鋼跟我說起,“文革”中有一年他去杭州,在山洞外聽到熟悉的琴聲,循聲走去,發現原來是幾個學琴的小青年在學拉《梁祝》。洞內無光,他們就打著手電筒照樂譜。還有一年他去昆明,得知某大學鐘樓這幾天來頗為怪異,每天晚上會發出微弱的燈光,好像在向某個方向傳遞信息。警惕性很高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決定在某夜突擊“捉鬼”,入夜后,鐘樓果然亮起微弱的燈光,他們模仿《奇襲白虎團》里的志愿軍偵察排,緊逼包圍,摸索上樓,一個手勢后,其中一工人踹起一腳破門而入,眾人一擁而入,手電筒打開亂照一氣:“不許動!”誰想到,眼前呆若木雞的竟是他們自己的孩子!這些孩子從學校的圖書館里搞來塵封已久的《梁祝》唱片躲在這里偷聽。一聽而上癮,成了每天的節目。
滬上收藏家楊忠明告訴我,他原來單位里有個同事,小提琴拉得非常出色,能將《梁祝》完整地拉出來。“文革”后期被總政文工團招去,誰料半年后在林彪“三箭齊發”運動中被趕了出來。原因是開后門進去的,而且在部隊里還偷偷拉《梁祝》毒害農村來的戰友。這個倒霉蛋回到了上海,在一個街道工廠里干粗活。二十年前工廠倒閉,他也下崗了,夾著小提琴到處討飯吃,有時還去教堂里演奏《安魂曲》什么的,每拉一曲得50元。
當時我們還聽說上海某中學音樂老師教他的幾個學生拉小提琴,其中一位女學生很有天分,進步神速,有一天她提出想聽聽心儀已久的《梁祝》。音樂老師給她找來這張膠木唱片,躲在倉庫樓梯下的小角落里偷聽。不料他們的行蹤隨即被人發現,那人報告工宣隊后。很有點戰術意識的工宣隊沒有打草驚蛇,花了幾天時間守候于此。幾天后,當他們再次“密室相會”時,破門而入,一舉擒獲。校方給這個老師捏造了個“引誘女學生失身”的罪名,關在一間破房子里隔離審查。
那個女學生呢,在學校里遭到師生的白眼,回到家里則要忍受父母的呵責。在得知老師被隔離后,她偷偷地跑到昏暗的隔離室外,通過窗子碎玻璃的缺口,將兩只剛出籠的肉包子遞給老師,以示慰問,不料被工宣隊活捉。被押送回家后,又遭父親一頓暴打。第二天,她趁家里沒人時打碎一只熱水瓶,吞碎玻璃自殺……
這下鬧大了,這個老師被送到公安局,關了小半年又送到工廠強迫勞動。

里革委阿姨的《梁祝》
后來,我也終于聽到了《梁祝》的唱片,那是在一起學琴的同學家里聽的,破窗簾拉得密密實實,大熱天啊,赤膊穿短褲聽完后大汗淋漓,但絕對過癮。而且我們永遠記住了主旋律。
這位同學姓陳,他是我們幾個中拉得最好的。中學畢業前,部隊來學校招文藝兵,他去報考了,成績不錯,但最終沒被錄取。后來得知他曾在家里偷偷拉過《梁祝》片段,正巧被里革委的阿姨知道了,關鍵時刻去學校揭發。陳同學后來按政策發配到崇明農場,還經常在毛澤東思想宣傳小分隊拉幾下。有一次收割稻子時,一不小心被飛快的鐮刀割去了一節手指,要命的還是左手中指。回家休養時他悲傷地砸爛了心愛的小提琴。
1978年,《梁祝》開禁的那天晚上,那位政治覺悟很高的阿姨看到我同學正守在收音機旁,異常興奮地告訴他:“現在你可以聽《梁山伯》了,現在政府允許啦,我也要聽聽的。”后來,這位阿姨看重映的越劇電影《紅樓夢》,看一趟哭一趟,一口氣連看三十多遍,你只要看到她兩眼紅腫得像一對核桃,就知道她剛從電影院回來。
還有一位同學與陳鋼同名,被昆明部隊錄取,其實他也在家偷偷拉過《梁祝》。也許里革委阿姨沒有聽到。
前幾天潘寅林告訴我,1959年《梁祝》首演時,他在上音附小,是十三四歲的娃娃,老師不準他們拉《梁祝》,因為這里有愛情,“少兒不宜”。“文革”后期,他已經是上海交響樂團的首席,但上臺只能拉“紅色小提琴”,《梁祝》好比是一塊燒紅了鐵板,碰也不敢碰。直到1981年他出國后,才在日本與東京都交響樂團等五大樂團合作,先后演奏了六場《梁祝》。優美而傷感的旋律一下子征服了日本聽眾。
我沒有拉過《梁祝》,一沒有譜子,二段位不高,故不敢嘗鼎一臠。中學畢業后參加工作,干的是力氣活,手指很快又粗又僵,十年后再摸琴,發現粗硬的手指再也捕捉不到小精靈般的音符了,夢想就此破滅。不過當初躲在暗室里偷聽《梁祝》的情景,是每年同學聚會時必定要重提的往事,也是一再確認我們情誼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