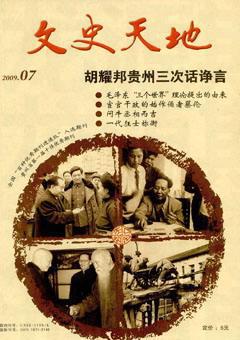并非平庸無能的魯莊公
王 財
魯莊公(公元前705-662年),春秋時期魯國第十六世國君。自從《曹劌論戰》被選人中學語文課本后,魯莊公就成了曹劌的反襯,“以莊公的駑鈍、浮躁反襯曹劌的機敏、持重。”(孫綠怡,《中華文學鑒賞寶典》)從而認定魯莊公是個平庸的國君:“他把戰爭的勝利寄托在施行‘小惠和祈求神靈的保佑上,說明他無能;他急于求戰,又說明他軍事上無知。”這種對魯莊公的片面的、極不公正的評價,影響了一代甚至幾代人。出于對歷史負責、對魯莊公負責和對后代負責的原因,我們有必要對魯莊公進行全面的考證和作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
在羞辱中即位
魯莊公是魯桓公的長子。桓公六年九月丁卯日生。因與桓公的生日相同,故取名為“同”。后立為太子。桓公十八年春,魯桓公在齊國被齊襄公謀殺。同年夏天,13歲的太子同即位,這就是魯莊公。
桓公十八年春,魯桓公不聽申繻的勸阻,執意帶著夫人文姜到齊國去。魯桓公與齊襄公在濼水會見。夫人文姜與齊襄公舊情復發,勾搭成奸。魯桓公知道后,對夫人發怒。夫人就去告訴了齊襄公。這對奸夫淫婦開始密謀殺夫。齊襄公先是宴請魯桓公,等到魯桓公酒醉后,就派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彭生乘機折斷魯桓公的脅部,將魯桓公殺死于車上。
《春秋》記載這件事,是為了揭露他們的奸情。魯桓公與齊女(文姜)結婚,是為了重新建立齊、魯兩國前代國君的友好關系。他們的婚姻是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愛情的結晶。文姜本是齊襄公的女弟,在魯桓公還沒有迎娶文姜夫人前,齊襄公準備將她嫁給鄭國太子忽,但被太子忽辭謝了。《史記》中稱文姜為“婦”而不稱“女”。說明她在未嫁魯桓公之前,與齊襄公已經建立了比較深的感情,早已是齊襄公之“婦”了。魯公子犟到齊國來迎娶文姜時,齊襄公還破例送姜氏到罐地。但這種個人感情是無法超越政治需求的。愛情之火只能被壓制,但不會熄滅。十五年后,情人重逢,舊情復發,被壓制的愛情之火就熊熊燃燒起來了,但燒過頭了。在事后幾年里,她仍然多次與齊襄公在不同的地方私通。
《春秋》沒有記載魯莊公即位大典的事,因為他的母后文姜沒有回國。《春秋》不稱姜氏而稱夫人,是因為莊公與文姜斷絕了母子關系。可見,魯莊公是在羞辱中即位的:作為兒子,他的母親的行為讓他蒙羞,父親被殺使他受辱;作為一國之君,先君在他國被謀殺,又“無所歸咎”,更是奇恥大辱。但作為一個年少的新的二等國的國君,拿強大的齊國和荒淫殘暴的齊襄公又能怎么樣呢?集國恨家仇于一身的魯莊公,只能將羞辱、怨恨深深地掩埋在心底。為顧全大局,只得忍讓;為挽回一點面子,只好向齊襄公“請得彭生以除丑于諸侯”。于是“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事情就這樣了結了。
“以德服人”獲贊美
莊公八年的春季,莊公在太廟前操練士兵。夏季,魯、齊兩國軍隊圍攻鄖國。郕國戰敗后向齊軍投降。魯國的仲慶建議要攻打齊軍。魯莊公說:“不能這樣。我實在沒有德行,齊軍有什么罪過?罪是由我引起的。《夏書》說:‘皋陶努力樹立德行,具備了德行,別人自然降服。我們還是姑且培養德行,等待別人降服的時機吧!”秋天,魯軍回國。君子由此贊美魯莊公。
按理說,魯師聯合齊師圍攻郕國,郕國戰敗后只向齊師投降,齊國就沒把魯國放在眼里,有點欺人太甚。仲慶請伐齊師,也是在情理之中。魯莊公不但沒有同意,反而將罪過攬在他一個人身上。并且強調務必要培養德行,等待別人降服的時機。通過這件事,我們可以發現魯莊公不在乎一時的名利,不計較暫時的得失,要厚積薄發、以德服人。
魯莊公的“修德以待時”也是有其歷史原因和現實意義的。
周公旦堅持以仁、德治天下,頗得民心,諸侯臣服,為后人稱頌。他的兒子伯禽受封魯地,這就是魯公。魯公伯禽當初到受封的魯地去治理,三年后才來向周公匯報政事。周公問:“為什么來遲?”伯禽回答:“改變那里的民俗,革除那里的禮儀,三年才完成,所以來遲了。”由于魯公的變革,魯國的民俗、禮儀都從周制。周公的仁政、德治思想在魯國的歷代國君中影響很深,魯莊公及后來的國君也是如此。到魯昭公時,伯禽之治仍然存在。“魯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
從魯公伯禽到魯莊公,已歷經十五世,三百余年。由于歷代國君均好義不好戰,魯國不是很強大,在當時屬二等國。而他的鄰國齊國,還在太公呂尚受封之初,“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就在魯莊公十五年,齊桓公開始稱霸。齊國常常對魯國虎視眈眈,幾欲滅之。面對強大的齊國,魯莊公也只能“修德以待時”。
魯莊公在政治上以仁、德治天下。在《曹劌論戰》中,從他回答曹劌的三個問題中也可以看出。魯莊公為應付這場戰爭作了充分的準備:對官吏——“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這雖然是“小惠”,但表明他平時就善待部下,具有公平正直、兩袖清風的高尚人格;對神靈——“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這雖然有點“迷信”,但體現他對神靈的敬畏,誠實守信、實事求是的為人準則;對人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這充分體現了他的民本思想,說明其賞罰分明、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他自認為從上至下都是問心無愧的:上對得起祖先神靈、下對得起將軍、大臣和平民百姓。他所做的這一切說明他一貫以仁、德治天下:他以人為本、取信于民,才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常施“小惠”,才得到了將軍、大臣、謀士們的擁護和幫助。所以當齊國來侵犯時,朝中大臣謀士們才會群策群力、鼎力相助;曹劌才敢來、才愿意來出謀劃策;前方的將士們才會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后方的人民才會源源不斷地給予支援。
主張和平、反對侵略
《左傳》中記載了魯莊公在位的三十二年間,魯國參與了十次戰爭。其中五次是自衛還擊戰,三次是幫助別國平定叛亂,二次是主動出擊。這些都是正義的戰爭,沒有發動過侵略別國的戰爭。十次戰爭中,有八次是取得勝利的,只有二次失敗。從下面的幾場著名戰役中。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在實戰中不斷成長、成熟的魯莊公及其不斷提高的軍事指揮才能。
乾時之戰。莊公九年夏季,魯莊公討伐齊國,護送公子糾回國。他聽信了管仲發來的錯誤信息,認為公子小白已經死了,沒有做認真的準備,慢慢地、大搖大擺地向齊國進軍。可是,公子小白已經提前到了齊國,做了國君,正張網以待。秋季,魯軍跟齊軍在乾時作戰,魯軍敗績。莊公躲過一劫,換車逃回了魯國。
長勺之戰。就是《曹劌論戰》中描寫的那場戰爭。莊公十年春,齊軍攻打魯國。魯莊公準備迎戰。曹劌請求進見。他的同鄉人說:“那些吃肉的人在那里謀劃,你又去干什么!”曹劌說:“吃肉的人目光淺短,沒有深謀遠慮。”于是入宮進見,曹劌問魯莊公:“憑什么來作
戰?”魯莊公說:“暖衣飽食,不敢獨自享用,一定要分給大家。”曹劌回答說:“小恩小惠不能周遍,百姓不會跟從的。”魯莊公說:“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擅自增加,祝史的禱告一定如實相告。”曹劌說:“一念之誠也不能代表一切,神明不會降福的。”魯莊公說:“大大小小的案件,雖然不能完全洞察,但必定合情合理去辦理。”曹劌回答說:“這是為百姓盡力的一種心意,可以憑借這個打一下。雙方交戰,請讓我跟著去。”魯莊公和曹劌同乘一輛兵車,與齊軍在長勺展開戰斗。莊公準備擊鼓。曹劌說:“還不行。”齊軍三次擊鼓后,曹劌才說:“可以出擊了。”齊軍大敗。莊公準備追上去。曹劌說:“還不行。”曹劌走下車來,仔細觀察齊軍的車轍,然后登上車前的橫板遠望,說:“行了。”就追擊齊軍。戰勝后,魯莊公問曹劌取勝的原因。曹劌說:“作戰全憑勇氣。第一次擊鼓,能振奮勇氣;第二次擊鼓,勇氣就減少了一些;第三次擊鼓后,勇氣就沒有了。他們的勇氣沒有了,我們的勇氣剛剛振奮起來,所以戰勝了他們。大國是難以琢磨的,恐怕他們有埋伏。我仔細看他們的車轍已經凌亂了,遠望他們的旗子已經倒下了,所以才追擊他們。”
乘丘之役。莊公十年六月,齊國和宋國的軍隊駐扎在郎地。公子偃對魯莊公說:“宋軍的軍容不整,可以打敗他。宋軍敗了,齊軍一定回國,請您攻擊宋軍。”魯莊公不同意。公子偃用老虎皮蒙上馬,私自帶兵從雩門出去攻擊宋軍。魯莊公領兵跟著進攻。在乘丘把宋軍打得落花流水。齊軍也就撤走了。
在這次戰爭前,魯莊公是有點畏懼齊、宋聯軍的。他知道一個齊師就夠他喝一壺的,更何況還是齊、宋聯軍來犯,就沒敢輕易聽取公子偃的建議。但當公子偃擅自帶兵沖入宋軍陣地后,他還是果斷率軍出擊,齊心協力打敗了宋師。在初時,他是有點過于謹慎,但能及時出擊,說明他還是能審時度勢,不盲目冒進,也不優柔寡斷。
部地之役。莊公十一年夏,宋國因為乘丘那次戰役而入侵魯國。在這次戰爭中,魯莊公將從曹劌那里學來的“一鼓作氣”理論運用得更超前:他還未等宋軍擺好陣勢,就逼壓過去,把宋軍打得落花流水,倉皇逃竄。
如果說,在乾時之戰和長勺之戰時,魯莊公對軍事理論不甚了解,在軍事指揮上是完全依靠他人的,那么在乘丘之役中,他已初步掌握了一點軍事知識,能主動協同部下作戰;到鄑地之役時,他就已經能夠運用所學到的軍事理論,獨立指揮戰爭了。通過這幾次戰爭。齊桓公看到了魯國的實力,也看到了在實戰中不斷成長、成熟的魯莊公。后來齊桓公就不敢再對魯國輕易動兵了。
《左傳》中記載了魯莊公在位的三十二年間,魯莊公參與的七次結盟。其中六次是為了講和、幫助別國平定叛亂或打抱不平,目的都是為了和平,而不是為了侵略、瓜分或稱霸。只有與齊國大夫的那次結盟,是因為齊襄公死后,齊國無君。為護送公子糾回國做國君打好國內的政治基礎。在其他諸侯出于侵略、瓜分或稱霸目的的結盟,他都沒有參加。比如莊公十五年春,齊桓公稱霸的那次齊、宋、陳、衛、鄭等國諸侯在鄄地的會盟,魯莊公就沒有參加。
愛惜人才、善用人才
魯莊公是一個愛賢人、得賢人、用賢人的賢主。從他不殺管仲這件事上可以看出,他是愛惜人才的。
當初,齊襄公謀殺魯桓公,與魯桓公夫人私通,又誅殺很多不該殺的人,生活淫亂,多次欺辱大臣。他的弟弟們害怕禍及自身,次弟糾由管仲和召忽護送逃到魯國,因為他的母親是魯女;次弟小白逃到莒國。后來襄公被無知所殺,雍廩又殺了無知。莊公九年夏,莊公護送公子糾回國。可是公子小白先從莒國回齊國做了國君。秋,魯軍跟齊軍在乾時作戰,魯軍敗績。齊國送信給魯國說,公子糾是國君的兄弟,不忍心殺他,請魯國將他殺了。召忽、管仲是國君的仇人,請將他們送回齊國來,把他們剁成肉漿才甘心。否則,就要圍攻魯國。魯國害怕了,就在笙瀆殺了公子糾。召忽自殺,魯國將管仲關進了牢房,準備送他回齊國。施伯對魯莊公說:“齊國想得到管仲,并非要殺他,是準備重用他。如果齊國重用了管仲,他將成為魯國的后患。不如殺了他,拿他的尸體送給齊國。”莊公不聽,將管仲押送回齊國。齊桓公聽了鮑叔的建議,任管仲為國相。
魯莊公不是不知道管仲是一個人才,也不是不知道放虎歸山必有后患的道理,同時他也知道如果先斬后奏,殺了管仲,齊國也不會拿他怎么樣。但他沒有聽從施伯的建議,執意將管仲送回齊國去。一方面是他懾于齊國的壓力,不得不將管仲通過外交手段交給齊桓公。另一方面是他確實認為管仲是一個人才,覺得殺之實在可惜,所以舍不得殺。
其實,魯莊公也不是一個手軟的國君。對那些不是很有德行的人,他也是主張殺之以絕后患的。如,他曾建議兒子斑,將調戲梁氏的圉人葷殺死。因為葷力氣很大,只能殺不能鞭打,否則會留后患。不出魯莊公所料,斑后來就被葷殺死了。魯莊公沒有殺管仲,說明他不但認為管仲是人才、而且是君子,相信他不會成為魯國的后患。事實證明他是有遠見的,管仲不但沒有成為魯國的后患,恰恰相反,管仲還巧妙地幫了魯國一回。
齊桓公五年,齊軍討伐魯國,魯軍將要戰敗了。魯莊公就向齊桓公請求,愿意獻出遂邑來平息這次戰爭,齊桓公答應了。齊桓公與魯莊公在柯會盟。將要結盟時,曹劌在壇上拿匕首劫持齊桓公,說:“歸還魯國被齊國侵占的地方!”齊桓公答應了。然后曹劌才拿開匕首,北面坐在臣子的座位上。后來齊桓公后悔了,想不歸還魯國的地方并且殺掉曹劌。管仲說:“這是您在被劫持時已經答應的事情。殺曹劌,只是一小會兒的快樂罷了,但是在諸侯中會形成背信棄義的印象,會失去天下的援助,不能這樣。”于是齊桓公就歸還了侵占的魯國的地方。諸侯聽到這件事后,都信服齊桓公,想來依附齊國。
本來,魯國戰敗,割地求和,是魯莊公自愿的。曹劌先違反盟約,在壇上用匕首脅迫齊桓公。齊桓公不得已才答應返還從魯國侵占來的土地。事后齊桓公反悔,殺曹劌,重奪魯地,魯國也無理可講。齊桓公要這樣做,也不是做不到的,甚至再發動一場對魯國的戰爭都是極有可能的。魯國剛戰敗,再打也是很難取勝的,還可能丟失更多的土地。這時,管仲十分巧妙地勸諫齊桓公,既化解了這次矛盾,又讓齊桓公獲得了守誠信的美譽,還保住了曹劌的性命、魯國的領土。我們也可以認為這是管仲在報魯莊公當年的不殺之恩。
不拘小禮小節
在長勺之戰中,魯莊公對曹劌是言聽計從的,因此落了個目光短淺、昏庸無知的非議。其實,作為諸侯國的國君,有時他也是比較專制的,特別是在他執政二十幾年后,就連曹劌的話他有時也是不聽的。
莊公二十三年夏,魯莊公到齊國去觀看祭祀神社。曹劌勸阻說:“不可以。禮是用來整飭百姓的。所以會見是用以訓示上下之間的法則,制定財賦的標準;朝覲是用以糾正排列
爵位的儀式,遵循老少的倫次;征伐是用以攻打對上的不尊敬。諸侯朝覲天子,天子視察四方,以熟悉會見和朝見的制度。如果不是這樣,國君是不會有舉動的。國君的舉動一定要給予記載。記載而不合乎法度,后代子孫將會怎么看您呢?”魯莊公這次就沒有聽曹劌的,硬是到齊去觀看祭祀社神的活動了。這說明魯莊公一方面對當前的魯國和齊國的政治形勢有全面、客觀的估計;另一方面,他以為到齊去觀看祭祀社神活動,還可以增強兩國的友好關系。
莊公二十三年秋,在桓公廟的柱子上涂上紅漆。二十四年春,又在桓公廟的椽子上雕花。御孫勸諫說:“我聽說:‘節儉,是善行中的大德;奢侈,是邪惡中的大惡。先君擁有大德,而您卻把它放到大惡里去,恐怕不可以這樣做吧?”但他沒有聽御孫的勸諫。可能他認為這不算是什么大的浪費,還能表示對先君的孝心和敬意。也許是他未能報殺父之仇而感愧疚,才這樣做的。
莊公二十四年秋,哀姜來到魯國,魯莊公叫同姓大夫的夫人進見,進見時用玉帛作為見面禮。御孫進諫說:“男人進見的禮物,大的是玉帛,小的是禽鳥,用東西來表明等級。女人進見的禮物,不超過榛子、栗子、棗子、干肉,以示贄誠敬而已。現在男女用相同的見面禮,這是沒有區別的。男女的區別是國家的大法,由于夫人弄亂了,恐怕不行吧。”也許是他比較喜歡哀姜,或許是對齊國的敬意,他沒有聽御孫的勸,就破了這次例。
此外,《左傳》中還有魯莊公在夏天出現日食、秋天發生洪水時,擊鼓、用犧牲祭祀神廟;不為國事到洮地去與杞伯姬會見。這些也是不合禮制的,因為發生日食、洪水等天災時,不能用犧牲,只能用玉帛祭祀,也不能擊鼓。諸侯不是為了百姓的事情不能出行。但這些在魯莊公看來,都是無關大節的,與國家的興衰存亡沒有什么影響。只是違背了一些小禮小節,也就無所謂了。說明他是一個平時不太注重小禮小節,而遇國家大事,還是不糊涂的人。
后繼乏人
魯莊公晚年對繼承人的安排不當,留下了禍患,導致魯國在他死后幾年內,動蕩不安。當初,魯莊公建造高臺,可以看見黨家。在臺上魯莊公見到孟氏就愛上了她,便跟著她走。孟氏閉門拒絕。莊公答應立她為夫人,她就答應了。劃破手臂和莊公盟誓,后來就生了子斑。一次正當雩祭,事先在梁家演習,莊公的女公子觀看演習,圉人葷從墻外調戲她。斑發怒,叫人鞭打葷。莊公說:“不如殺掉他,這個人不能鞭打。他的力氣很大,能舉起稷門把它扔出去。”斑沒有殺得了葷,恰逢莊公也生病了。莊公有三個弟弟,大弟叫慶父,二弟叫叔牙,三弟叫季友。莊公娶齊女哀姜做夫人,哀姜沒有生兒子。哀姜的妹妹叫叔姜,生了子開。莊公沒有繼承王位的太子。由于他愛孟氏,就想立孟氏的兒子斑為太子。莊公病重后,就向叔牙詢問王位繼承人的事。叔牙說:“慶父有才能,有慶父在,可以繼承王位,您有什么可憂慮的?”莊公擔心叔牙將來立慶父為王,等叔牙退出后又問季友。季友說:“我將以死來侍奉子斑。”莊公說:“剛才叔牙想要立慶父,你說該怎么辦?”季友派人以莊公的旨意命令叔牙等待在鉞巫家里。讓鉞巫用毒酒毒死叔牙,說:“喝了這個,你的后代在魯國還可以享受祿位;不這樣,如果你死后,后代就沒有祿位。”叔牙就喝了毒酒,回去,到達逵泉就死了。魯莊公就立叔牙的兒子為叔孫氏。八月初五,莊公死在正寢里。季友按照莊公的授意立子斑為國君。子斑即位,住在黨氏家里。先前慶父與哀姜私通,想立哀姜妹妹的兒子開。十月初二,慶父派圉人葷在黨家殺死斑。季友逃跑到陳國。慶父竟然立公子開為國君,這就是湣公。滑公二年,慶父與哀姜私通更加厲害。哀姜與慶父想謀殺湣公后,立慶父為國君。慶父派卜齮在武鬧刺殺了滑公。季友聽到這件事,從陳國帶著滑公的弟弟申逃往邾國,派人在魯國作內應。魯人準備誅殺慶父。慶父害怕了,逃亡到莒國。這時,季友帶著公子申返回魯國,立申為國君,這就是釐公。釐公也是莊公的小兒子。哀姜害怕了,逃到邾國。季友用財物賄賂莒國來求取慶父,慶父被送回魯國。季友派人去殺慶父,慶父叫大夫奚斯去請求季友赦免他。季友沒有答應,奚斯哭著回去。慶父聽到奚斯的哭聲,就自殺了。齊桓公聽說哀姜與慶父亂倫,從而危害了魯國,就把她從邾國召回來,在夷地殺了她,把她的尸體運回齊國。魯釐公請求歸還哀姜的尸體并予以安葬。
魯莊公雖然順利的平穩的將他的君位交給了他心愛的女人所生的兒子,但他還沒有為兒子掃清政敵。對他身邊存在著的隱患沒有加以防范,比如,對他的大弟慶父的陰謀、他的夫人哀姜、兒子的仇人圉人葷,他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更不用說根除了。導致魯國在他死后幾年內,動蕩不安。
從以上這些歷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魯莊公在政治上,以仁、德治天下;在軍事上,重視操練士兵;外交上,堅持“修德以待時”。魯莊公愛惜人才,重用人才;主張和平、反對侵略;主張結盟、反對稱霸。正是這樣,魯莊公才能在三十二年的統治期間,保持內無大亂、外無大患的和平形勢。他既無大功,也無大過;既不是名望很高,也不是聲名狼藉;他處事謹慎、為人低調、不拘小節、不善張揚。所以有的人才片面地認為他愚昧無知、目光淺短、昏庸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