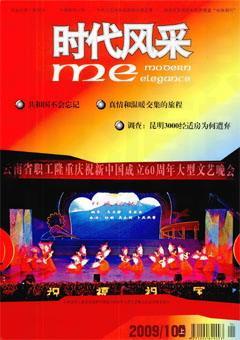1989耿鼎:技術為王
瓜 瓜
1948年,13歲的耿鼎作為一名童子兵,參加了淮海戰役。
由于氣候潮濕而寒冷,耿鼎長了一身疥瘡,到渡江作戰時,他與部隊家屬和傷病員一起留在了后方。1950年1月,耿鼎轉業到了重慶。戰爭之后,百廢待興,各個部門大量要人。耿鼎沒上過學,組織上把他送到速成識字班,學習b、p、m、f,開始認字。到1953年,因為生產建設的需要,他進入技工學校,這是耿鼎接受技術啟蒙的開端。一年多以后,工廠就催著要人,耿鼎到了重慶的一家兵工廠,那時,廠里有幾名老師傅和耿鼎同是北方人,是抗日戰爭時就遷到重慶大后方去的。老鄉見老鄉,拜師學藝順理成章,耿鼎學到了他們的許多絕招,成為廠里的生產骨干。
此時的耿鼎事業愛情雙豐收。還在技工學校時,耿鼎就和一位來自昆明珠璣街的女子談起了戀愛。1958年,有情人終成眷屬。1958年,為了支援云南。耿鼎婦唱夫隨,到了昆明。
籌建昆明重機廠時,廠里要加工30多根銑膛,這是一件考驗人的活計,難度大,要求高。廠領導問耿鼎:“你能不能干?”耿鼎回答:“可以干,沒問題。”結果,耿鼎一人開著機床,身邊七八十人圍著他轉,既打下手,又學技術。
1984年,北京搞了一個工具展覽會,既有理論又有實物,要求各個省派種子選手觀摩學習,耿鼎和其他云南“種子”一起結識了當時全國著名的技術能手,其中就有后來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的倪志福。當時,這些高手之間相互學習的風氣十分濃厚,問什么教什么,傾囊相授。
耿鼎回到昆明,同樣做了很多實物,在昆明和各個地州巡回講座,大力推廣。1966年,全國推廣會來到昆明,之后又由耿鼎帶隊到貴陽、重慶、成都等地傳授技藝。耿鼎初學深孔鉆時,通常在一根2米長的柱中打20毫米的孔,采用自動轉屑,只需五六分鐘,人很輕松,打出來的外斜度,不會超過一根頭發絲。后來,廠里生產20臺斷面車床,需要在一根立柱上打95毫米的孔,一般的加工太慢,三四天打一孔,耿鼎利用深孔鉆的原理做了一套工具,30多分鐘打一孔,精度仍然很高。過去車大螺母,因螺矩太大,光潔度差,效率也低,幾個班次都做不出一臺。耿鼎制作了一個浮動導桿,操作時再不振動,光潔度有保證了,效率比原來提高了五倍。類似的東西,耿鼎在廠里推廣了幾十項。
耿鼎在云南各地講學、推廣、攻關,為各廠培養了上千人的技術骨干。僅昆明重機廠的300多名刀具隊隊員,后來成為廠級領導干部的就有100多人。
耿鼎經手的大項目有很多。1988年,昆明重機廠要從德國引進塔吊起升的卷簡,為了不負眾望,他被派往德國考察學習時,就把回國加工的方案都做好了;1990年,小龍潭煤礦引進2臺昆明重機廠和奧地利合作生產的履帶式斗輪機,每臺都是800多噸的大型設備,耿鼎作為項目安裝負責人,其技術的精湛高效得到外國專家和廠方的一致贊賞;在幾家磷肥廠和氮肥廠,耿鼎親自安裝的干燥機,首尾幾十米的距離,誤差都不會超過半毫米……
從普通車工,到車間主任、分廠廠長、副總工藝師,耿鼎技術為王的本色從未改變。
1999年,耿鼎雖已退休,但余熱不減。一家軍工企業委托他們廠生產潛水艇發射魚雷裝置,一些人同意,另一些人說根本就做不出來。最后,只好“請耿師傅回來看看”。
耿鼎花3個月時間看完了圖紙,邊看邊考慮實施方案。在模擬的水倉中做實驗時,需要考慮到不同的水深處魚雷的阻力大小,由于內空直徑大,30多米長的裝置,其連接的精度從頭至尾誤差必須控制在0.5毫米以內,設備要求相當高。當每個零部件的加工方案擬定以后,耿鼎終于下結論:“可以做”。
魚雷發射裝置成功地安裝運行之后,這家軍工企業的總工程師拜耿鼎為師:“我是你的關門弟子”。
如今,耿鼎兒孫滿堂,一大家子生活得其樂融融。游泳、爬山、釣魚、打羽毛球,74歲的人,著自襯衣,穿背帶褲,看上去腰板挺直,精神抖擻。或許是鉆研技術的原因,耿鼎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幾十年前的往事,其發生的年月仍舊記得一清二楚,這是他人生的一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