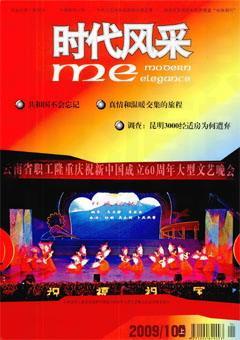經適房買得起也要住得起等5則
“有新房子誰不愿意住?但搬那么遠開銷會增加一倍,還有十幾萬元貸款要還,每關愁得覺部睡不著。”就在廣州保障性住房戶主轉租事件以違規戶被責令退房告一段落后,有違規戶道出的這番心聲卻引人深思。高昂的生活成本正成為部分經濟適用房和康租房戶主在月供、月租之處不能承受之重。
點評:住房困難戶好不容易盼來了政府提供的保障房,到頭來卻發現自己雖然有了相對便宜一些的住房,但出行難、購物難、上學難、就醫難、上班難等一大堆難韙在那兒候著,家庭日常生活開支也隨之增加一應該說,這種情況在當前來看絕不是什么個別現象,而是比較普遍。
說到底,問題還是出在保障房的民生定位上。保障房的保障對象,是買不起商品房或無力自行解決住房問題的城市低收入人群,這部分人本身就缺乏消費能力,如果保障房的價格優勢在其地理劣勢的對比下顯得微乎其微,勢必要令獲得保障資格的購房者陷入兩難境地,既擔心失去服前的機會,更操心將來如何過日子。實際上,現實中也確有這樣一些人,他們要么無奈地放棄到手的購房權利;要么明著將房子買下來,暗地里再租出去,以緩解生活壓力以及因購買保障房而產生的供貸壓力。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保障,但從優化生活的角度上看,居民的其他權利保障也不容忽視。這就要求我們在保障性住房建設規劃上,要凸顯民本思想,要充分考慮居民的實際困難和基本需求,加大對保障房所在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盡量為居住保障房的低收入家庭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條件,使保障性住房在改善民生中真正發揮社會保障功能。
“嚴禁扎堆聊天”的治民思路很可怕
抗州市北景園菊香苑小區的公告欄里,貼出了一張名日(1號公告)的告示。其中第9條規定,有些小區居民每天會在小區門口扎堆聊天,影響了小區形象。所以要求大家自覺遵守公約,禁止在門口扎堆聊天。
點評:在人情冷淡的都市,扎堆聊天這樣其樂融融的場景是難能可貴的,是小區居民和睦相處的表現,應該說扎堆聊天是在給小區加分,怎么就影響小區形象了呢?
只要聊天的居民不影響小區門口的交通,以影響小區形象為理由禁止居民扎堆聊天未免顯得太過牽強。別忘了小區本是供人們扎堆居住的地方,“以‘人為本”才是小區管理之道,而“以形象為本”的思維邏輯不免顯得荒唐。
“嚴禁扎堆聊天”的公告絕非民意使然,在一個提倡民主的社會,跳過民意而做出的決定能得到多少人的認同呢?做出決定、制定規定不尊重民意,搞一方獨裁,這明顯是不符合我國現代的治國治民思路的。這種管理思路必將得不到人們的擁護。要知道。失卻民心就等于失去了管理資本,再談管理無異于空中架樓。不論是企業管理還是小區管理,抑或大至行政管理,以人為本、尊重民意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之道。
“荒”的不是民工
和逐漸回升的經濟數據幾乎同步,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正在加劇。以至于沿海用人單位組團到中西部地區“搶”人。整個珠三角,乃至東部沿海城市的企業部在為“招不到工人”而發愁。
點評:“民工荒”并不是一件新鮮事,前些年珠三角也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然而。環境的變遷,當前的“民工荒”僅僅解讀為經濟復蘇的表現,恐怕并不夠。
必須看到的是,“民工荒”的出現,是經濟發展的產物,也是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民工荒不斷出現與兩個因素有關,一是企業擴張,新企業增多,直接需要新生勞動力;二是當地產業結構調整或升級,企業需要不同技能的工人,導致適用對路的勞動力不足。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產業規劃中,并沒有對勞動力市場同步考慮。使得大量用工過分短期化,一些企業追求低成本勞動力,不愿對勞動力進行技術培訓,導致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自發狀態。一會兒是農民工找工作“慌”,一會兒又是農民工緊缺,如此反復。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的企業仍然沒有真正重視農民工。企業紅火時,員工們只有超負荷勞動,而應有的合法權益、尊嚴卻被企業忽視。而金融危機一開始,很多民工又被自己的企業送回老家。現在老東家又有新訂單,又需要招人了,可是誰知道這樣的訂單能持續多久,值得他們來回奔波嗎?
中國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人力資源,珠三角卻在經濟復蘇的過程中出現了普工短缺,這兩種看似矛盾的現象糾結,需要我們的企業進行反思。
“民工荒”真的是缺民工嗎?或許,缺少的是企業吸引力、是對勞動力的保障。
集體研究不是免罪金牌
重慶市萬盛區文廣新局退休職工,現寄居在渝北兩路的王新聲大爺遇到這樣一件怪事——他每月要到萬盛領一次租房補貼,車費至少要花80元,而他領的錢卻只有79.52元。不能辦張卡定期轉賬嗎?領導說,不行!理由是。集體研究決定的。
點評:這則荒唐的新聞說明:在打造服務型政府的今天,一些政府工作人員為民服務的人性化觀念是如此闕如。
花80多元的路費,領70多元的補貼,活生生地將一個政府補貼,變成了一種權力刁難。完全可以通過轉賬等多種形式解決的問題,卻成了政府部門服務公民的一個荒唐現象,在這里,服務意識、服務思想不見蹤影,甚至變成嘲弄。
在一些人眼里,特別是官員眼里,“集體”仍舊是壓在孫悟空身上的五行山,成為肆意侵犯個人權益的借口,或者在問題出現時,讓一個虛化的“集體”為決策者個人責任埋單。
不知道萬盛區房管所所稱的“集體研究決定”,究竟是“集體決定就是正確的”意思的表達,還是為王老漢的遭遇推卸責任。但無論何種目的,都毫無道理。就像“民主,有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一樣,集體,也有很多罪惡假汝之名。多年來,“服從集體決定”成了慣性口語。在這里,“集體”成了“政治正確”,不容置疑。需要專斷時,將自己的決策上升到集體的高度;需要擔責時,則將自己的責任消解在集體的虛無里。“執政為民、服務發展”、“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仆”……這樣的口號已經不少了,但人民最需要的是落實啊。
制度“差之毫厘”,聽證“謬以千里”
《廣州市政府重大行政決策程序規定》公開征求意見,政府重大行政決策須通過座談會、公共媒體征求公眾意見,并組織專業論證會及聽證會。聽證代表中,利害關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
點評:如此明確地規定“聽證代表中,利害關系人代表不得少于2/3,現職公務員不得被選為聽證代表”,恐怕是首次。長期以來,聽證代表的構成備受質疑。由于聽證代表的構成要求不明確、產生程序不透明,讓聽證代表的身份很尷尬。不排除其中有某些利益代言人,有和事佬,抑或成為“擺設”。最基礎之一的聽證代表魚龍混雜,嚴重影響了聽證效果。
制度“差之毫厘”,聽證“謬以千里”。盡管聽證會要求遵循公開公正客觀等原則,盡管聽證會制度有所規范,但由于聽證制度執行十多年,已暴露出不夠完善的問題,或者說,存在著明顯的漏洞,讓聽證會的“民主功能”、“科學決策功能”大大減弱。這些制度性弊端、制度性漏洞,導致相當多的聽證效果“謬以千里”,事與愿違。堵塞制度性漏洞,讓聽證制度“不差毫厘”,進而,為民主法制建設快馬加鞭。
聽證代表的構成上,明確利害關系人代表的比例,并且“剝奪”現職公務員的代表資格,是一種“制度性修復”,也是制度性進步。把可能存在的不公正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更能“清晰”地聽到民眾的聲音,尤其是利害關系人的聲音,這些聲音更真實,更加原汁原味,即便有反對聲,也是還原聽證功能的“原聲”。利害關系人代表有望給聽證“興利除弊”。除了從聽證代表構成上完善聽證制度外,還應該在確保聽證公正公開客觀等環節上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