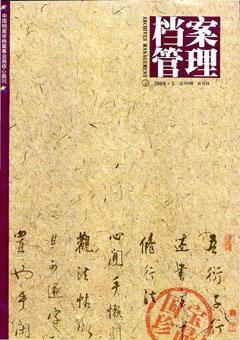檔案意識虛擬不得
任漢中
進入信息時代,借助計算機技術(shù)和網(wǎng)絡的發(fā)展,虛擬似乎成為一個熱門話題。檔案界步圖書界之后開始了有關(guān)“虛擬”的研究,出現(xiàn)了“虛擬檔案”、“虛擬檔案館”等眾多新名詞,欲將存在了幾千年的實實在在的社會核心信息資源的實體虛擬了。把以可靠性、真實性為生命。以最高社會信用等級為存在價值的檔案混同于一般的信息類別,全然不顧檔案的基本屬性。檔案內(nèi)容可以信息化,也可以“虛擬”,可檔案卻應該是現(xiàn)實的物質(zhì)存在。我常常納悶,檔案界的一些學術(shù)研究者,為什么沒有了最基本的檔案意識?難道他們的檔案意識也被虛擬了嗎?
我在指導學生的畢業(yè)論文和學年論文時,常常感到困惑,而在通讀了學生們的大作后,我才漸漸有些明白,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一個虛擬的想象物,他們心目中的檔案是從書本上得來的印象,他們的檔案意識自然也是建設在假想的基礎之上的。因為他們沒有具體接觸過檔案和檔案工作,只是把從書本上得來的有關(guān)檔案和檔案工作的印象當做研究對象而進行孜孜不倦、鍥而不舍的刻苦鉆研,其精神可嘉。對于本科學生,我們無可厚非,他們即將走上工作崗位,實踐會讓他們補上短腿的部分。而我們的碩士、博士們卻少有這個機會,將會沿著虛擬意識的道路走下去,直至成為檔案學研究的主力軍。我難以想象,檔案學研究會走向何處?我并非反對高學歷,但也要伴隨著對檔案實際的縱深認識,將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認識從虛擬走向?qū)嵲冢瑢n案和檔案工作要有實際的了解。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存在決定意識。沒有對檔案和檔案工作的深入接觸,怎么會有科學的檔案意識呢?為什么社會公眾沒有檔案意識,是因為他們沒有機會接觸檔案,也很少有人進入檔案館。公眾的檔案意識能靠檔案部門畫餅似的宣傳建立起來嗎?費孝通先生的社會學研究一直以江村為自己的研究基地,才有了巨大的成就。而我們的一些檔案學者從學校到學校,一直浮在書本上紙上談兵,有多少人有自己的檔案學研究基地?有多少人進行過實例解剖?有多少人在進行實證主義的研究?檔案意識并非一兩次的參觀、調(diào)研所能確立的。由于檔案意識的虛擬,沒有了觀念的羈絆,可以越過一切現(xiàn)實的障礙,任思緒自由地飛翔,不乏站著說話不腰痛的豪氣,有敢于說“不”的勇氣。厚道一點的干脆揚長避短,不懂的就不說,圍繞著檔案的外圍打擦邊球,在電子政務、信息管理、電子文件等領域若即若離,而少有人深入到檔案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去。我們都知道,檔案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也知道國外的檔案學家大都是從檔案館產(chǎn)生,對于檔案學研究來說,實踐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可當前檔案學界的時尚話題有多少是從檔案實際工作中提出來的?有多少是遠遠地脫離檔案工作實際的“屠龍之技”?眾多的“基于”類的文章有多少是基于檔案工作實際?有多少“范式”、“模式”能在實際工作中運用?這無一不是虛擬的檔案意識惹的禍。
檔案學界“虛擬”的走俏,正是一些檔案學者虛擬的檔案意識造成的結(jié)果。在虛擬的基礎上建立的檔案學也將是虛無縹緲的玄學。檔案不能虛擬,檔案館也不能虛擬,檔案意識更不能虛擬。檔案學不要再天馬行空了,而是要深入到檔案工作實際中再謀發(fā)展。
(摘自《檔案界》網(wǎng)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