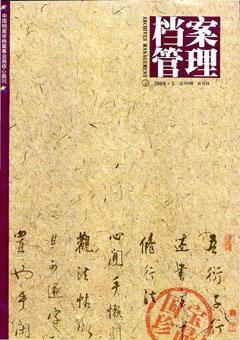由《檔案學論衡》引發的思考
羅富敬
摘要:發展“大檔案”思想,將可轉化為檔案的文件即檔案化的文件視為檔案的前端狀態,即可對諸多學者一直在爭論的文件為檔案學研究對象之說給予合理解釋,促使檔案學研究對象重新駛入正軌。
關鍵詞:檔案學;研究對象;文件;大檔案
1對檔案學研究對象認識的演變
閱讀陳永生教授的《檔案學論衡》一書,發現作者開篇即論述檔案學研究對象,顯示了作者對該主題的重視程度及其在整本書中的重要作用。關于檔案學研究對象,1986年吳寶康老先生在其《檔案學理論與歷史初探》這一專門研究檔案學理論與歷史的著作中,就把檔案學的研究對象表述為:“研究檔案和檔案工作領域內有關檔案的科學管理和提供利用的客觀規律以及檔案工作歷史發展規律。”吳老先生認為檔案學的研究對象是“檔案和檔案工作”,這個觀點代表了當時研究的最高水平,但隨著檔案學研究的不斷深入,這個觀點受到質疑,因為這種表述將檔案學自身排除在檔案學的研究對象之外,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缺陷。于是,1994年陳永生老師在其著作《檔案學論衡》中一開篇就指出了這個缺陷并提出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即他本人贊同的觀點:“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檔案現象及其本質規律。換句話說,檔案學就是研究檔案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這種表述,將一切檔案現象,包括檔案工作、檔案學、檔案工作者、檔案意識、檔案教育等都囊括了,代表著20世紀90年代比較前沿的研究成果。馮惠玲和張輯哲教授在2001年出版并于2007年修訂再版的《檔案學概論》中也采用了這一觀點。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認為文件是檔案學的研究起點,檔案學的研究對象不僅是“檔案現象”,還應包括“文件現象”。文書學(文件學)應納入檔案學的學科體系。把文件現象和檔案現象截然分開,把文件現象排斥在研究對象之外的認識,顯示出其局限性。2008年,鐘其炎也撰文表示同意這種觀點,認為在文檔一體化開展和電子文件迅速增多的今天,不將文件納入檔案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實在是不符合檔案工作實際。王茂躍、吳品才等學者雖對文件概念的細分意見不一致,但都共同認定一點,認為“大文件觀”的概念應為檔案學者重視。2008年,胡鴻杰在其力作《中國檔案學的理念與模式》中闡明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中國檔案學研究的邏輯起點是文件。這說明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文件在檔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2文件與檔案關系——將文件納入檔案學研究對象的適用性分析
2.1傳統文件與檔案的關系。我們知道,大部分的檔案是由文件轉化而來的,而文件辦理完畢,挑出有價值的部分予以保存之后就變成了檔案,今天的檔案是昨天的文件,今天的文件就是明天的檔案,即文件是檔案的前身,檔案是文件的歸宿。但要注意,并不是所有的文件都可以轉化為檔案,能轉化為檔案的文件只是眾多文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需要一定的條件:也并不是所有的檔案都是由文件轉化而來的,有相當多的一部分檔案是其他載體形式所承載的信息,其前身或許就是檔案,并不是由文件轉化而成。因此,說文件也是檔案學的研究對象,或許說服力還不夠,畢竟不是所有的文件都可轉化為檔案,因而所有的文件并不都是檔案學的研究范圍。
2.2大文件觀中文件與檔案的關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論認為:文件形成后的整個生命運動過程中,我們都可以稱其為文件,只是依據文件先后呈現出的不同價值類型。我們相應地分別稱其為現行文件、半現行文件和非現行文件。在此理論的指導下,我們發現文件包含了檔案,檔案也屬于文件。檔案是文件中的一部分,或者說檔案是文件運動至特定階段的產物或別名。以前我們對文件的認識是比較狹隘的,僅包括現行文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論中的文件就是一種大文件觀,認為文件自產生至其永久保存或消亡,其價值和保管方式會發生改變,或許其名稱也會發生改變,但它自始至終都保持其文件的性質。美國的著名檔案學家謝倫伯格早在幾十年前就已提出了文件雙重價值論,這也是基于大文件觀的。
根據文件生命周期理論在中國的運用情況,一些學者認為文件是檔案學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應該把文件也歸為檔案學的研究對象之一。但是,筆者認為,既然依照大文件觀中文件的概念,文件的性質貫穿了其從生至死的全程運動軌跡,檔案只是文件運動中某一個階段的特定產物或者說是文件運動特定階段的別名,那么,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就不是“檔案現象及其本質與規律”了,若改成“文件現象及其本質與規律”恐怕還會更加名正言順一些吧。這并不是筆者的一家之言,早在2008年,學者任漢中就已為學界鉆入文件的胡同中找不到明確方向而深感憂慮,呼吁檔案學研究應該回到以檔為本的軌道。
2.3大檔案觀中的文件與檔案的關系。有學者認為,所謂“大檔案”,指的是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全部對國家和社會有保存價值的檔案。其相對的概念“小檔案”,是指綜合檔案館保存的檔案及按傳統觀念應進館保存的檔案。這里的“大”和“小”,是檔案保存空間上的相對概念,大檔案保存的空間更大一些。包括一個城市、一個地區的檔案:小檔案保存的空間更小一些,僅包括一個檔案館的檔案。也有學者認為,“大檔案”是指將種類繁多的檔案門類都歸屬于檔案,都對社會產生了有利的作用。更有學者認為,“大檔案”就是將此后會轉化成檔案加以保存的文件看成是檔案的前身,對其進行檔案化的文件管理。筆者此處提到的“大檔案”是第三種觀點,認為“大檔案”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認為從檔案管理角度來看,檔案工作者倘若非要把觸角延伸到文件管理領域,那他可以把某些文件也視為檔案,即那些將來會轉化為檔案的文件,可稱作“檔案化的文件”,這個觀點并不是筆者自創,早在1997年澳大利亞著名的檔案學者在構建文件連續體理論模型時就已經指出檔案化的文件是檔案的前端部分了。如果站在這個角度,將“大檔案觀”中的檔案概念放人檔案學研究對象中,那么“檔案現象及其本質與規律”這一概括就已包括了能轉化為檔案的文件及已轉化為檔案的文件等的研究了。這樣,一些學者認為檔案學的研究對象中應包括文件及文件工作的觀點也被包括了進來。
3檔案學研究不變的主題:檔案——檔案學的研究對象的論證
3.1檔案本位主義對檔案學研究對象的影響。什么是本位主義?本位主義就是為自己所在的小單位打算而不顧整體利益的思想或行為。本位主義者缺乏大局觀和全局意識,考慮問題時往往以小團體為中心,無論利弊得失都站在局部的立場上,為了維護少數人的利益而忽視整體利益,嚴重的甚至不惜損害集體利益而換取部分人的私利。舉個日常生活中的實例,比如說,自己在等公共汽車,就希望車見人就停,不管是不是停點;如果自己坐在車上了,就希望別動不動就停,一路開到終點最好。這就是一種最典
型的本位主義思想。即做什么事情都從自身出發,不常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
同理,檔案本位主義就是說,檔案工作者在檔案工作的過程中,容易從自身出發去考慮問題,檔案工作者應該這樣、應該那樣,覺得權力越大、職能越多,就越有利于檔案工作地位的提高,或者是認為社會各界的其他工作都要為檔案工作提供便利,其他的社會工作都是輔助性的工作,一切以檔案工作為中心。當然,這并不是一個好的現象,容易造成一種“泛檔案觀”,即認為一切皆是檔案。
檔案工作者如果懷著檔案本位主義的思想,一切工作皆從自身出發,想讓其他社會工作都以自我為中心,很可能就會在不經意間造成越位或越權的情況發生。文件是和檔案比較相近的一個概念,文件和檔案兩者又存在轉化與被轉化的關系,因此,一些檔案本位主義者就會把文件也看成是檔案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說是檔案的一種前端處理狀態,于是,很可能就會把文件也認為是檔案學的研究范圍,為檔案學研究爭取更多的內容,如果檔案成為檔案之后,后面還有更多的形態的話,檔案工作者也一定會想方設法將其也歸入檔案學的研究范圍的吧,
所以說,眾多學者之所以會把文件看做是檔案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檔案本位主義心理作怪,殊不知,自己的事情都沒有做好,卻想去包攬別人的分內的事情,且不說有沒有能力做好,別人是斷然不會輕易將自己分內的事情交與你做的,不然,豈不是在搶人飯碗了?或許有人說每個行業都有本位主義思想這個潛規則,那么,文件工作者是不是也有著本位主義的思想呢?檔案是由文件轉化而成的,從這個方面來說,檔案是文件運動階段中的一個特殊形式,那么,檔案當然也屬于文件,這是不是就意味著文件工作者可以將檔案工作也納入其工作范圍呢?如果真能這樣,那么這經過了幾十年的歷程才慢慢發展起來的檔案學研究實在就沒必要存在了。
3.2文件連續體模型對檔案學研究對象的啟示。20世紀90年代,澳大利亞著名檔案學家弗蘭克·阿普沃德提出了文件連續體模型,該模型利用四軸四維的概念輔助我們理解文件連續體模型。在此模型的文件保管軸中,阿普沃德將檔案“數量”和“質量”的變化過程呈現出來,它們分別是(檔案化的)文件、(利用中的)文件、機關檔案全宗和社會檔案全宗。可以看出,在文件連續體模型中,阿普沃德將能轉化為檔案的文件與不能轉化為檔案的文件區別開來,他這里主要強調的是將來能夠轉化為檔案的文件。當然,站在檔案的角度來說,這些都是(檔案化的)文件,即檔案工作的一個前端狀態。這種把部分對檔案工作有用的文件納入檔案學研究范圍的觀點,正是筆者所認為的“大檔案”思想。檔案化的文件,是一種文件,同時,也是檔案,這為檔案工作在電子文件時代的前端管理和全程控制思想提供了條件保障。從文件連續體理論可以看出,檔案是檔案工作的主要內容,也是檔案學研究的對象。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圖書情報檔案系來稿日期:2009-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