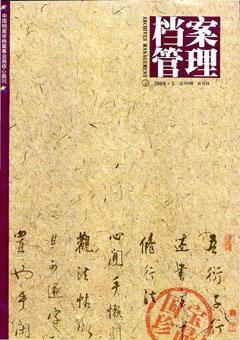兄弟檔案核心期刊文摘9則
胡紹華
論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共性與差異
匡定發、吳文革在《檔案學通訊》2009年第3期撰文,就上述命題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分析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共性與差異,有助于準確把握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相互關系,進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制度建設,推動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進一步發展。
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共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戰略性和政治性的社會地位相同;二是客體對象具有資源性和無密性:三是義務主體履行職能的政府主導性:四是開放方向和服務對象的同一性:五是基本要求相近;六是目的、目標或結果相同。
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差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主要目的不同;二是客體對象同源但內涵有別;三是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在其活動與運行的方式、程序和便民性等方面都差異較大:四是政府信息公開與檔案開放的時效性要求差異很大。
數字檔案館、電子文件檔案館和電子文件中心辨析
肖秋會、楊青在《檔案學研究》2009年第2期撰文,從國內外數字檔案館、電子文件檔案館和電子文件中心的建設情況分析入手,論述三者之間的共性和差異。
作者認為:數字檔案館、電子文件檔案館和電子文件中心都是為了應對數字環境下檔案信息與保管和利用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是它們在建設背景下的共性。
其差異主要表現在:一是名稱上的不同;二是保存檔案成文件的久暫性不同:三是管理的主要對象不一樣;四是管理功能上的差異;五是工作宗旨的不同。
深圳市開展文件集中管理的實踐與思考
方燕在《中國檔案》2009年第4期撰文,系統回顧和總結了深圳市開展文件集中管理的過程和經驗。
關于深圳市開展文件集中管理的時代背景,主要有四:一是適應政府職能轉變的需要;二是經濟高效化的需要;三是信息化建設具備一定基礎;四是適應文件生命運動規律。
關于深圳市開展文件集中管理的實踐:一是由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立法,明確“文件中心”的機構設置和深圳市機構編制委員會批準建立文件中心并明確其職能;二是由深圳市檔案局先后制發了《深圳市機關、團體、事業單位文件集中管理辦法》等一系列規范、標準;三是從2006年起開展了電子文件接收管理系統的研制開發,建立了電子文件中心與數字檔案館一體化系統架構及三級管理模式與應用系統建設;四是在深圳市市民中心檔案新館落成后,其文件中心開始全面履行其職能,開展了對駐市民中心的26個單位的文件接收、保管與利用工作。收到了初步的成效。
關于經驗和體會。經驗有三:①應加強文件前端控制,以保證檔案的完整性與安全性;②應采取強力措施保證文件的真實性,提高檔案的可靠性與效力性;③應實現有效監管,保障檔案的管理質量與效率。體會也有三:①實現文件全程統一管理是提高文件管理質量的必要條件;②健全的文件管理法規體系是文件集中管理的根本保障;完善的安全措施是文件集中管理的可靠前提;③便捷的利用服務是保證文件集中管理的根本目的。
談重大災害聲像檔案的拍攝與收集
陸志剛在《檔案與建設》2009年第5期撰文,以其參與“5·12”汶川特大地震災情與災民生產、生活情況的拍攝經驗,對此問題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①加強重大災害聲像檔案的拍攝與收集,能為今后工作查考、歷史研究、賑災減災和城市建設提供重要參考。②第一時間迅速介入重大災害聲像檔案的拍攝與收集,是檔案工作者真實記錄歷史的神圣使命。③實地實時拍攝,是重大災害聲像檔案獲取最快速、最直接的方式。為此,應強調拍攝的及時性、準確性和全面性,強調器材和畫面的高質量性。④全方位多角度拍攝,是反映拍攝主體和內容的全面性、準確性的重要保證。⑤面向社會收集照片,是彌補重大災害聲像檔案不足的重要手段。⑥配備高素質的攝像人員。是保證重大災害聲像檔案完整齊全的關鍵。
以民生檔案基礎數據庫建設為重點,加快檔案信息資源開發利用
梁紹紅在《浙江檔案》2009年第3期撰文,就建立民生檔案目錄數據庫和開展民生檔案全文數字化過程中所遇到的共性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一是要把保護原件作為民生檔案數字化的重要目標。二是要統籌考慮檔案數字化的效益問題。民生檔案被利用的概率很高,有的案卷和文件的利用率甚至達100%。優先對這些檔案進行數字化,不僅可以較好體現檔案部門的開放理念和服務姿態,而且數字化的整體效益也非常突出,三是根據不同民生檔案的特點確定其數字化的范圍。四是要處理好民生檔案利用中的保密和保護隱私問題。
從檔案收集到知識積累
徐擁軍在《山西檔案》2009年第Z期撰文,就知識管理環境下如何做好檔案的收集工作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
第一,要樹立“大檔案觀”,按知識資源體系擴大檔案的收集范圍。組織的知識資源包括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隱性知識是指難以用語言文字表達,存貯在員工大腦中的知識。顯性知識是指易于用語盲文字表達,記錄于紙張、磁帶、磁盤、膠片等載體上的知識。顯性知識又分為內源顯性知識和外源顯性知識。內源顯性知識主要來源于組織自身各項職能活動中直接形成的文件、檔案;外源顯性知識主要來源于組織通過采集、購買等方式從外部獲取的書籍、報紙、期刊、資源、數據庫等。
第二,要注意生成文件、固化隱性知識。隱性知識管理的一種重要途徑就是隱性知識顯性化,即通過生成記錄將隱性知識“編碼化”或“固化”于文件之中,使之轉化為顯性知識,然后通過文件的傳遞與利用實現顯性知識的價值。要使隱性知識顯性化,需采取以下三種方法:一是程序化生成文件。即對員工工作過程進行客觀記錄,使之生成文件;二是總結性形成文件,即通過工作結束后的回顧與反思,使工作中的經驗、體會得以留存;三是彌補性生成文件,即通過“口述史”的采錄來彌補可能被遺漏或不完善的知識。
第三,擴大文件歸檔范圍,控制內源顯性知識。包括:對非正式或一般性文件的歸檔;對電子文件的歸檔。
第四,收集外部信息,獲取外源顯性知識。
傳統檔案服務向知識服務過渡研究
徐擁軍、陳玉萍在《北京檔案》2009年第4期撰文,就傳統檔案服務如何向知識服務過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①在服務理念方面,要由以檔案機構為中心向以用戶為中心轉變;②在服務目的方面,要由為用戶提供檔案向為用戶提供知識轉變;③在服務主體方面,要從由單個員工提供服務向由專家團隊提供服務轉變;④在資源基礎方面,要由基于分散的檔案資源向基于集成的知識資源轉變;⑤在服務方式方面。要由被動服務向主動服務轉變;⑥在服務手段方面,要由機構化服務向智能化服務轉
變;⑦在服務策略方面,要由標準化服務向個性化服務轉變;⑧在服務過程方面,要由階段性服務向全過程服務轉變;⑨在服務時效方面,要由滯后服務向超前服務轉變。
傳統檔案與現代檔案的判斷標準芻議
劉巍、王世福、劉志芬在《檔案》2009年第1期撰文,從分析檔案學界提出的“檔案物質實體雙重構成”的新觀點入手,指出:所謂“檔案歷史聯系的記錄”,是指檔案歷史聯系整理勞動的物化成果,是專門揭示記錄和固化檔案歷史聯系的,并提出了“檔案所具有的歷史聯系的程度是判斷傳統檔案與現代檔案的根本標準”的觀點。作者認為,只是依據“事由”或“來源”形成一維的檔案歷史聯系的記錄,即為傳統檔案;而同時依據“事由”、“來源”和“年代”形成三維的檔案歷史聯系的記錄,即為現代檔案。確定這樣一個判定傳統檔案與現代檔案相區別的標準,是基于以下三點考慮:一是使判定具有客觀性和實在性:二是使判定具有可操作性;三是使判定具有本質性。
基于上述認識,作者認為:檔案的載體形態不能成為傳統檔案與現代檔案的分水嶺。因為檔案的載體形態不是區分傳統檔案與現代檔案的決定因素。對于傳統的紙質檔案,只要將其歷史聯系的記錄轉化為多維的結構,它就可以成為現代檔案:而如果電子檔案的歷史聯系的記錄仍然保持傳統的一維結構,那么它仍然是傳統檔案。
此外,作者還引申出一些針對傳統檔案和現代檔案的相關認識。
從整理民國時期軍隊檔案看如何優化檔案整理工作
劉宏亮在《蘭臺世界》2009年5月上半月刊撰文指出:在參加對館藏民國時期軍隊檔案的整理中。深切感受到檔案整理對檔案利用的重要作用,對如何優化檔案整理工作也有新的認識。作者認為:
第一,應把史料價值鑒定作為檔案整理的重要內容,使其在整理過程中得以優化。檔案價值鑒定是檔案整理工作的基本內容,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檔案整理的質量以及館藏的優化。為此,在整理過程中,應根據事先確定的原則,對檔案材料進行必要的篩選和區分,對確實沒有利用價值的材料,應按照規定程序呈報有關部門進行妥善處理。
第二,應把檔案整理與檔案編研結合起來,使整理過程成為研究利用過程。為此,一是檔案整理人員要帶著編研課題去整理:二是檔案研究人員應盡可能參加檔案的整理:三是應加強整理人員與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合作。
第三,要用多維視角進行檔案整理,使檔案價值得到全面體現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