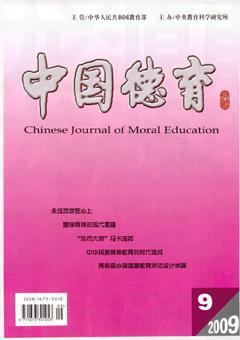“榜樣”:被修飾了的校園模具
武秀霞
在當前的學校教育中,榜樣有點“成災”。如果 “榜樣”真能在數(shù)量上超過了人們的可接受能力,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是現(xiàn)實中“榜樣”不是數(shù)量過剩,而是力量被推崇到了極致。如今的“榜樣”群體,其強勢力量正日益膨脹,榮譽的“光芒”足以照亮其整個人生旅程。因而,“能夠成為榜樣”幾乎成為今天每個學生的目標:他們?yōu)榭荚嚩喃@一分而拼命,為受到周邊人的好評而背離自我甘愿套上虛偽的外殼……
一、人本非“完人”:“榜樣”衍生的弦外之“因”
長期以來,學校教育者們都將“榜樣”篩選視為上好的評價和激勵機制,認為教育對象只是一群不完整的可“塑”之“材”,甚至認為那些尚未接受教育的孩子與一般的動物相比,除了具備更大的可塑性外,并無什么差別。盡管德國哲學家、人類學家 H?普勒斯納把人視作是一種文化生物,將人與一般的動物嚴格區(qū)別開來,但其同時也默認,人生來就是一種“有缺陷的生物”,是尚未確定、仍不定型的,其本質(zhì)還處在發(fā)展中,因而每一個人一生中都需要不斷地發(fā)展和完善。而且,人在其所成長的每個階段,本來就在有意無意關(guān)注他人的行為、思想,不斷地利用自己的模仿能力去適應(yīng)周邊新生的環(huán)境。這于是顯現(xiàn)出我們對外界文化的汲取和適應(yīng)之需。如此,那些由于甘愿模仿而失去自我的學生,是否可以說咎由自取呢?校方在這個過程中真的沒有什么過錯嗎?
因為抓住了學生與生俱來的這一特點,學校一直以來都在不斷地籌劃、規(guī)范、塑造某些適合他們口味的模板,將那些已被塑造得近乎完善的學生視作一個個精美的“藝術(shù)品”,并為其“披紅掛彩”,命名為“榜樣”,引來旁人乃至尚未懵懂的普通學生的嘖嘖贊嘆!更可悲的是,那些本來可以慶幸自己未被型塑,故可以找到自我的非“榜樣”學生們,卻在這種激烈的榜樣評選競爭中喪失自尊,否定自身。這究竟是為什么?“因為你還不夠完美、不夠完善!照著“榜樣”的言行去做吧!”冥冥之中,一個弦外之音在學生們的耳邊響起。如此,體系化的“榜樣”就這樣理所當然地建立了!
或許,那些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教育者們會就此而想到理想的托辭:我們是為了學生的完善,為了讓他們有效地、更快更好地認識他們先天的不足,并且試圖努力完善之。這個過程體現(xiàn)的是學生個體對其自身自然性的不滿足、否定和揚棄,是一種“超越”意向!他們也許還會搬來存在主義的理論來證明為學生設(shè)立規(guī)范的合理性——人的存在是一種虛無。這就說明,我們無法為自身訂立一個確定的遙遠的目標。做好眼前工作,確立一個近期的目標以供追求,然后再探索下一個奮斗的方向才是現(xiàn)實,而榜樣就是眼前最理想不過的奮斗目標了。然而,他們?nèi)绻娴倪@樣去定義學生的發(fā)展路線,恐怕學生的生存樣態(tài)只是一種非連續(xù)的“超越”意向,他們極易在途中迷失自我,導致人生之路的碎片化甚至扭曲。
當然,教育者們設(shè)立“榜樣”的初衷或許的確出于“善”的期望,因為教育的使命本就在于幫助人成為“人”,保證人的持續(xù)性發(fā)展。或者換句話說,讓一個生來未成熟的人在社會當中有一種“生活能力”。這種“生活能力”,正像布列欽卡所說,是一個人在他所屬的社會中能夠獨立生活、承擔社會責任、感受到一種意義感和幸福感所需要的必要的能力、知識和觀念的總和。然而凡事被看得太重,被推崇到極致都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
二、被廢棄和固化著的生命:“榜樣”模具塑造的代價
我們固然無法否認“榜樣”在提供給學生前行的方向之感以及前進的動力方面的獨特功效,但是,任何一種事物如果過分強調(diào)就容易背離初衷,導致異化。“榜樣”也非例外。目前榜樣正是處于這樣的境遇:由激勵轉(zhuǎn)變?yōu)椤耙?guī)訓”。那些有形有色的相關(guān)活動以及那些“榜樣”稱謂的載體都漸淪為一種“符號”,有名卻無實——提到“榜樣”,人們頭腦中浮現(xiàn)的僅僅是一系列的官方標準,而榜樣的載體,如某些“三好學生”“優(yōu)秀學生”稱號的獲得者,淪為了學校篩選出的模具。為了讓學生發(fā)展,不斷超越自己,教育者往往在平日的教育活動中,通過營造諸多競爭性氛圍向?qū)W生灌輸某種“求勝”心理。他們設(shè)立“三好學生”等“榮譽稱號”,將獲得者視為供他人仿效的“榜樣”,似乎在暗示:像某某做才是優(yōu)秀的。
誠然,教育攜帶一定的規(guī)訓因子在某種程度上是必需的,因為我們需要獲得包括個體對社會的適應(yīng)力、責任心等在內(nèi)的生活能力,這些能力的獲得即隱含著個體對社會規(guī)范的某種認同。然而,倘若只強調(diào)規(guī)范,人就無法形成起碼的判斷能力(而這種能力卻是一個人獲得生命的意義感和幸福感所必需的)。這也就是說,教育的功能領(lǐng)域并不僅僅局限于人的社會化,而是從根本意義上讓人成為一個人。這個“人”是一個主體人,而不單單是社會人——“主體人”區(qū)別于“社會人”就在于他是人生意義的自我掌控者,是擁有理性的自由、自主性,持有“我、你”人際關(guān)系之信念,存有人類共契價值的個體存在。那種僅僅強調(diào)對規(guī)范、標準的遵從的教育等都只是一種極端化的“規(guī)訓”,甚至是為社會培養(yǎng)一種“工具人”。而現(xiàn)實的教育對于“榜樣”的設(shè)立,對于獲得這類榮譽的學生的評價、篩選過程,體現(xiàn)的恰恰是“規(guī)訓”壓倒了“超越”。
從學校教育中一路走過來的人,回顧一下自己的人生歷程,首先浮現(xiàn)于腦海中的不過是無休止的學習、考試、評比、排名。曾經(jīng)的榮譽、成績似乎并沒有為他們的有意義人生帶來什么,反而是失落甚至是某些重要素質(zhì)的遺失。之所以這樣,很大的原因在于,教育對于包括“誰應(yīng)當成為榜樣”,什么樣的標準就可以成為“榜樣”等在內(nèi)的評價機制總體現(xiàn)為一種“定性”色彩。一方面,這些評價機制如今依然一如既往地將核心定位于學習成績上,那些所謂“榜樣”的入選者需要具備的條件,往往是靠前的成績排名。只有排名達到規(guī)定要求的學生才有資格考慮各類榮譽稱號的爭取。這一定程度上促發(fā)了一種現(xiàn)象,那就是學生為了爭取某類“稱號”而拼命攻讀,試圖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尊嚴”所在。“成績”“榮譽”成為他們的學習目標,而學生自身則成為“榮譽”的奴隸,其本應(yīng)得到發(fā)展的生命因此而固化。另一方面,“榜樣”的授予,遵循的往往是少數(shù)原則甚或“一貫性”“連續(xù)性”原則。某一特定角色的承擔者只占群體的極少數(shù),縱使參選學生多于預設(shè)名額,校方、教師也會毅然決定從中再次“篩選”,將獲選的學生推上榮譽的殿堂。而一旦該生獲得了此種榮譽,其后來榮譽的獲得會變得更加容易,似乎這是人的慣性心理所致,認為“榜樣”就是出色的,不會改變。
然而,那些“三好學生”“優(yōu)秀學生”等榮譽稱號的載體(即少數(shù)成績突出的學生)實際上只是一個符號,一個品牌式的代言人,由于其恰好符合了學校預先設(shè)立的“榜樣”標準而暫且被推上了榮譽的領(lǐng)獎臺,學校也借此向其他學生聲明,那些“三好學生”“優(yōu)秀學生”的行為、做法才是恰當?shù)摹⒄_的。對于那些與這類標準相背離的或是那些行為反叛的學生,等待他們的是懲罰,是被“拋入”另一種模子的“差生”“問題兒童”,是“被廢棄的生命”。這類“模子”與“榜樣”形成鮮明對照,其事實上是在突出“榜樣”的優(yōu)越性。至于那些按“規(guī)律”學習卻難見起色的學生,學校、教師也為他們設(shè)立“進步獎”等諸如此類的榮譽,在相應(yīng)的群體中營造“競爭”氣氛,尋找少數(shù)優(yōu)勝者。如此,一種似乎完備的“榜樣機制”就在“有獎勵,有對比”的教育氛圍中建立起來了。然而,這種過于強調(diào)學習成績,加上那些相應(yīng)的長期不變的評價標準體現(xiàn)的正是一種極端化的“規(guī)訓”,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動物式的“訓練”,這是榜樣成為純粹“符號”的問題所在。
三、“我”是誰:“模具”的控訴
“榜樣”的載體是“人”,榜樣的符號化即意味著人的符號化,意味著個體成為片面的、不完善的,甚至是被某種特定的“符號”所規(guī)訓、驅(qū)使和奴役的“工具”。其表明“符號”存在的意義大于人自身的價值意義,這導致的后果便是“特性角色”的形成,便是學生“自我”被“榜樣”的光芒所掩埋。
“特性角色”在麥金太爾看來,指向那些在人數(shù)上非普遍的被賦予特權(quán)的社會階層。這些人擁有供他人模仿的特權(quán),擁有許多普通人所不具備的“優(yōu)點”。社會給他們許多特權(quán)以及贊譽,正是為了鼓動其他的普通民眾去效仿他們,以其為“榜樣”。他們是“由社會挑選出來的‘典范”,是“體現(xiàn)著社會的道德理想,具有文化代表意義和履行某種重要社會功能的‘角色”。依照這種看法,校園“榜樣”作為日益膨脹的勢力群,也同樣在不斷地充斥著其它級別的群體文化。這些長期壟斷各類榮譽的學生正是校方公認的最優(yōu)秀的典范,他們即是校園中的“特性角色”。
然而,這些榜樣真的如此優(yōu)秀嗎?他們真的是一些充實了自我、品味到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的“人”嗎?問問這些曾經(jīng)充當過學校“特性角色”的人,回顧其走過的人生,他們是因此得到了更多還是失去了更多?問問那些一直與“榜樣” “特性角色”無緣的人,他們是否因為那些角色的存在而失去了其本該有的東西?事實上,這種所謂的“文化代表”只能是有限群體內(nèi)的代表,這類代表的思想、行為只是在有限的生活圈中適合了某種規(guī)范。他們相應(yīng)的典型行為被過分地強調(diào)、拔高,而其它的部分則被舍棄。在這些被舍棄的東西中,不少很可能正是他們自身真正具備的“優(yōu)良素質(zhì)”。這導致的結(jié)果,不免會是片面的發(fā)展,是“自我”的遺失。那些憑借學習成績充當過所謂“特性角色”的人,隨著其人生履歷的增長,很有可能會發(fā)現(xiàn)原來那種顯赫的聲譽并不一定帶給其多少有意義的東西,甚至阻隔其獲得許多人生本該擁有的體味。另外,那些在學校中未曾成為“榜樣”的人,由于他們自身本有的良好素質(zhì)沒有得到明確認可,而可能多次與“發(fā)掘自身優(yōu)點”的機會擦肩而過。他們甚至衍生自卑心理,放棄自己本應(yīng)有的超越意向,而盲目向著“榜樣”的規(guī)范型塑自身。殊不知,那些由教育者擬定的評定標準本來就蘊含很多主觀因素,正像麥克?F?D?揚所說,教師眼中的所謂能力較強的學生也就是在學校能力分組中位列較高的學生,只不過是接觸了并且愿意接受教師規(guī)定的概念。因為教師通常認為A學生的行為是正確的,所以他們學習知識的方法也是恰當?shù)?于是正確的學生行為就等同于他們的學習能力。這不一定說明他們有能力在更加概括、抽象的層面上掌握知識。如此,那些成為榜樣的以及尚未成為但日夜渴望成為榜樣的人,其實現(xiàn)的或者所追求的是否可以說,只是一種“他者化”的“我”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自我”呢?
回歸麥金太爾關(guān)于“特性角色”的描述,即可看出,這種“特性角色”蘊含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種貶義,其攜帶有許多負面性因子,如道德的淪喪、自我的遺失。對于那些擔當“特性角色”的人而言,其由于僅僅充當著某些空洞的符號稱呼,他們的所言所行總是充滿著被動——這一角色(或者符號)要求他們怎么做就怎么做,其似乎從未慎重地思考過自己的人生意義是什么,自己眼前所做的有什么實在的價值。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會把自己的角色視為一種快樂,然而這種快樂能維持多久卻令人置疑。而對于那些與“榜樣”體驗無緣的人而言,由于難以得到教育者的贊可,他們失去了諸多發(fā)展、認識自己以及發(fā)掘自身優(yōu)點的機會,這是否也是一種悲劇?這種悲劇由誰導致?恐怕異化了的“榜樣”機制無法脫離干系。
如果那些曾經(jīng)為了擁有和維持“榜樣”稱號(或榮譽)以及那些為了爭取這個符號而拼得你死我活卻收不到半點成效的學生,他們在后來發(fā)覺到了“自我”的遺失,并且為此而感到痛苦和遺憾,那么,其心中是否會燃起痛徹心扉的控訴:我是誰?我在哪里?是誰剝奪了屬于我自身的東西?也許他們中的一些人始終會處于模仿他人的混沌和麻木中,甚至享受著因此而帶來的某種快樂,如此,其只能是喪失生命本真的“孤魂野鬼”了……為避免或減少這樣的悲劇發(fā)生,恐怕盲目或者過分推崇“榜樣”機制的每一個人真該好好想一想了。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江蘇南京,210097】
責任編輯/劉?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