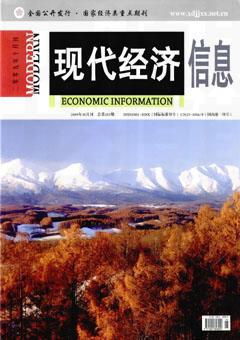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
摘要:《史記》是我國古代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開創了為經濟立傳的先河。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闡明了他的經濟觀點,在承認人的趨利本性的基礎上,主張國家應順應經濟規律,農、工、商、虞四業并重,市場自由貿易,這樣才能民富國強,促進社會的發展。他支持人民經商致富,認為仁義道德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并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論”。
關鍵詞:司馬遷 《史記?貨殖列傳》 經濟思想
司馬遷是我國古代偉大的史學家和文學家。他傾畢生精力寫成了一部巨著——《史記》,完成了父親的遺愿,盡了史家之職責,了卻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理想。《史記》作為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紀傳通史,奠定了史學有獨立地位的基礎,同時還做出了許多創舉。其中,《史記?貨殖列傳》、《史記?平準書》開創了經濟列傳,證明司馬遷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狀況對社會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這在當時“重農抑商”的政治環境中,不能不說他不但具有史家實錄的精神,而且還有大無畏的精神,言別人不敢言之言,做別人不敢做之事。研究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對今天經濟社會的發展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基礎——對人的趨利本性的認識和肯定
司馬遷主張經濟社會的發展既要盡物之性,還要盡人之性。他的自由經濟思想,包含了尊重自然規律,充分地利用或者順應人和物本性的內容。司馬遷所謂的對人性的理解主要是以人們的趨利本性為基礎的,他能為致富者立傳就已經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場。他認為,人們對利益財富的追求是一種天性,是一種非常自然的本性,是不用學而與生俱來的。正所謂“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1]因此,他列舉了多方面的事實證明人具有趨利的自然本性。“賢人深謀于廊廟,……歸于富厚也。……壯士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不避法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出不遠千里,……奔富厚也。悠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戈射漁獵,……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弛逐,斗雞走狗,……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2]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3]它不但肯定了人的趨利本性,還肯定了人民追求自身利益的正當性。“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4]他說這些人“皆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奸”,而是“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5]他們不做官,不殺人越貨,根據市場經濟形勢的變化即時應對,獲取利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這就是為什么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提出的經濟思想在今天我們看來依然先進,就在于他抓住了人的本性和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對物性的理解。司馬遷認為:“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6]他還引用管仲的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明白“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7]這就是說,由于財富,編戶的貧民,對比自己財富多十倍的人就要屈服,對多百倍的就要害怕,對多千倍的就要受他役使,對多萬倍的就要做他的奴隸,這是事情的道理。糧食充實,人民才知道禮節;衣食足夠,人民才知道什么是榮譽,什么是恥辱。禮節是產生于富有之時,而消失于貧乏之時。所以貴族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小人富有了,就能做好工作。河水深了,魚兒自然就產生;山岳深了,野獸自然就棲息;人富有了,仁義自然就歸附。富人得了勢,名聲就越顯赫;失了勢,門客離去,就不快樂了。說明財富占有情況決定奴役別人或受人奴役,禮節道德離不開一定的物質基礎。在兩千年前,并且西漢初年就已經頒布賤商令的情況下,司馬遷能朦朧地認識到這一點,體現了他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二、司馬遷看重商業,主張四業并重,順應經濟規律
司馬遷認為社會經濟活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他看重貨殖,強調農虞工商四業并重,缺一不可,只是自然分工的不同,是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他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貨殖列傳》和《平準書》中。《貨殖列傳》以文景時繁榮的社會經濟為背景,描述了漢初經濟的上升景象,肯定商人的歷史作用,鼓勵發財致富。《平準書》則概述了漢武帝時期經濟的滑坡趨勢,諷刺當時的“重農抑商”經濟政策。兩種背景,反襯對照,形成鮮明的對比,生動地描述了漢初至漢武帝時代西漢經濟的形勢變化,表達了司馬遷進步的經濟史觀。在漢代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司馬遷在考察各地情況之后,意識到商業必然興起的歷史發展之勢。他認為,中國人民喜好的、人們奉生送死的物質生活資料要“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們不可能直接生產他們所需要的所有生活資料,肯定了商人的橋梁作用。他還引用《周書》的話,“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認為“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而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把這四者看作是衣食之源,肯定了農、虞、工、商在社會生活中的不同作用,農、工、虞乃生產之本,但如果沒有商的流通,將裹足不前。在《貨殖列傳》中司馬遷用大量篇幅描寫了各地物產和商業流通情況,并指出商業流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這四者只是社會的自然分工不同,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
社會生產的發展是有規律的,國家應當為人民致富創造條件。司馬遷引用了計然的這么一段話,“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8]司馬遷認為這段話講了一些商品經濟規律和經濟政策。第一,經商如同打仗要懂得戰爭和戰備的關系一樣,必須明了商品和時間的關系。掌握二者關系,就掌握了經商之道。第二,要了解年成的好壞,提早做好物質準備。第三,把握好糧食價格,合理調整物價,既不損害農民又不損害工商,價格合理,市場興旺。第四,要懂得商品貯存的道理,一定要貯存好的易藏易售商品,不要屯積易腐敗、腐蝕貨物以求高價。第五,根據市場價格高低的辯證關系,決定貨物的拋售與囤積。第六,要搞好貨幣流通。這實際上講了時間和商品的關系,商品價格,貨物貯存原理及貨幣規律等問題。范蠡運用計然這些經濟理論使越國“修之十年,國富”,報了吳王夫差滅國之恥,“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從司馬遷引用計然的話和列舉范蠡以末業興越的例子,可以看出司馬遷發展商業、繁榮經濟推動社會發展的觀點。另外,白圭的“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做法,也是對經濟規律的尊重和運用。
三、市場對經濟活動有自發的調節功能,主張自由貿易
司馬遷認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懼欲者也。”他承認一切正當的求富行為都是天經地義的。人民生存,就要消費,這是自然規律。由于各地風物之差異,人們又有不同的分工。那些中國人民喜好的“謠俗被服飲食送死之具”,各行各業的人會“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征貴,貴之征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也?”[9]意思是各行各業的人都從事他們的專長,竭盡他們的力量,去求得他們的欲望。所以物價賤時,人人要買,這就是漲價昂貴的征兆;物價貴時,人人不買,就是跌價賤落的征兆,這都是自然調節的。人人勸勉他們的職業,愉快他們的工作,好像水往低處流,日夜沒停止的時候。不必去征召,他們就會自個兒工作;不必去請求,他們就會出產貨品。以上一切,不都符合“道”和自然應驗嗎?因此,基于這樣一個思想,司馬遷主張自由貿易,自由貿易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司馬遷看重商業正說明了這一點。
這在競爭中,必然優勝劣汰,即“巧者有馀,拙者不足” ,“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司馬遷認為這種現象也是正常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即使貧富兩極懸殊,出現以富役貧,也是不足怪的。在司馬遷眼中,貧賤是可羞的。“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10]意思是,如果沒有像山巖隱者的真正清高品行,而卻長久貧賤,愛談仁義,這真是羞恥的事。對于這種社會現象,他主張貧富自然演變,政府應當不予不奪,希望人們能夠通過勞動和才能達到致富的目的。嚴格地講,司馬遷的“富利”觀其實是“義利”觀。他并不輕看意識形態對經濟活動的制約作用,也十分贊成以儒家之禮義給人們以教化。他認為每個人都有欲望,欲望得不到就會發憤,發憤無度就會有爭斗。是故先王“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11]他反對“奸富”,認為“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12]明確排除那些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的行為,對這些人主張在教化不能奏效時,應當輔之以刑罰的手段。基于這樣的認識和主張,司馬遷還對封建統治者的經濟政策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13]的建議。最好的方法是順其自然發展,其次順勢引導到好的方向,再其次是教訓他們,又其次是用壓制的手段使行為齊一,最下等的方法是用武力奪取他們的需求。這些觀點和主張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精華,也是他對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經濟學說的重大貢獻,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通讀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它是記述古代商賈經商致富影響社會生活的一篇文章,文章以肯定人的趨利本性為基礎,闡發了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所以,我們應該順應經濟規律,農、工、商、虞不可偏廢,市場自身有其調節功能,政府應“善者引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站在“中國人民”的角度肯定了“素封”的正當性、合理性。所以,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解釋他為什么要寫《史記?貨殖列傳》時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14]贊揚了那些憑著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創業致富的“布衣匹夫之人”,專為他們立傳。研究司馬遷的這些經濟觀點和主張,在今天仍不失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注釋:
[1][2][6][10][12](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5.
[3][4][8](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2.
[5](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7.
[7][9][13](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51.
[11](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122.
[14](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769.
參考文獻:
[1](西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2](漢)司馬遷,白話史記:白話全譯本[M]成都:新世紀出版社,2007年版.
[3]朱宗宙,商道中“勢”的認知、“術”的運用和“責”的歸宿[J].揚州大學學報,2008,12(6):30-34.
[4] 陳小赤,略論司馬遷經濟思想的先進性[J].理論導刊,2008,2:116-117.
[5]張友彬,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J].文史博覽,2008,5:12-13.
[6] 張俊,論司馬遷的因俗變遷經濟觀及現代價值[J].上海經濟研究,2008,2:106-112.
作者簡介:李愛民,女,河南濮陽市戚城文物景區管理處,館員;廣西師范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