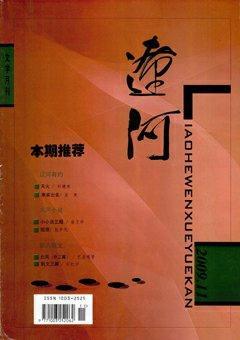且聽風吟
方 萌
那年清明,我二十九歲。我同父親穿行在千佛山的松林里。
因是清明,山間陰濕有涼意。父親的黑格子夾克衫被山風裹挾著,在他瘦削的背上吹起大大的包。我隨他身后保持著一兩步的距離,腳下山間小道的石板臺階經風吹雨浸后是一種乳白色。石板縫隙里有螞蟻進進出出地忙碌著。父親在路旁一棵捆綁著“嚴禁煙火”大鐵牌的松樹前停下,對我說,從這里往下行應該就是了。有生以來,我和父親的腳步在同一條路上沉重,有著同一種心情。但我想,這種沉重不會再有第二次了。
祖父的墓地周圍沒有石柵欄,也沒有其他屏障,只有一棵巨大的古樹。而樹干離地面半米高處有一很大的樹洞,好像一個虎口在向我們父子大張著口。出于好奇,我把頭伸進去看,那里面似乎混雜了這世界上我從未目睹過的黑暗。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見。
父親把我喊過去,開始給祖父祭墓。他從我手上接過當年他們父子常喝的那種“糊涂仙”酒,滿滿地斟了三大杯,然后便也叫我俯身跪下,緊接著就聽父親的聲音嗚咽起來。只聽他說:“爸,我和您的孫子方萌來看你了,這是您最愛喝的‘糊涂仙酒,請您再喝一杯吧……”
四周潮濕而陰暗,這時有微雨落在我們父子的臉上。我從正面凝望著略顯低矮的墓碑與上面斑駁的文字,我看見文字上方似乎有一洼霧水慢慢凝聚成一雙蒼老的眼睛在盯著父親看。我屏住呼吸將懷中那束潔白的鮮花恭恭敬敬地放在石碑下方,花兒飄出清香,淡出光彩,墓碑上好像又有了生命。山風在淺吟低唱,酸楚微雨,縹緲悲泣,然后還有那不確定的生死距離。一切的一切,都讓我難以釋懷。
下山路上,我有些惶惑不安,我問父親:“爺爺會喜歡這里嗎?”父親沒有立即回答,而是沉思許久才說:“應該不會吧?莊稼人就愛一望無際的田野和牛羊,但你奶奶卻喜歡這里。”
奶奶在時我還小,曾聽爺爺說,她是我們全家當年的“偉大舵手”,是她用超前的理念將全家從鄉村帶到縣城,把七個子女一個個推進大學校園,而后他們便撒向大江南北。她的功勞和形象對我來說雖然有些模糊,不比在爺爺背上的記憶來得親切,但也讓我滋生出了許多的懷念和愛戴。
聽了父親的話,我在他的身后突然就有了一種想表達出來的欲望,我說,我要給爺爺奶奶寫篇文章。然而父親卻說:“這想法我早就有過,但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一樣,假如寫不好,怕會玷污了他們一生的善良和清白。”
那一刻,我欲言又止。
然而,當我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時候,卻已是一年之后的又一個清明,地點竟是在我們居住的縣城以北一個叫“龍山”的父親墓地上。那兒沒有張著大口的樹洞,也沒有透著滄桑的大鐵牌,只有一束和去年送給爺爺一樣的白色郁金香,及一瓶他和爺爺都愛喝的“糊涂仙”酒。
可是,爸爸走得太匆忙,太匆忙了。
就在這一年,我談了個女朋友。又到清明節的時候,我便同她帶了一些父親的遺物到墳前焚燒。這雖然令母親有些不快,但我堅持去做,因為我要燒掉母親的全部哀思。父親是個瞇著眼睛看世界的人,他的性格與祖母相似,干起事情來風風火火。他走的時候外面是寒風呼號的冬夜,是母親伸出手為他合上眼瞼的。母親說他是個有思想,有執著信念和追求的人,而我更贊同后者。母親一有空閑就翻看父親未完成的攝影作品集。父親拍過無數張圖片,每一張都記錄著一種心境。女友說,她也不能理解我為何非要燒掉這些精美的作品。至于我這樣做是否正確,我不敢斷定。但我引用了這樣一句話說服她:“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之后,我們便沉重地將那些圖片一一投入火中。看它們在火中扭曲,萎縮,痛苦不堪。女友的眼淚來得真切,而我卻在陰冷的風中體會著它們給予的溫暖。
墓地后面有一塊巨大的巖石,我扶女友坐上去。山坡下有片桃樹林,桃花開得滿山坡,風穿過桃林挾著花香撲面而來。
“你父親會喜歡這里的。”女友說。
“應該會吧。”我抬手將她的幾縷在風中飄舞的碎發撩至耳后。
“我將來也要到這里來。”女友垂下眼簾低聲又說。
聽了這話,我似乎被電擊了一下,身心悲涼地懸在了半空。這就是她對我的愛情誓言,沒有做作,沒有華麗的詞句,有的只是那種發自內心的表白。
我一時無語,一把摟她在懷。假如她說這里就是天堂,我會永遠在這里陪她待下去。
“我更喜歡楊樹林,桃花太張揚,開起來近乎瘋狂。”我停頓了許久從巖石上跳下來說。
這一點我與父親不同。他有許多手捧“尼康”,肩扛“索尼”穿梭在桃花林中的照片,是當年幾個攝影界的好友和他一起外出采風時為他拍的。父親曾眉毛舒展瞇著眼睛對我講照片上的自己,他說這是一種戰斗的姿態,攝影就和在戰場上瞄準射擊一樣,也和你寫文章是一個道理。必須要確認自己同周圍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僅是感性,更重要的是尺度。一幅作品離自己的構思越近時,你感受到攝影機快門的后坐力會越強。
然而,不幸的是我很少有這種體驗,我現在把父親一生的體驗成果又還給了他。
“爸,我們走了,我們會再來看您的……”
我們留下一束潔白的郁金香,然后便轉身撲向了山坡下的桃樹林。可是我卻陷入了近乎絕望的情緒中,為什么我就找不出比父親作品中更為美妙的東西來傾訴清明的悲壯和抑郁?為什么就感覺不到那“桃花叢中琵琶聲”的美妙?
我穿過桃花林,又走進楊樹林,祈盼著耳畔嗚咽的風能給我療傷,給我說明這一切的困惑。
六年過去了,我仍未驅散掉那種無奈的苦悶,仍試圖用文字完整地傾吐我對父親和祖父,以及祖母的追思。可是,六年之久,一次次燈下執筆疾書,一次次在準備投遞的路上拆開,然后撕得粉碎撒向天空。讓那些情感和記憶的碎片飄在陰濕的路上,飛入那濃而稠的黑暗里,幻化成十九束潔白的郁金香,為父親祈禱,為父親悲歌。
可是,今又清明,我卻又似乎聽到來自天堂的父親對我的吟唱:人生就像攝影一樣,只要有一個留住美麗的堅定信念,鮮花就會永遠綻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