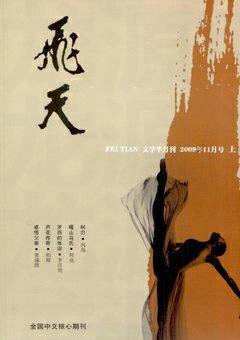理想與存在之辯
郝江波 趙 蕾
穆旦,作為“九葉詩人”的代表,是中國現代派詩歌的奠基者和大成者,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袁可嘉曾稱贊穆旦:“在抒情方式和語言藝術的現代化問題上,他比誰都做得徹底。”{1}唐祈稱穆旦為“四十年代最早有意識地傾向現代主義的詩人{2}。穆旦為詩,善將個體的心理體驗與現實結合,借助新奇的詩歌意象,抒寫出超越具體感遇的深層哲思,給讀者豐富廣闊的閱讀思考空間,“使讀者在伴隨而來的錯綜復雜里仍有一明確方向指導自己的反應;至于在此無形定義圈內的聯想發掘,讀者充分自由”。{3}長詩《神魔之爭》是穆旦最優秀也具代表性的詩作之一。首先它是穆旦詩作中最長的一首,容量大,系統地表現了詩人對一個問題的思考,且形式獨特,從整體結構到意象設置,都體現出詩人獨到的藝術品格,作品的鋒芒也因之更為明利。第二,穆旦1939年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學習,開始系統接觸英美現代主義詩歌和文論,并產生強烈興趣。《神魔之爭》作于1941年6月,最初連載于1941年8月2日至5日的《大公報·綜合》。當時正是穆旦詩歌創作向現代主義方向發展漸趨成熟時期,因而該詩鮮明地體現出穆旦乃至整個“九葉派”所倡導的“現代化”、“戲劇化”詩風。因此,解讀《神魔之爭》對了解、研究穆旦及九葉詩派詩藝有必要的價值。
同為九葉詩人的唐祈認為:“穆旦也許是中國能給萬物以生命的同化作用的抒情詩人之一,而且似乎是中國有肉感與思想的抒情詩人之一。”{4}《神魔之爭》很充分地印證了該評價。該長詩從體式上可看作一幕頗具象征意味的現代詩劇。東風、林妖、神、魔這些概念意象,被賦予生命成為詩劇的四個聲部角色。各聲部之間既有駁辯聯系又獨立成意,通過答問、辯駁完成詩人主體思辯。在這里,詩的感性意象表層與思想內核血肉融呈。那么詩的思想內核到底是什么呢?顯然,我們有必要先將詩劇四個聲部的象征含義作一定方向的解析。
唐祈在論及《神魔之爭》時說:“東風是齊生死的生命本身的象征,它把種子到處播散,又讓烈火燃燒,如此平衡著力量。它的分裂是神與魔的斗爭。”{5}這種認定是有道理的。從詩中我們看得出東風是宇宙、自然運動的結果和表現,是生命的征候。他以一種超然的姿態出現在詩劇中,帶給我們對生命伊始且至今延伸的整個生命過程的理性認知。他冷靜地注視、訴說人類浩劫的歷史:“在山谷,河流,綠色的平原,/那最后誕生的是人類的樂聲,/因我的吹動,每一年更動聽,/但我不過揚起古老的愚蠢:/正義,公理,和世代的紛爭——”同時冷靜得近乎殘酷地宣示著未來:“你所渴望的,/遠不能來臨。你只有死亡,/我的孩子,你只有死亡。”但若將東風象征義固化為生命本身,并將神魔斗爭看作是他分裂的結果,這就未免有不妥之處。在整個詩劇角色中,東風情感外露最少,既無激情,也無迷惑,始終平和冷靜,是整個詩劇的理性主控基調。應該說,東風的闡釋最為接近詩的主旨。他象征的應該是基于生命而高于生命的“秩序”,自然科學稱之為規律,自始至不見盡頭的終,他都是統一的。
神與魔的象征義,既易解又難解。易解之處在于,神、魔這組對立意象在文學作品中曾多次出現,如彌爾頓的《失樂園》、歌德的《浮士德》中,都曾出現上帝(神)與魔鬼(魔)的爭斗對立,這可作為鑒照參考而不至于偏離象征的本義方向。難解之處在于,對神魔的理解易失之淺浮,而將之與當時時局相扣連。將神定義為時存秩序的象征,而認為魔則代表了革命的反叛者。這樣的理解將詩歌的象征層簡單化,淡化了詩歌的豐富性。作品中,神與魔一出現,便各自發出自己的宣言,神說:“一切和諧的頂點,這里是我。”魔說:“而我,永遠的破壞者。”從這里入手思考,此處神、魔是一對相矛盾、相糾結的意象。神是至善至美的和諧理想的象征,而魔則代表著與理想對立的實有存在,他的特征是殘缺和丑惡,是不諧的律動。這二者對立時空應該是與東風的存在同步的,即步從歷史而指向未來。當然,時局秩序的斗爭自然也是融含其中的。林妖的迷惘與失望是個體生命存在體驗的焦灼,他的形象是個體思考的負載,與東風、神、魔形成互補而構成作品完整的意象象征框架,為主題思辯的展開奠定基礎。
作品或者說作者的思辯又是如何進行的呢?這最明顯也最主要地體現在神與魔的駁辯中。神在作品中作為自古而來的和諧完美的化身,宣稱自己如“愛的誓言。它不能破壞”,宣稱自己有“遠古的圣殿”,有“美德的天堂”和“不屈的恩賞”。而魔則針鋒相對,將神所擁有的聰明、高貴、正義、自由一一解構,而置換以對應的存在實有。他宣告自己沒有“美德的天堂”,有的是“寒冷的山地、荒漠”,指出神那些所謂快樂的子民,實如牛馬蟲豸,“被放逐在兇險的海上”,得到的只有恥辱、滅亡。在魔犀利而切中要害的詰辯下,神步步退卻,開始自省“我是誰?在時間的河流里,一盞起浮的、永遠的明燈”。開始自問“我錯了嗎”?最后陷于恐懼和失望的期望:“畏懼是不當的,我所恐怕的/已經來臨了……/站在旋風的頂尖,我等待/你涌來的血的河流——沉落,/當我收束起暴風雨的天空,/而陰暗的重云再露出彩虹。”在之后的部分中,神不再出現。魔則愈辯愈強,情緒也益愈暴烈。他呼喊“黑色的風”和“詛咒”,在絕望的孤獨中呼喊戰爭,驕傲地宣稱自己是“過去、現在、將來死不悔悟的天神的仇敵”。在魔悶雷樣的詩句中,我們知道他戰爭的目的不是要同情、撫慰和茫昧的笑,不是要“天庭的和諧”,他根本不相信和諧的存在,他抗爭的意義就在于抗爭本身。神魔駁辯的過程和結果,作了這樣的表達,“完美和諧”的歷史由來已久,但它只是人類夢寐追求而永遠無法達到的幻象,或者說根本就是謊言。苦難和苦難的抗爭乃是不變的存在。詩人在同年7月所作的《哀悼》中,有“人世的幸福在于欺瞞/達到了一個和諧的頂尖”的詩句,也是對“和諧”的解構。就這樣,作品中和諧的神“退隱”了,而殘缺、苦難、暴烈的魔越來越堅定,他才是實有。
神與魔的駁辯之外,是東風和林妖的述答。東風葆有自己一貫的冷靜,笑看紛爭,對林妖預言式地回答:“我的孩子,你只有死亡。”雖殘酷卻表達出作者所感知的“歷史的真實”,體現了詩人“辯證的自然主義的看法與超越的自覺精神”。⑤昭示的是詩人深刻哲思的一面。此處東風可看作是“作品的思想導言人”,他的闡述是對神魔辯爭的理性收束。林妖的問詢對話,述說對自身性質、命運的疑問和設想,表現的是個體人對存在和生命終極價值的思考,是神魔之辯在個體中的具體體現。而林妖的迷惘與失望,是詩人內心痛苦的外化。林妖的一段合唱出現兩次,并以之結尾,其間所透的迷失無奈之情,成為詩人印到作品中的情感基調。由四個聲部的辯爭、述答中,我們得到這樣的啟示:生命從開始便在苦難和殘缺的存在中存在,且一直在持續,不見變更。那一直以來追求的和諧完美乃是幻象,苦難和丑惡才是實有。個體唯能于迷惘和失望中做不止的抗爭。
穆旦的《神魔之爭》產生于抗日戰爭如火如荼的時代,與民族苦難的激發肯定有莫大關系。詩人個人的感遇、詩作問世之時的社會狀態,是詩人哲思的激發因素,只能作詩歌主題的切入點,而絕不是詩人詩作思考抒發的全部,還有更廣更深的思考融在作品中。我們說該詩不是成功的鼓動宣傳品,卻堪稱是超時空的思想藝術杰作,它以新奇的結構和意象組合表現詩人對歷史和未來的思考。它所揭示和預示的,也許正是人類永遠無法擺脫的存在真相。
參考文獻
{1}{3}袁可嘉.新詩現代化的再分析[A].論新詩現代化[C].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88.
{2}{4}{5}唐祈.搏求者穆旦[A].新意度集[C].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1990.
注:文中詩句均引自李方.穆旦詩全集[Z]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
責任編輯 曉 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