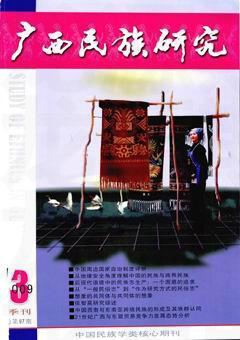李紹明先生的學術經歷和學術思想
李紹明先生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民族學家。1950年秋,他進入華西大學社會學系民族學專 業就讀,系統學習了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史前考古學與語言學等知識,并在1951年和 1952年夏季兩次到羌族和彝族地區進行調查研究。1952年秋,全國大學院系調整后,就讀于 四川大學歷史系,接受了蘇聯民族學、中外通史、民族史和民族志的教育,增加了史學修養 。1953年,又調入西南民族學院民族問題研究班學習,系統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的教 育,并進一步學習了民族理論與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獨特而豐富的教育背景,使他掌握了 民族學、民族史、民族語言、民族問題理論等多方面的知識,并成為在民族學、民族史、民 族問題和民族理論上均頗有建樹的學者。
從1954年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開展調查研究起,他把學術生涯中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了民 族學的田野調查。1956年到1963年,他先后在四川云南的彝族地區、四川的羌族和藏族地區 進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對民族學深深的熱愛,使他堅持著“咬定青山不放松,任爾 東西南北風”的信念,并在1977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得以恢復和發展時,回到自己熱愛的研 究領域,全面整理過去的成果,進行理論升華。改革開放以后,他組織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田 野調查工作,其中中國西南民族學會大規模的六江流域調查、酉水流域土家族的調查、西南 絲綢之路調查、金沙江流域考古文化調查等,均在學術上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多年的田野調查,誕生了一大批優秀的學術成果。他對涼山彝族奴隸制度的研究,為豐富中 國民族學的學科理論,為涼山社會改革的實踐做出了應有貢獻。由其總纂的《涼山彝族奴隸 社會》一書被譽為“科學大廈的奠基石”。他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觀點對藏族社會進行 研究并提出康區的特殊性以及“穩藏必先安康”的重新認識,受到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肯定 。他主持羌族社會歷史調查后的研究成果及合著的《羌族史》,為羌族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他主編的《川東酉水土家》一書,填補了四川土家族研究的空白。他還在民族識別、民族 文化、民族法學、客家研究諸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近年來,他又成為藏彝走廊區域綜合研 究的帶頭人。
20世紀90年代以后,李紹明先生將精力投入到中國民族學的學科體系建設工作,秉承其在《 民族學》一書中提出的思想,全力推進民族學與人類學的中國化。對國內高等院校人類學民 族學課程的設置、研究力量配置及研究重點的確定、對人類學華西學派學術思想的總結,均 體現了這一追求。他一直主張民族學研究既需要有大的理論作指導,又要做扎實的田野,要 在繼承前人求實學風的基礎上,結合實際開展研究。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作為民族學家,李紹明先生四處奔走,呼吁社會各界共同保 護羌族文化,合理開展文化重建。他負責的專家小組起草完成了《羌族文化生態 保護實驗區規劃綱要》、《四川省地震災后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保護與恢復重建規劃綱要》 ,得到國務院批準,成為指導災區災后文化重建的原則。
李紹明先生是四川社會科學界的帶頭人,長期擔任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民族學科規劃組成員及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評委、四川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職務,締造了四川省民族學、歷史學 、民俗學、文物和博物館學界團結一心的局面。他是我國民族學界的智者,在全國性學術團 體中國民族學學會、中國民族史學會、中國史學會、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擔任了許多學術 職務,在民族學研究的組織和學術活動工作上傾注了大量心血。馬曜先生曾經在為《李紹明 民族學文選》所作的序言中稱他為學術活動家,并說他“約己以讓,故能得眾多助”。李紹 明先生留給我們的諸多人文遺產,值得我們好好珍惜。
(本文由四川省民族研究所供稿)
〔責任編輯:陳家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