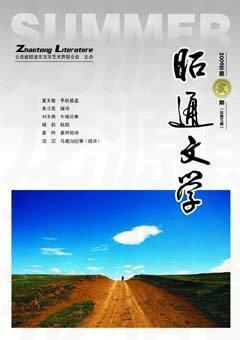一棵樹的命運
李 林
風,呼呼地刮著。雨,颯颯的下著。
小樹在風中搖曳,在雨中渴求。
站到窗前,一陣冷風吹散了我本已有些零亂的頭發,趕緊吸口冷氣,關緊窗戶。耳邊突然響起了“啪啪”的雨打窗玻璃的聲音。透過灰蒙蒙的天幕,遠處一棵小樹在風中瑟縮著,顫抖著。
土地很瘦,瘦得極像一副人的骨架,沒有肉體和血液。四周是空蕩蕩的,沒有一棵與它做伴。盡管瘦,小樹的根還是深深扎入“骨骼”里吸取那一點兒養分;即便空,也并不寂寞,靠著那長綠的枝葉,向人展示一個生命的存在。
小樹是棕樹,是四年前干才栽下的。干才是人名,學名叫崔文才。也許是父母都是地道的農民,希望他以后學文化,長知識,才給他取了個文學色彩濃厚的名字。山里人喜歡在人的名字前加上“干”或“亥”。男的像“干才兒”“干龍兒”“干斌斌”。女的如“干花兒”“干芳兒”。有的還在中間加一個“老”字“干老三”,“亥老四”。一表示親切,二則是鄉村的習俗。“干”或“亥”沒有小的意思。這里的人大多都比較高大、魁梧。而干才卻是名副其實的瘦小孱弱。初見干才時,最明顯的便是那件藍“滌卡”四個包外衣,肩上已補了兩塊顏色不一致的疤,兩只袖口已經脫線,有幾縷絲線飄著,衣角邊垂到膝蓋上不遠處。不用說這件衣服和他的個子極不相稱,是熱心人送的。短而茸的頭發像一層枯黃的苔蘚蓋住腦袋,一雙“脫臼”的膠丁鞋發出“啪啪”的響聲。每次聽到這種聲音我們就可以大概斷定是干才從門口經過。干才家在學校租給我們的民房斜后面,大多時候他都從這里經過。剛開始時,干才只是快速的朝我們的住處看幾眼便小跑開了,漸漸地紅著臉和我們打招呼,并講述一些打柴、掏鳥雀、放豬的趣聞。除去飄雨的日子,干才放學后的大多時間都是打柴、放豬。每天傍晚,一個十歲的小男孩,背上壓著沉甸甸的柴,一頭干瘦的母豬和兩個豬仔在前面帶路,男孩嘴里不時發出“嗷”、“嗷”的吆喝聲,伴著晚霞和清風,干才一天的生活畫卷就這樣合上了。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干才平常而單調的生活因父母的離去而變得蒼白,恍然。在那間低矮潮濕,墻的四周開著裂縫的土房子里,干才的哭喊聲引來了村里的人,村民們聚到家里,借助從瓦縫和門里透進的光隱約地看清一個陳舊的秦柜,傍邊歪放著幾口土吊鍋、土壇子。稀疏的樓板上隱約擺放著兩張床,干才的父親靜靜的躺在那兒,無聲無息中走完他的最后一步。人們看著走路三步一喘,兩步一停,脖子粗得像桶的干才的母親和干才,決定有錢出錢,沒錢出力,就這樣把一個土生土長,平時腰間系根草繩的人送入了黃土。剩下的日子,命運依然嘲弄著這個十歲的孩子。和他相依為命的母親在父親走后的一個月撇下他獨自走了。出喪那天,村里的男女老少擠滿了窄窄的山路,肅穆的空氣似乎凝固了。只有干才撕心裂肺的哭聲在山谷中回旋。緩慢的前進中老人們走兩步又用袖口抹下模糊的雙眼,小孩子們不再嬉戲打鬧,他們看到的是一張張嚴肅而冷靜的臉。
時間一分分過去了,在村子邊平緩的臺地里,多出了兩個土堆。土堆后是一棵干才從自家后園移栽的棕樹。復山那天,干才默默地種下了一個心愿陪伴父母,自己守著那個縹緲搖曳的家。四年的風霜雨雪,洪澇或干旱,小樹的根扎得更深,干長得更壯。初春的小雨洗禮后,陽光沐浴下的小樹顯得碧綠綠、亮澄澄的。碩大的幾張葉片緊緊護住還不夠堅強的軀干。栽時還不足一尺的小苗,現在有一米多高,它似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在含情脈脈的遙望遠方,又似一個英姿颯爽的鋼鐵戰士在守衛這塊神圣的土地,它不是與百花爭艷,與小草襯綠,同群峰爭雄。它是代替一顆心愿守護著地下的兩個靈魂,那是干才的父母。小樹四季隨風哀鳴,隨雨啜泣,隨霜雪而戴孝。它經歷著自然環境的考驗,目視著人生的悲歡。
一棵樹的生命,不擇地勢和環境,苦苦的掙扎,默默地生活著,折射出它主人的生活歷程。
【責任編輯 楊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