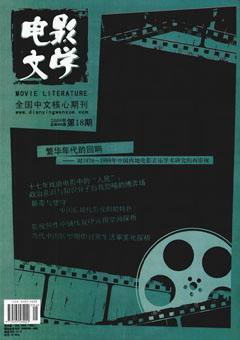“整體復調”:對《蘇州河》敘事的另一種分析
邱代東
摘要作為20世紀90年代末一個實驗性的敘事文本,第六代導演婁燁的《蘇州河》在敘事上的發展不僅是結構性的借鑒與革新,更是一次創作觀念變遷的實踐行為。它用敘事方式本身所具有的張力將故事控制在了一個昆德拉所描述的“整體復調”世界里。敘述視角的平等轉換、情感的節奏控制與共時性時空等都是《蘇州河》“整體復調”的特征。
關鍵詞“整體復調”;元敘事;時空
圍繞第六代導演婁燁的代表作《蘇州河》,在已發表的評論文章中受到的關注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把目光集中在該片與希區柯克的《暈眩》之間互文本性的主從關系上”;一類則是剖析其獨特的敘事藝術。該影片迷宮式的敘事空間是研究者們把握導演婁燁如何進行敘事實驗的契機。由巴赫金的小說理論可以知道,小說在發展的過程中存在兩種敘事風格:單語小說和雜語小說,單語小說向雜語小說過渡的條件是“語言語義中意識形態的解體”。“90年代的中國文壇,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如巴赫金所描繪的,由于‘意識形態中心的解體,一個多種異質話語并存,互相爭鳴,沒有固定的中心與邊緣、主調與副調之分,也缺乏普遍有效的共同游戲規則的話語格局慢慢形成了。”這樣的話語格局為第六代導演創作提供了“雜語”背景,使他們的電影出現多元共生的復調特征。
“復調”來源于音樂術語,指兩個或多個單獨的聲部旋律同時展開,雖然整個樂章結合嚴密,卻仍保留各聲部的獨立性。巴赫金借這一術語評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創作特征。他認為“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復調,這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特點。”“巴赫金著重強調的是主人公自我意識的獨立性、對話性、主人公與主人公、主人公與作者之間的平等。”熱奈特在細讀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的基礎上發展了巴赫金的“復調”,將“復調”理論由“內在的理論基調”發展至敘事技巧的范圍。他將敘事視點的轉移所造成敘事體式的變異稱為復調。米蘭·昆德拉領悟到前兩者對于小說結構的重視,在他們的基礎上探索并實踐了自己的“復調”理論。昆德拉充分調動創作中的“復調性思維”用于建構敘事上的“整體復調”。“進行全面形式實驗”的《蘇州河》在世紀末年的出現為“整體復調”在電影領域開辟了新的實踐空間。它打破了以往中心敘事的特征,呈現視角、情感空間多元共存而又平等共生。同時,《蘇州河》時間和空間上前后交錯的特殊結構則為整部電影營構了一個情感和意義沒有先后、主從之分的復調空間。
一、視角的轉換與控制
電影時間長度一半的時候,敘事視角的轉換將整部電影一分為二,成為由“我”構造馬達的愛情故事與馬達完成自己故事的臨界點。前半部分由“我”塑造了馬達與牡丹的愛情故事。“我”用“應該是”等編造的、不肯定的語言將馬達和牡丹拉入了鏡頭成為故事的中心。在牡丹跳下蘇州河之后,“我”作為講述者已經進行不下去這個故事,而是由馬達自己完成自己的故事。在此,馬達作為被講述的對象,跳出了“我”的控制,成為另一個與“我”生活在蘇州河周圍的人。盡管“我”已把故事發展的權力移交給馬達,但馬達沒有成為另一個“我”——控制故事的人,而是發生故事的人。他從這一刻起與美美具有平等的發言權,成為一個自由生活但仍舊被“我”或鏡頭敘述的人。
有趣的是,“我”由全知的視角轉移到第三人稱敘事,這個敘事權力移交的過程中發生了連“我”都震驚的“事實”——牡丹的出現。她與馬達因醉酒而遇車禍死亡。女孩牡丹的出現成為電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實——存在與美美一模一樣的女孩。這由美美與牡丹的尸體出現在同一畫面獲得證實。在“我”為與美美極其相似的牡丹表示出驚訝時,《蘇州河》的故事結構暴露出其最外面的一層:全知的導演虛構的“我”和“我”與美美的愛情故事。回到電影的開頭,美美問“我”對愛情的看法的時候,面對“我”勉強的肯定,她干凈而利索的否定表明了她不相信馬達所描述的真愛。這個時候,以“我”的視角開始了第二個套層的構造者講述馬達與牡丹的愛情故事的過程。這個簡單的套層結構本可以持續到電影的結束。然而,當牡丹與美美“相遇”,“我”的講述便跳出了我所能控制的層面,直接連接上導演的敘述。可見,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套層結構,而是—個里外相接、不規則的套層。
由此可以看到的是,導演在影片中變換的視角不僅順利滿足了敘事結構特殊的需要,而且從不同的角度完成了主題的建構,將虛構的本質通過不同的視角而構成的敘事結構呈現出來。在整個過程中,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講述人的出現最終所依附的仍舊是導演本身。用昆德拉的話說,就是作者的統一意識賦予了他們的獨立,形成一種視角轉換的“復調”。
二、情感空間的分布與節奏
導演對情節的特殊安排使電影充滿了情感的節奏感。整部電影存在兩個情感波峰:一個是牡丹被綁架后跳下蘇州河,出現時間為電影長度的一半;一個則是“我”與美美分手、馬達找到牡丹,出現的時間為電影長度的四分之三。第一個情感波峰出現的時候,在“我”的視角下,馬達背叛了他的愛情,參與綁架牡丹勒索錢財的勾當。而牡丹則在發現自己被愛人背叛的時候,跳下了蘇州河。在綁架發生之前,馬達與牡丹之間情感的交流少得可憐,用“我”的話說就是“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在一起,然后呢?自然就是愛情。”在這一個情感波峰下,他們有了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對話,盡管是站在蘇州河橋上的護欄兩側扮演著威脅與被威脅的角色。在第二次情感波峰來臨時,情感交集的人物擴大至4個,增加了“我”與美美。因為馬達的出現,
“我”與美美終于站在一個平臺上交換對愛情的看法。“我”第一次說出了自己的真實看法:“我們是先做愛再分手,還是分手后再做愛?”這一問題觸動了美美長久以來對愛情不信任的焦慮。她憤怒的離開便是對“我”的回答。隨后,如寫意一般,與故事線索完全沒有關系的“插曲式段落”使電影暫時處于一種舒緩的情調中。音樂電視的拍攝與歡樂舒適的陌生人聚會,在“我”的攝像機下成為營造氛圍的工具。而就在第二個情感波峰結束后人物之間的被懸置的關系獲得了極端的解決:馬達與牡丹遇車禍雙亡。隨后,電影開端時呈現的紀錄片般的平靜再一次出現。插曲式段落的柔和氣氛(柔板)與突然的車禍死亡(急板)暗示著情緒的突轉。它們的對比將所有的情感力量集中在了一起。這與昆德拉描述《生活在別處》的情感“復調”特征相同。
對于“我”這個特殊的角色,隨著整部電影歷經了三次情感表述與態度的轉變。從電影一開始的記錄畫面出現,“我”僅僅作為客觀的表述者,面對美美的愛情只有不假思索地被動配合。當“我”成為馬達與牡丹故事的創造者時,“我”以全知全能的作者身份出現。“我”塑造了馬達和牡丹,賦予了他們生活與情感,并以似是而非、毫無肯定、相對隨意的敘述參與其中。在牡丹跳河后,馬達跳出“我”虛構的故事,存在“我”與美美的同一時空
中。“我”的參與便進一步轉變為情感層面上的。牡丹與美美出現在同一個畫面時,“我”因虛構與真實的相遇而震驚、困惑。作為一個虛構與被虛構的對象,隨著自己情感表述與態度的變化,“我”的認知呈現出一個由客觀、局外然后困惑,懷疑的過程,也正是隨著轉變的過程,電影的主題——虛構得到了敘事上的支撐,步入“復調”結構的核心。
三、時空的交叉與并置
在《蘇州河》敘事結構里,時空的設置呈現出交錯的狀態。而交錯的結點出現在牡丹跳河后,“我”不能繼續馬達的故事而讓馬達完成自己故事時。結點之前,“我”虛構的馬達與牡丹之間的故事開始于“我”的敘述,在時間上處于“我”與美美的“愛情”開始之后。結點之后,馬達跳出了“我”的虛構敘述,成為與“我”同時存在于同一時空的人。也就是說,馬達存在的時間與“我”所存在的時間在同一空間獲得吻合。開始的時間不同,卻獲得相遇而行,這使電影的時空結構出現了交叉。值得注意的是,當故事虛構變成現實并與“我”存在同一被敘述的層面上時,影像前后并沒有提示性的變化,影像層面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真實可信。不難聯想到的是,整部電影中,出現的那一系列暗示馬達與牡丹故事真實可信的信息:“我”在報紙(生活中事實的載體)上看到的女孩跳河的新聞、打撈上來的尸體等。這些信息作為看似可靠的內容為馬達與“我”出現在同一時空做了強有力的鋪墊,從時空的角度對抗了“我”所虛構的故事。
不妨做個假設,馬達與牡丹的故事是真實存在的。那么整部電影故事的時空結構就顯得清晰明了。馬達與牡丹、“我”與美美的故事發生在同一時空里。“我”在獲知了馬達后,為馬達虛構了一個他出現在美美之前的背景故事。當馬達出現在美美之后,馬達繼續自己的生活。這樣的分析之所以叫做假設,是因為導演沒有給出任何可以證實并肯定的信息,反而故意讓前后的事實產生令人困惑的巧合,如“我”隨意虛構的馬達情況與真實的馬達一模一樣。電影中的“我”在圖像與聲音所敘述的內容吻合的時候,居然告訴觀眾相互抵觸的兩句話:“別信我!”與“我的攝像機不會撒謊。”在導演有意將真實與虛構混淆的前提下,惟一可以獲得證實的便是虛構本身。在虛構下,時間上的錯位與交叉所達到的效果正是在讓觀者在不得不淘汰基于時間順序而排列的先后標準,采用平等的目光加以審視。由此,電影的敘事突破歷時性,完成了共時性空間的構建,使人物、觀念與事件的展示獲得了一個并置在同一水平線上的機會。
蘊涵著一個復雜的敘事結構,《蘇州河》的誕生似乎是20世紀前后文本實驗的一個綜合性樣本。《蘇州河》在敘事上的實驗有的是導演有意為之,有的卻是導演并沒有察覺的隱形創造。是世紀末文化語境的變遷為《蘇州河》提供了成長背景的同時也提供了可闡釋的注腳。它“整體復調”敘事的結構不單純是一個敘事結構實驗,而是價值觀念的變遷反饋在了內容與結構上引起的異變。架構在虛構的基礎上,以往的價值判斷在《蘇州河》里變得蒼白無力,作者與人物出現同樣的迷惘。而這種迷惘卻在觀影的過程中促使觀眾進行了反思。從某種意義上講,昆德拉“整體復調”所推崇的不僅是平等的創作理念,更多的是構建一個比獨語更接近真實的雜語空間。事實上,這也正是大多數第六代導演所認同的。婁燁用《蘇州河》完成了他對雜語空間的創造。《蘇州河》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解剖的敘事范本的同時也從側面揭開了第六代導演與往代導演不同的創作意識與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