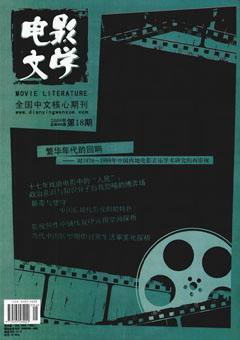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諷刺藝術風格
王海濤 劉曉輝
摘要電影《肖申克的救贖》通過多層面的諷刺策略,在對立的結構中對真相、崇高、救贖和自由等宏大敘事話語進行解構批判,而溫情主義的結局又消解了藝術批判的深度,好萊塢的大眾文化消費模式最終構成了藝術對現代社會與藝術自身的雙重消解。
關鍵詞電影藝術;諷刺敘事;現代性解構
由弗蘭克·達拉邦特導演的電影《肖申克的救贖》改編自史蒂芬·金的小說《麗塔·海華絲與肖申克的救贖》,講述20世紀40~60年代末,在一座名叫肖申克監獄里發生的故事,圍繞新囚犯安迪、老囚犯雷德、由獄長諾頓等人,呈現了一幅美國監獄的多維圖景。《肖申克的救贖》發行不久即獲奧斯卡獎7項提名,被稱為電影史上最完美的影片、好萊塢最有氣勢的十大巨片之一,1995年該版獲得全美影帶租售冠軍。除卻商業成功以外,影片也給人們帶來了諸多的人生思考,從藝術表現方式來說,我們必須承認“諷刺”的多層面運用是該影片獲得成功的重要手段。
一般諷刺在敘事作品中以3種方式出現:作品的語言中、作品的事件中、或者作者的觀點中。再進一步可以把諷刺分成四類:(1)語言諷刺。即說反話;(2)情境諷刺或命運諷刺,這有兩種情況,其一是在表象與事實之間制造的反差:其二是敘事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希望某件事會發生,結果相反的事卻發生了;(3)戲劇性諷刺,即故事與讀者期待視野之間形成反差;(4)語調諷刺,即敘述者以一種語調方式暗示所指與能指的分裂。
一、影片中運用的語言諷刺
如典獄長諾頓引用圣經語言教導囚犯:“我是世界之光,跟隨我的人不會行于黑暗,還會擁有生命之光。”而實際上,在他管理之下的肖申克監獄罪惡累累,他加給獄犯的只有更深的黑暗。在實行獄外計劃時,諾頓口口聲聲自稱這是“一個真正的、有進步意義的服刑和改造。我們的服刑人員,被正確的監管的服刑者,將走出高墻,為各種公共服務進行勞動。”他的話中反復強調“真正、進步、有意義、確實”等崇高的概念,而其真實的動機只是滿足個人的貪婪。而承包商為了保護自己的生意不被諾頓搶走,采取了賄賂的方式取悅諾頓:“嘗一下我太太特意為你烤制的餡餅吧,然后再考慮一下。”這里,表面上是溫情的友誼,而實際上“餡餅”之下掩蓋著骯臟的交易內幕。這樣各自冠冕堂皇的能指語言與追求私利的所指之間形成了鮮明對照。語言諷刺的刀刃凸顯出其內在的鋒利。此外,像影片中喜歡雞奸男犯的三惡徒命名為“三姐妹”,專橫跋扈的守衛隊長哈雷被捕時,敘述者黑人瑞德形容其“哭的像個小姑娘”,老布魯克斯上吊自殺前在旅館屋梁上刻下“布魯克斯·哈特蘭到此一游”等等,都具有非常明顯的“言此意彼”的諷刺意味。
二、影片中情境諷刺或命運諷刺運用
影片開頭是莊嚴的法庭庭辯,一邊是主人公安迪對謀殺妻子和其情人罪行的蒼白無力的辯解,一邊是起訴律師滔滔不絕、言之鑿鑿、氣勢逼人的有罪推理,從表象上看,一系列證據鏈均指向了安迪,而事實上雄辯的律師和莊嚴的法庭共同將無辜者的命運推入有罪的深淵。
除了主人公安迪外,影片中其他人物也不同程度地表現出命運的諷刺:瑞德在獄中努力改過,希望能獲得假釋重回社會,然而自由的希望接連破滅,當他被“體制化”而變得只適應獄中生活時,卻意外獲得了假釋的自由;老布魯克斯在拘禁生命的獄中呆了一輩子,當他刑滿出獄重獲自由時,卻無法面對與從前迥然不同的世界,他甚至想到以再次犯罪的方式入獄,但終因“太老了”而只能以自殺了結殘生;典獄長諾頓處心積慮,一邊以獄犯的救贖者自居,一邊壓榨獄犯做著大肆斂財的勾當,然而到頭來“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三、影片中的戲劇性諷刺
影片中有兩個戲劇性諷刺的例子,其一是安迪在戶外工作時,偶然聽到監獄守衛長哈雷談及遺產繼承的收稅問題,就大膽地去為哈雷獻計避稅,安迪此舉在瑞德等人看來是極度危險的“自殺”之舉,然而最終安迪卻戲劇性地為每個同伴贏得了3瓶啤酒,讓他們飽享“自由”的愉悅。其二是青年湯米是主人公安迪幫助的對象,安迪幫助他取得了中學文憑,使他的人生充滿了希望,然而由于他對安迪案件的線索了解,最終卻因安迪要求重新調查自己案件而遭典獄長陰謀殺害。前一個戲劇性諷刺令人會心一笑,后一個戲劇性諷刺則令人唏噓不已。影片就整體敘事結構來說,就是巨大的戲劇性諷刺,以救贖者自居的諾頓等人終遭覆滅,而安迪、瑞德則在自己的努力下終獲自由,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柔弱勝剛強”的戲劇性諷刺,這種諷刺在觀眾那里得到深刻的兩相對照,從而超越了故事角色的視角限度,使影片意味深長。
四、影片中巧妙的語調諷刺
《肖申克的救贖》的主敘述人是瑞德,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肖申克這個特殊監獄環境中的黑人,一方面他缺乏系統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又深諳監獄的環境,對人性的特點、監獄的潛規則都有相當的了解。在假釋無望的心境下,身上形成了一種對抗主流價值觀念的玩世心態,這些通過其語調明顯地反映出來。當安迪問瑞德進監獄的原因:“也是無辜的嗎?”瑞德輕描淡寫地回答“肖申克監獄惟一有罪的人。”從表面上看瑞德坦承自己真的殺過人,但其語調平淡,更透出一種對負罪感的麻木,因為經過多年煉獄般的生活,他對有罪無罪這樣的問題已經不再關心,他已經不會輕易相信任何人。再者,監獄生活經驗使他明白,有罪或無罪在肖申克這個地方根本沒有任何區別,在最后一次假釋答辯時,瑞德聽之任之的諷刺語調反映出瑞德對監獄教化制度的不滿,同時也暗含對自己命運的徹骨悲傷。這種語調諷刺既使作品具有一定的喜劇性和黑色幽默感,又加深了反思的深度。
五、觀后的感悟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故事時間跨度為20世紀40~60年代,這是現代性價值觀念一方面在社會現實中得到進一步強化,另一方面在文化哲學領域引起懷疑的時代。反思現代性的理性觀念,尋求感性的解放是先鋒藝術家和哲學家思考的命題。而《肖申克的救贖》很好地切入了這一時代主題,通過諷刺這一具有解構力量的武器,對現代性的宏大話語,諸如真相、崇高和救贖、自由等進行了解構和反思。
真相即事實,其客觀性得源于事實,是人們認識真相的基礎。而在影片《肖申克的救贖》中,我們發現人們認識的事實往往來源于虛構,巧舌如簧的律師循循善誘,足以使安迪獲不白之罪;湯米獲得的兇案真相在諾頓踏滅煙頭的剎那間,即永墮黑暗;而子虛烏有的斯蒂文先生也在安迪的精心營構下,走向陽光燦爛的海灘。影片給我們的思考是,當認識真相的“皮之不存”時,現代性主張的真理又“毛之焉附”?顯然影片的諷刺性追問直指現代性的價值中心,對其構成了巨大的解構。
崇高是現代性的價值追求,在西方宗教文化之下。人生就是通過追求崇高而獲得生命意義的救贖。然而,《肖申克的救贖》中的崇高和救贖往往與卑鄙和陷害共生,或者成為壓抑個體的新的異化力量。現代社會體制按現代性
原則建立起的規范本身也具有一種崇高品質,但它對原則、規則、程序的臣服遠超過對生命本身的敬重。如銀行經理審核化名斯蒂文的安迪時,他所相信的只是“他具備所有的證明,駕照、出生證、社會保險卡、簽名也十分符合。”安迪的命運在此又一次被逆轉(第一次他沒有殺人而被定罪,而這次他不具身份卻被賦權)。新的監獄長考察瑞德的假釋時,第一句話就是“檔案上看你已服了30年的終生監禁”,這里“檔案”不僅代表了事實,更具有現代性社會規范意義。個體生命在這種規范壓抑下,其生存尤顯卑微而渺小。
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的深層結構是由相互對立的一組關系構成深刻的諷刺,從這些對立關系的轉化(崇高轉化為卑鄙,救贖轉化為陷害,自由轉化為滅亡等)使人們思考現代性價值觀念的虛無之感。肖申克監獄一方面作為社會的懲教機構擔負著救贖犯人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在體制框架下不斷使獄犯獲罪。安迪本為無辜之人,但為諾頓洗錢的行為構成犯罪,其自我救贖的行為是通過自我獲罪的方式而取得,這一方式證明了現代社會法則的虛無和蒼白。我們還可以發現作為英雄形象的安迪,其行為動機來源于體制化的世界力量介入,他的無辜獲罪以及他的戴罪(偽造身份)新生都源自現代社會的發展帶來的各種負面影射。
然而,影片并沒有將這一指向現代社會弊端的深層反思貫穿始終。一方面導演為主人公建構充滿神圣、崇高、偉大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又用逃避、金錢對這種神圣、崇高、偉大進行了無情的解構。這種充滿悖論式的結構方式使《肖申克的救贖》的主題呈現出復雜和含混的特征,也使整個影片呈現出深層諷刺的張力。安迪憑借其豐富的知識、高超的智力、過人的勇氣和鍥而不舍精神,不斷地尋求個體生命的救贖,最終他逃離監獄,逃離了美國,在大海邊與瑞德共享余生。但這種結局并不能給深度思考的觀眾帶來現實的解脫,因為安迪們最終還是要回歸這個體制化的社會。安迪自我救贖的行為只是印證好萊塢一直宣揚的個體英雄神話,只停留在個體意義上。而非整體性意義的救贖。安迪的逃脫至多是個人暫時的勝利,而非人類精神和理想上的救贖。這種世外桃源的救贖行為實際上具有一種更大的消解性,即電影作為藝術,提供給當代人們一種溫情脈脈的想象,讓觀眾在理解前述諷刺的現實指向的同時,又墮入溫情的夢幻之鄉。這是好萊塢大眾文化產業在消費主義時代的必然選擇,這種自我消耗恰如卡林內斯庫所說,后現代主義藝術的典型特征是一種深刻的“反精英主義,反權威主義、自我的擴散、參與。藝術成為公有的,可選擇的、免費的或無政府的。諷刺成為激進的、自我消耗的游戲。”
從更廣闊的意義上說,《肖申克的救贖》并沒有對業已形成規范的現代性宏大主題進行深度剖析與透視,反而以英雄主義、略帶黑色幽默地固化了現代美國的中心文化的價值觀念,電影藝術的先鋒性最終通過藝術的大眾化歸位而消解,從而在文化立場上對藝術自身的先鋒性原則進行了一次自指諷刺。
簡而言之,諷刺的本質就是在生存虛無的前提下,用永恒的追問來反抗生存的“虛無”。諷刺就意味著生命感受與生命承擔過程之間存在著尖銳對立。一方面深知生命本身的無意義,另一方面卻不斷地追問生命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使生命獲得意義,以此來反抗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