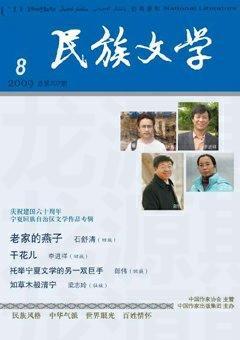我的城
張毅靜
我九歲,家里有了雪白的浴缸和抽水馬桶。那是我爸節(jié)衣縮食攢下錢,自己動手組裝的;工費不計,他自己既是設計師又是泥瓦工。從此我們家人可以不再去那怵人的公共澡堂子和廁所了。
這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讓我從那個時候起就和我的城隔開了。
那時的銀川,陳舊、迂緩,正如人們調(diào)侃的那樣:一條大街兩座樓,一個警察看兩頭。孩子們在土平房之間狹窄的泥土地上奔跑,女孩跳皮筋男孩打彈珠。父母不讓我去參與,他們喜歡讓我看書畫畫聽唱片。他們說:女孩子家,除了好好學習不需要去做其他……
然而這座城并沒有因為我的不玩而感到落寞。
人類城市從出現(xiàn)伊始,就帶著容納、自由的特質(zhì)。所謂“大隱隱于朝,小隱隱于市”。在鄉(xiāng)民社會里,來上一個生人,或是多買了半斤肉都可能成為村人的談資。人們久居在某處,彼此相知。分享同一種價值,遵守同一份道德默契,一切都簡單,穩(wěn)定。而城市,因為流動的人、不確定的目標、迅速變化的身份,使它有理由讓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寫下這樣著名的句子:“我是我,我從自身出發(fā),借由選擇與行動,我塑造自己。”
我像一塊面團,順著父母的意愿塑造著自己。我的城順著時代的感覺也在塑造著自己。
時光進入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整個社會忽然出現(xiàn)一種亢奮的情緒:“下海”、“廣州”、“鄧麗君”、“杰克遜”……跟隨著電視機潮水一樣進入到這座原本沉靜閉塞的城。
作為一個孩子,我驚奇地張大了眼睛。雖然放眼看去,很少有美麗的東西:破損的路面,陳舊的校園,違章的建筑,防盜的鐵窗,八股的教育,貧乏的娛樂。但我從大人的表情中知道,這只是黎明前的過渡期。我只要安靜地念好自己的書,銀川會長出和維也納森林一樣翠綠的樹木,會有一流的美術館、音樂廳,圖書館,全都不要票;銀川還會有咖啡屋,有旋轉(zhuǎn)餐廳、高爾夫球場……而我自己也會有一柜子美麗的衣服,到這些地方去可以打扮得齊齊楚楚……
可是,難道我除了埋頭在課本之上,其他什么都不用去做,這一切就會實現(xiàn)?
“是的!因為你現(xiàn)在的身份是學生。學生只要把書念好,就是對社會、對父母、對家庭最好的貢獻!”父母師長如此斬釘截鐵的回答,讓我沒趣地聳聳肩……從上小學起,老師就說我們是祖國的花朵是未來是主人翁,卻原來連我的城都不需要我親手添塊磚加塊瓦似的。
沒用我出一點力,銀川的高樓一座座聳立,道路延展,從小城鎮(zhèn)的風貌逐漸轉(zhuǎn)向現(xiàn)代格局。廣場有了,和巴黎廣場上一樣的鴿子也有了;時裝店、開放式公園、夜總會、花草樹木下的擁抱接吻都有了……在我整個成長期,我的城搭上了改革開放的快車,一路開往現(xiàn)代化的康莊大道。我是一位全程緊盯窗外飛馳畫面的旅客,當車子飛一樣疾馳,沿途的每道光影、每種氣味、每處景色都隨著迎面而來的勁風吹入我皮膚的每個細胞,脹滿它們、撐破它們……
我終于長大成人,離開象牙塔進入社會,父母對我的影響逐漸弱化,我開始在我的城里真正地生活。
我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學生,我擁有多重身份。正如諾貝爾獎得主阿瑪?shù)賮?森所說:“一個人可以同時是意大利人,女人,女性主義者,素食者,小說家,經(jīng)濟保守主義者,爵士樂迷和倫敦居民。”身份如陽光下的三棱鏡,隨著鏡面的轉(zhuǎn)動,我開始發(fā)出屬于自己的光。
我有一座容許、鼓勵女性發(fā)光的城。
它是回族自治區(qū)首府,可是伊斯蘭宗教色彩并不濃郁。歷史上數(shù)次形成的移民潮,使它海納百川。這個城市美女如云,“五步之內(nèi),必有悅我目者;十步以外,必有悅我心者。”銀川人普遍注重穿衣打扮,盡管喜歡逐著時尚“跟風”,但就連中老年婦女也個個收拾得有模有樣。可以隨心所欲地穿,可以美不勝收地展露,這本身已經(jīng)就是人類爭取了幾千年后才取得的進步。地球上不是直到此刻依舊有些婦女連面紗都不許隨意摘下嗎?——巴黎的優(yōu)雅氣質(zhì)很大一部分是由女人裝扮而成,我的城也因為美麗的女人而千嬌百媚。
和北京上海之類的國際大都市相比,我的城更適合人居住,或者說是更適合女人居住的城市。
沒錯,如果你從銀川往外走,驅(qū)車一個小時就會看到廣闊的、非常貧窮的農(nóng)村。面對干涸、窮困、失學等等苦難,我對我的國家城鄉(xiāng)之間的現(xiàn)狀有著深刻而鮮明的體驗。
但是如果我們不把諸如拯救苦難之類的任務扛在自己的肩上—— 一個社會如果把這些使命讓女人過度承擔,那基本就可以叫做不人道。所以我,一名城市女子就常常沒心沒肺地不去關注我生活之外的哀愁。
從小老師告訴我: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既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懊喪……但事實上,這不是一個女人應該過的一生,女人的一生不應該這樣度過,她應該有適度的悔恨,適度的懊喪,適度的碌碌無為以及適度的虛度年華。否則,她才是真正虛度了一生。
當我坐在銀川的書城,閑閑地翻看《納蘭詞》時,我毫不臉紅地承認自己既不聰明也不能干,但這并不妨礙我向往自由而優(yōu)雅的生活。
何況我的城里有太多像我一樣的女子。
我的城周圍碧水環(huán)繞,空氣清新。它安寧、整潔、便利,地方雖小卻五臟俱全。北京時髦保齡球,銀川就會建個“天威保齡球館”;上海有了滑雪場,銀川馬上跟著來;廣東人要吃鮑翅海鮮,銀川就會有“雪花大酒店”……任何一個場所里都有女人。跳舍賓練芭蕾學英語做SPA當驢友爬雪山……沒有什么事是銀川女人不參與的。銀川女人生就一種落落大方的氣質(zhì),身體健康,興致勃勃,非常自信也非常自得。可能外邊的人會覺得銀川老土,可銀川人,尤其是銀川女人卻頗以自己生于“首府”而驕傲哩!
我的城雖然是個都市,可是它不喜歡傳奇;銀川女人雖然再活色生香,可是她們不妄想傾國傾城。街頭屢屢走過戴蓋頭穿長袍的伊斯蘭婦女,她和染著黃發(fā)穿著小吊帶的少女一同前往肯德基,她的明眸并不顧盼,可是那目光深邃悠遠,看著你的同時好像穿越了時空。——這可能就是屬于銀川、屬于我的城的最獨特的風景。
我在這座城市里越住越久,我的身體已經(jīng)抹不掉它賦予我的氣味。
我辛苦地工作,當我作為中國電信員工為了網(wǎng)絡暢通常常忙到夜色闌珊時,我感受到了在一個大時代里作為普通勞動者的辛勤與不易;我努力地寫作,當我作為一個癡迷文字的人嘔心瀝血寫下一篇篇文章時,我把美好的感恩,由衷的快樂,都凝進了文字之中。當它們像小鳥一樣,帶著對愛、對美好、對善良的期冀飛向天地間,那一刻,我心潮澎湃。文字是我永遠的愛,對它,我的敬仰與愛慕無法言說。
我的城包容著我,在愛中學習,也在愛中修行。
我早已不再與它隔膜,我和我的城是“人面桃花相映紅”。
春來,我的城楊柳依依,有布谷鳥在叫:“布谷!布谷!”我就快樂地跟著我的愛去郊外踏青。云淡風輕,那一刻,沒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沒有什么急欲要犧牲所有人幸福以達成的國家目標,沒有什么不能挑戰(zhàn)質(zhì)疑的社會準則,沒有一定要肅然起敬的理論學說,只有愛情的可能,生命的愉悅,私密的甜蜜,真心的笑容。
那一刻我的笑容青春明媚,就是我的城最好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