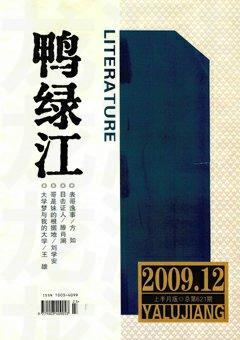哥是妹的根據地
劉學安,男,1965年8月生于江蘇沛縣,1995年開始發表小說,主要作品有《劉大買車》《水中有朵盛開的蓮花》《季美麗張大寶和足球》《風水寶地》等,現從事教育工作,業余致力于短篇小說和千字散文創作。
整個春天,小妹都沒打來電話。
兒子的高考分數一下來,妻子就沉不住氣了,幾次催促我跟小妹聯系,我沒有理睬。我知道小妹年后把家和才上初中的外甥交給公婆,就去了妹夫攬活的建筑工地做飯,起早貪黑很不容易,我不能再給小妹心里添堵。可兒子的入學通知書一到,妻子的催促就有了逼命的味道,見逼命也無效,妻子就搶去了我的手機,我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就騰地起身奮力去奪。兒子聽到客廳里響動異常,就從自己的房里出來,把糾纏在一起的我和妻子拉開,就對我說,你讓她打,我倒想看看她咋張開那個嘴。聽了兒子的話,我就重新回到沙發上。妻子卻瞪著兒子說,我都是為了你,你倒站到了他那邊,沒良心的東西。兒子走到妻子面前說,我給你創造機會,你就是這樣說我也不計較,誰讓媽平常那么疼我呢?媽,你現在隨意打,我擋住爸,反正我也想聽聽,大半年沒聽到姑的聲音了,好想的。妻子聽了,正想緩和的臉又陰云突起,厲聲說,你給我滾回自己房里去。兒子也來了氣,身子一轉,三步并作兩步,然后嘭的一聲,關上了自己屋的門。
妻子這次破例沒去安撫生氣的兒子,低頭在我的手機里翻找,找到小妹的號就按呼號鍵。一按沒人接,再按沒人接,倔強的妻子第三次一聽對方不應答,就重重地把手機扔在我坐的沙發上,然后也嘭的一聲關上了臥室門,新一輪冷戰又開始。我暗自慶幸,又可過一段肅靜的日子。
遺憾的是這輪冷戰時間太短。第二天早上,我就被妻子從沙發上一把拽起,睡意朦朧的我心里雖然非常惱火,卻沒有發作,很明顯,妻子想繼續昨天的戰爭,我無心戀戰,就把臉轉向另一邊。沒想到妻子用力把我的頭一轉,讓我的臉對著她后,說,連打了三次都不接,就是再忙,都過一夜了,也得給你這個親哥回個電。我說,沒回,就說明她的手機不顯號。妻子說,不顯號,也得知道有未接來電。我說,知道有未接來電,就能認為是你打的?妻子說,不能認為是我打的,也應該認為是你打的。我說,她要是不認為是我打的呢?妻子說,那也應該認為是兩邊家里打的,不能挨個給回一個?我說,小妹沒有你聰明。妻子說,我要有她聰明,就不會讓她搞成這個樣,你要不打,你就去找。我眼一閉,決心不再理睬。妻子手猛一松就下了最后通牒,陰著臉亮開嗓門說,我再問你一遍,你到底去不去?你要不去咱就離。我正想著如何應對,兒子突然又打開門說,要離就快離,今天就去辦手續,你們一走,我也走,再也不進這個家。
后來的幾天,妻子沒再鬧,我按照兒子入學通知書上的要求,抽空到相關部門辦理了各種手續。這期間,我也試著打過幾次小妹的手機,先是沒人接,再是已關機,后來再打手機已欠費。我就打妹夫的,剛響兩聲,妹夫很親熱的聲音就傳過來,哥好,我在工地。我說,都好,你忙嗎。妹夫說,忙,家里有事嗎,有事您就說。我說,家里沒事,小芹的手機咋回事?妹夫說,她年后來這,手機就好自動關掉,又天天忙得抽不出時間去修,就放在了住處沒帶,前幾天手機又欠費,就徹底不用了,反正俺倆在一起,大哥以后有事打我的。我說,還以為又出啥事了。妹夫說,哥你放心,沒有出啥事,要不,等會讓小芹給你回一個。我說,不要回,你們忙吧。
小妹真的沒有回電話。
小妹的電話是突然來的。
已是晚上十點多,我剛從廣州坐上回家的火車,一聲“我在仰望月亮之上”很突兀地在相對靜下來的車廂響起,對面及左右鄰座都瞅我,我不好意思地一一點頭笑笑,就從褲兜里掏出手機,一看是小妹的,就趕緊接。小妹說,哥,你在哪?我說在廣州。小妹說,是送侄子上學吧?我說,是,手機修好了?小妹說,那個不能用了,這是別人送的。我說,你倆不是在一起嗎?小妹說,他現在又在另一個工地攬了活,我們一人看一個。我笑笑說,小妹不簡單啊,都當工頭了。小妹說,哥別笑我了,也是沒辦法的事,不就是想多掙兩個錢嗎?我收住笑說,要是遇到事,你能行?小妹說,我只是幫他看著,啥事都是他來回跑。我說,你可得用心看好。小妹答,哪能不用心?聽小妹說到這,猛然意識到小妹打電話肯定有事,就問,小妹有事吧,有事你就說。小妹那邊有了停頓,我就又重復說,有事你就抓緊說。小妹說,哥,你可別生氣,侄子上大學,咱爹娘前段日子都告訴我了,我一直想等拿到工錢再跟你打電話,沒想到你都送侄子到學校了。我說,妹,我知道你難,這事先前哥沒告訴你,你也別怨哥,我已坐上回家的車,要是因為這事,你就別說了。小妹問,你把侄子安排好了?我說,都安排好了,要是沒事,我就掛了。小妹又停了停說,哥,那,那就掛了吧。我就掛了。
我把手機放進兜里,抽手時,右肘部撞在了后靠背上,雖說不疼,還是下意識地揉起來,才揉了兩下,又想起小妹打來的這個電話,小妹肯定有必須說的事,肯定還是她無法解決的事,我趕緊掏出手機又打給小妹。小妹說,哥,你有事嗎?我說,有。小妹說,哥,你有啥事就快說。我說,你有啥事就快說,挺麻利個人,咋也學會吞吞吐吐了?小妹說,哥,我沒事,你要沒事就掛了吧,你手機可是漫游收費的。我說,小妹,別磨蹭了,我知道你有事,你要是不說,哥這一路都放心不下。小妹再把話傳過來,就有了哭腔,哥,我沒事。電話就斷了。
我又打過去,直到服務小姐說“對方不應答”,小妹都沒接,我又打,手機只響了兩聲就斷了。正瞅著手機納悶,小妹發的信息就到了,小妹說,哥,我沒事,只是問問侄子上學的事,一路平安。我盯著小妹發的信息,反復念了兩遍,又打了過去,小妹這次反應很快,說,哥,你有事就說。我說,妹,還記得以前我告訴你的話嗎?小妹說,記得。我說,我想聽你說一遍。小妹說,哥,我記得還不行嗎,我正忙著。我火了,說,忙也得給我說一遍。小妹說,哥,我真沒事。我說,你是真想讓我心懸一路?小妹說,我沒事。我再次火起,你再說沒事?小妹說,哥,你咋總盼著我有事呢?我真沒事。說完就掛了。
我再打,小妹的手機已關。我又打妹夫的。手機一通,妹夫說,哥,我正加班,有話您說。我就說,小芹已把事情告訴我了,你再細說說。妹夫說,哥,確實不好意思。我說,客氣啥,你再具體說說。妹夫說,你也知道,年前,因為蓋樓的那家企業出口美國的一大批貨款沒打過來就停產了,工錢沒給,上邊又壓著讓發清干活的工錢,我把家里所有的錢都拿出來都沒夠,您知道后又給了兩萬,還不夠,我又瞞著您一毛的利貸了私人兩萬,原說半年還清,現在都快超三個月了,人家逼著還,只好又麻煩您。我說,為啥不早說?妹夫說,您給的還沒還,侄子又考上了大學,您跟嫂子也夠緊的。我說,再緊,我們是月月進,你這一貸,可是天天往外扔呢,干脆利索地告訴我要多少。妹夫說,連本帶息得兩萬六,再加上兩個要工錢急著送孩子上大學的,要是可能,您就給想辦法在鎮里銀行貸四萬,最多三個月,等這邊錢一下來,我就連本加利都還上。我說,好,我知道了,你忙吧。
鄰座的已開始睡覺,我不好再打電話,幾次試著也睡一睡,眼就是閉不上,總是想著這四萬哪里去找。說實在的,自從打發了兒子上學,除了兩張已取空的工資卡,家里確實是沒錢了,按說,作為鎮工業助理,找個理由向手下的企業周轉一下也不是沒有可能,可鎮里有規定不允許不說,萬一向誰張了嘴,就欠了人情,人家以后再以此在工作上要方便,政策再不允許,可就是自己給自己下了套子。現在惟一的辦法就是貸,只要符合規定手續齊全程序運作規范,就是鎮里領導知道也說不了什么,誰能不遇到難事呢?可具體咋操作呢?以前還真沒貸過。
天亮時才迷糊著,又被下車的吵醒,睜眼一看手機已八點,就想給懂這事的一個朋友打電話,小妹的電話又來了,沒等我開口,小妹說,哥,你都知道了?我說,你不說,就沒人給我說了?還是親妹呢。小妹說,哥,不是我不說,讓你一路擔這個心思,我放心嗎?他剛才回來一告訴我給你說了,我就把他罵了一頓。我說,你別怪他,是我先告訴他你已經說了他才說的。小妹埋怨道,哥,你也會使詭計。我說,妹,對不起,我不這樣,你能說嗎?小妹說,本來打算,多做點,先把哥的錢還上,沒想到,這里活好干錢難要,先給的除了工地上這樣那樣的開支就不剩了,再要,人家讓等等,一等二等活就完了,更難要了。我說,這不是白受罪嗎?還干啥?小妹說,不干,就憑家里那點地,手里連個活錢都沒有,日子咋過?其實,只要攬下的活,就是人家留個尾巴不給,算著都是賺的,要不是年前什么金融風暴刮到這里,賺的大部分都欠著沒給,我們也不會難成這樣,我們也是急得沒辦法了才告訴你的。我說,妹,你放心,我一定幫你過了這道坎。小妹說,哥,能辦就辦,不能辦,也別急,這事就是急也不在乎三天兩天,你回來再說也一樣,千萬別在車上想。我說,妹,你放心,出門在外,啥輕啥重,啥得急啥能緩,我還是會處理好的,不過,你以后一定要記住我以前說的那句話。小妹說,哥,我記著呢。我覺得手機里小妹有淚在流。
又是晚上十點多出了徐州站,就上了往返縣城晝夜不停的大巴,凌晨一點就到了家,妻子開了門,問了幾句兒子學校的情況,聽說我在車上已吃過晚飯,就讓我趕緊洗澡休息。我洗完澡躺在沙發上,又繼續想貸款的事。正想著,妻子走到跟前說,還不去睡?我說,這不是睡下了嗎?妻子一把又拽起我說,到床上去。我笑笑說,這待遇可是好長時間沒享了,今晚是不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妻子也笑笑說,好好表現,這待遇算什么?說完就推著我進了臥室。
與妻子并排躺在床上,燈雖關了,眼仍閉不上。妻子探起身子看看我,問,為啥還不睡?是不是在想啥?我說,不想啥,這就睡。妻子重新躺下說,明天就要開學了,不想啥,我可睡了。我一愣,騰地探起身子,瞅著妻子說,是不是送兒子有功,想報答我?妻子瞅著我說,送你兒子上學,有什么功?就是有功,也輪不上我報答你。我又把臉靠近妻子說,是不是想讓我享受更高級別的待遇?妻子嘴一撇,我這天天讓人煩的黃臉婆,哪有啥更高級別的待遇讓你享?說完就瞅著我笑。我仍笑著說,半夜三更,話里有話地暗示我,是不是想讓我叫你舒坦舒坦?妻子一轉身,背對著我說,我一直都很舒坦,卻不知道你要享的更高級別的待遇是啥,要享你享,不享我可要睡了。我扳平妻子的身子說,這可是你說的。說完,三下五除二就翻身上馬,身子一展開,就快馬加鞭縱橫馳騁起來,像火車穿越長長隧道,兩旁不甚分明的景物在無暇顧及中頻頻后退,妻子開始長鳴,我更是揚鞭催馬風馳電掣,沒想到前面出現了一座銀行大樓,一看是傍湖鎮西門的那家,就想到了貸款,一想到貸款,我就看見銀行門口一群膀大身寬的漢子用刀子逼著矮小干瘦的妹夫去貸款。我趕忙緊勒韁繩。緩沖中,妻子見動作慢了下來就說,快。我再沒興致快起來,就下了馬。妻子讓再來,我仰躺在床上直搖頭。
沒有滿足的妻子開始了憤怒。妻子說,是不是在廣州住了賓館?我說,是。妻子又說,是不是找了小姐?我說,沒。妻子轉身騎到我身上,按住我的雙肩說,沒找小姐,咋這樣?我一把拽下妻子說,來回折騰了好幾天,我能不累嗎?妻子說,我看你不是累的,是心里有事,你一進門,我就看出來了。我說,沒事。妻子說,沒事?有事沒事你能騙了我嗎?你要是遇事不擺在臉上還能總是個助理嗎?我說,適可而止吧,別這山望著那山高了,能月月拿上工資就不錯了。妻子說,你看你那點工資多讓人稀罕。我說,又來了,能不能今夜讓我先睡個安穩覺?
妻子是一名教師,原在城區一所縣直小學上班,前幾年先是不聲不響托人在縣醫院開了個病歷請了假,接著就通過縣里一個負責教師人事的同學,把自己的工作關系轉到了縣城一個較遠的郊區村小,又自作主張在縣中學附近租了個門面做起了學生用書的生意。自去年公務員長了工資,教師要拿績效工資的消息傳進耳朵,年前就以兒子高考為由把門面轉給了別人,同時把暑假后想回縣城上班的要求說給了同學,然后全力以赴用在兒子身上,平常對待周末才回家又有了親熱需求的我,又總以怕驚動兒子為由,不是草草打發,就是堅決拒絕。非常時期,我不計較。沒想到兒子高考一完,我就慘了,先是說我的工資養不了家,別說再供兒子上大學,接著就說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財不發,見我不理,就讓我催要小妹拿走的錢,我仍不理。妻子見我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冷戰就開始,先是妻子做飯只做她和兒子的,我要吃得自己動手,心想自己動手就動手,只要相安無事。可經過幾年商場打拼的妻子已成了一盞并不省油的燈,每逢周末便舊事重提向我開戰,我先是任憑重炮快槍殺聲震天慘遭身心重創,仍頻頻掛起免戰牌。可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妻子言語殺傷力太大,我就奮力抵抗,有時一抵抗碰上從外面回來的兒子,我就趕緊打住迅速撤進兒子房里。妻子卻以為援兵到了,更是窮追猛打愈戰愈勇,兒子一看情形就出面干預,指責妻子。妻子一被指責,就收槍撤炮,一邊為自己辯解,一邊安撫生氣的兒子,我趁機逃出兒子房間。妻子安撫好兒子出來,見我在客廳坐著,就狠狠地睕我一眼,于是又是新一輪冷戰。
我以為三更半夜要求睡個安穩覺并不過分,可沒有了兒子干預的妻子,戰火一旦燃起,就再也無所顧忌。妻子說,想睡個安穩覺可以,先得把要說的事說清楚。我說,還有什么沒說清楚的?妻子說,你不是向我炫耀你的工資嗎?你看看咱這里當公務員的,哪個還用工資過日子?我說,不用工資過日子用什么過?妻子說,用工資以外的過。我說,這不是明擺著讓我犯錯誤嗎?你要知道,要是犯了錯誤再違了法,連我被你攥在手里的工資都沒了。妻子說,那就告訴我啥時候去要回那兩萬,要回來,你不想送禮再升一級,我還想貸出去弄幾個利息。我說,小妹能不還你嗎?妻子說,你說她啥時候還?你給我個準確日子,你就睡覺,不然,你別想睡。我說,我記得咱買這房時,小妹當時是不是給了十萬?妻子說,她給的我還了,我給的,她還了嗎?我說,當初裝潢這房子時,要不是妹夫丟下掙錢的活,幫著設計,跟著進料,領著人沒要一個工錢做了二十多天,你這兩萬能存下嗎?妻子說,要不是親戚,他能這樣嗎?我說,要不是親戚,小妹能向你張嘴借嗎?妻子說,要不是親戚,就是向我張嘴借,我也不借她,既然錢借你了,幫你應了急了,如今我急著用錢了,你就得趕緊想法子還,不光不還,還躲著連個話也沒有,以后誰還借你?我說,小妹沒躲也沒藏,小妹一聽說咱兒子考到廣州去了,就操辦錢,可錢不是土坷垃,想要順手就抓來了,要不是這段時間工錢難要,早給你了。妻子說,以前只一個人出去都掙錢,現在兩口子都出去了更掙錢,她不是沒有,是不想還。我騰地坐起,開了燈,瞪著妻子說,如今全世界都缺錢,她那種在外饑一頓飽一頓的日子還有準?妻子也騰地坐起說,正因為沒有準,你才得趁她有錢時抓緊要,你現在不抓緊要,等她的孩子也該像咱一樣花錢了,你就是要,她也不會還你,她肯定現在就開始為孩子準備了。我說,小妹不是你說的那樣人。妻子說,你說是哪樣?我說,她要是你說的那樣的人,不但現在大學畢業參加工作的不是我,她也不會等到我畢業工作結婚后再出嫁。妻子說,這些是你們兄妹的事,跟我沒關系,就算你上了大學有了工作,早知道你這死眼珠子肉眼皮的性子,我嫁誰也輪不到你。我說,好,好,好!妻子說,你也別好好好,就是現在跟你了,也不能說就跟你一輩子。我說,你也別以為自己有啥了不起,要不是我托人情,你也不會知道你有個同學在縣里負責教師人事,你更到不了縣城來。妻子說,要不是到縣城來,我能為這房子離開單位好幾年受這罪嗎?王寶釗十八年寒窯等來了做了官的薛仁貴,我跟你十八年卻養了你這個胳膊專往外拐的負心漢。妻子說到這一躍而起,跳下床,把我和我的衣服一起推出了臥室,嘭地關上門說,吳一鳴,你給我聽仔細,錢要不來,你不但不能在這屋里睡,我王彩鳳還得跟你離。